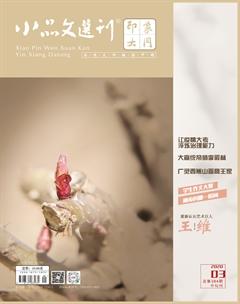母親的吉祥三寶:房子、自行車、縫紉機
姚一平
2019年的母親節剛剛過去,這些日子,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母親的許多往事,不時在我心頭縈繞。她老人家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七年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更加思念我的母親,
母親生前不僅含辛茹苦地撫育了我們兄弟姐妹五人,而且在1958年那個大躍進的年代里,一度走向社會參加工作,在呼市文化系統的“人民電影院”、“和平電影院”先后工作了五年。母親一生有過三件寶貝,可謂是她老人家的“吉祥三寶”,伴隨她走過大半個人生。
1945年,山西左云城內,結婚不到半年的父親,在日寇投降前夕,參加了八路軍,跟著賀龍的隊伍離開了家鄉。身懷有孕的母親,回到了鼓樓北面草市街12號我的姥爺家。第二年正月我出生了,從出生到離開左云老家來到當時的綏遠(呼和浩特市),七年期間我只見過父親一次面。聽說是父親所在部隊駐扎在大同口泉,他請了五天假,步行回鄉探親,一家人相聚僅僅只有三天。七年的童年生活,是母親帶著我在左云姥爺家度過的,日子過得十分清苦。
解放后土改的時候,政府按軍屬分給我和母親兩間磚瓦大正房,位置在縣城中心鼓樓附近,路東一個當年叫“萬云店”的大院里。房子離姥爺家很近,中間只隔著姓趙的藥鋪和姓武的中醫診所兩家店面。這兩間房子母親視若珍寶,因為從此以后,我們結束了無家可歸的日子,再也不用租房或六七口人擠在姥爺家一盤炕上了,心里別提有多么高興。
那時候,20多歲年輕的母親在縣城東街完小讀書,因為是軍屬,一切學雜費政府全免。每天放學后回姥爺家吃飯,晚飯后再領著我回自己家睡覺。除此之外,每月政府發給我們娘兒倆“優軍糧”小米或玉米45斤,成了我們母子和姥爺一家六口人主要的口糧來源。母親經常說:“感謝共產黨、毛主席、分給我家這兩間寶貝大正房,又分口糧,又免費上學”。沒有想到這兩間房子,后來演變成母親的“吉祥三寶”,在不同時期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綏遠和平解放后,1952年父親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在文化系統工作。1953年母親領著我,抱著剛過百歲的妹妹林平,離開老家來到當時的綏遠,從此一家人得以團聚,暫住在新城東街父親單位。1956年,我家追隨父親單位從新城搬到舊城。
這期間我二妹麗平和弟弟維平相繼出生,他們倆人一個出生在新城,一個出生在舊城。山西老家的那所房子被縣糧食局占用,換給我家的是南街魁星樓(圓樓)附近有著兩間正房的獨門獨院。我們離開左云后,姥爺找了家熟人居住,不收房租只為看門。
1958年大躍進年代,政府提倡解放婦女勞動力,鼓勵家庭婦女走出家門投身社會。已經四個孩子的母親,在文化系統的電影公司參加了工作。公司安排母親在舊城九龍灣的“人民電影院”上班,三年后又調到大召前的“和平電影院”。
那是1959年,我剛剛上中學,大妹妹上小學一年級,二妹妹和弟弟送到乃莫齊召旁的一家公立幼兒園,年邁的姥姥從老家來幫助料理家務。為了上下班方便和照顧幾個孩子,母親決定買一輛自行車。母親剛參加工作工資只有23元,連同父親兩人的工資合在一起才一百多元,加上老家親戚還需要經常接濟,生活并不寬裕。為了籌備買自行車的錢,一時間愁煞了兩位老人。經過反復考慮,決定還是把左云的寶貝房子賣掉,給母親買自行車。那時候人們生活水平很低,手中沒有錢,更何況老家那座小縣城。父母親回老家,兩間房加一個小院只賣了200元錢。去掉路費和留給姥爺的20元,回到呼市后,母親用剩下的160元,買了一輛26型墨綠色永久牌自行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自行車是人們的心愛之物,這輛墨綠色的26自行車,從此成了母親又一件心愛的寶貝。當年母親只有三十多歲,每當她騎著嶄新的自行車走在路上或者去人民電影院上班時,總會有人投來羨慕的目光。每逢周末周一去幼兒園接送二妹和弟弟時,母親便用自行車推著姐弟倆,一前一后既體面又方便。母親在電影院工作,是她最陽光的幾年,在這期間,曾經參加過兩次單位組織的抗旱和秋收勞動。一次是在保全莊,另一次是在八拜公社的白廟子。每次下鄉時間大約半個月,吃住都在鄉下,對于下鄉和各種集體活動,母親總是樂此不疲。在勞動閑暇,便騎著她的寶貝自行車回家看望姥姥和我們兄妹們。有了這輛自行車,我家大妹妹林平和大院里她的好友們,成了巷子里最早學會騎自行車的小女孩。
1962年,國家處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年代,物資極度匱乏。許多單位相繼下馬,精簡下放在職人員成了當時的一大潮流。在此大環境下,兩位老人商量,決定母親退職回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父親當年正在文化局電影藝術科任科長,家屬理應起帶頭作用。二是家里孩子多,而且都已經上學,況且姥姥年邁,又惦記著老家的親人們,長此以往也不是辦法。退職前,母親每月工資和加班費將近拿到40元,如今回到家里,僅靠父親一人工資生活,日子就顯得拮據起來。后來聽說通順北街的“呼市棉針織廠”,所生產的半成品手絹,碼邊這道工序可以放外加工,只要熟人擔保就可以。面對家務、掙錢兩不誤的好事,母親心動了。只是我家沒有縫紉機,這可難住了兩位老人。于是,母親又開始打她的寶貝自行車的主意了,決定賣了自行車買臺縫紉機。
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年縫紉機、自行車、手表通稱三大件,實行憑票供應,很難買到。寶貝自行車自然非常容易就出了手,因為保養的好,幾乎沒有賠錢。縫紉機價高,需要200多元,賣掉自行車的錢還差許多,何況票證又不好弄。最后還是父親從雜技團的一個鄭姓朋友那里,買了他家一臺八成新的二手貨。這臺縫紉機,從此便成了我母親又一件新的寶貝。
每次從棉針織廠背回來成包的半成品手絹,母親便沒日沒夜拼命加工。除了給一家人做飯,幾乎整天伏機操作,晚上一直干到深夜。那時候,雖然每張手絹加工費只有5厘錢,然而母親既手快又辛苦,每個月下來可以拿到近30元的加工費,折合六千張手絹。有了這臺縫紉機,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再不用花錢到外面找裁縫,每年還能省不少錢。即便1966年我的小妹文平出生,母親的縫紉機也一直沒有停止轉動。就這樣精打細算,母親用她的寶貝縫紉機和父親一起度過了那個困難年代。
母親用土改分到的寶貝房子,演變成的自行車、縫紉機三件寶貝,為我們這個七口之家,在不同的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母親的吉祥三寶,也成為我們教育晚輩的極好教材。現代人看起來實在是再平常不過,就其價值而言,也難與當今動輒幾十萬的房、車、高檔消費品、相提并論。然而在我們這些子女的心里,母親留下的卻是老一輩人精打細算、勤勞、堅忍、節儉的品格。也是那個年代母親對家庭、對子女、無私的付出和無疆的愛。
- 小品文選刊·印象大同的其它文章
- 別樣的風景
- 攏兩袖詩風 品一味禪心
- 大同古跡中的中國之最
- 櫻花開又放
- 1934年,蔣介石來了大同
- 糖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