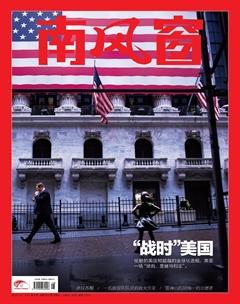疫情不是所有問題的理由
譚保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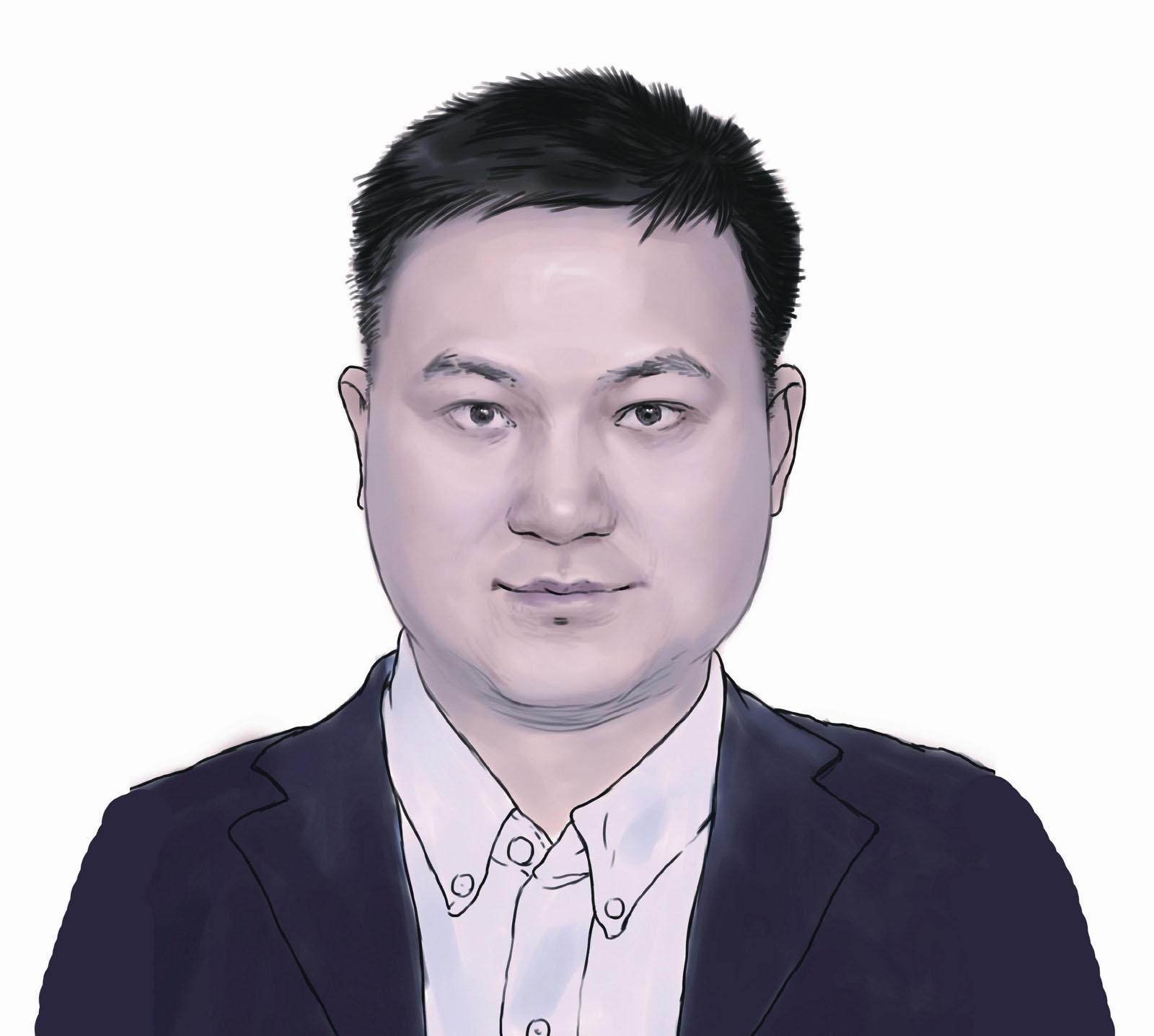
疫情暴發以來,很多地方通過兩個方式來刺激消費,有的是領導帶頭去“吃喝”,有的是發放購物券,也有兩者兼而有之。這些地方官是懂經濟的人,懂得在這個特殊時期,信心的重要性。
不過,消費要馬上起來,的確不現實,它只能慢慢恢復。而且,恢復的時間通道有多長,也取決于全球何時能夠戰勝疫情。但是,我們也不能把消費的疲弱完全歸罪于疫情,這會導致我們失去思考一些經濟領域結構性問題的能力。
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欲望,經濟學家還提煉出邊際消費傾向這樣的術語,但歸根到底,消費取決于財富能力。財富來自工薪和資本利得。首先,近幾年,很多工薪族的薪資其實變化不大,能跑贏通脹,已經實屬不錯。為什么?
很簡單,大多數中國人的就業都在民營企業,民企可以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服務型民企,提供白領崗位。另一類是制造業民企,主要提供工人崗位。就服務型民企(互聯網除外)而言,企業的盈利能力在這些年并無顯著提高,白領們的薪資增長自然也不顯著。
對制造業民企來說,它們的確為農民工進行過大規模地漲工資,但這些年,一些企業外遷東南亞,中國農民工的崗位正被越南人、柬埔寨人和馬來西亞人進行替代,大規模漲工資其實已經停滯。因此,工薪族的薪酬,已無法為消費快速增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即使沒有疫情。
再拿資本利得來說,過去幾年,我們經歷了兩次大事件,一是2015年股市大跌,二是2016年樓市“爆炸”。股市大跌好理解,它是財富的毀滅機,除了少數提前撤退的大鱷之外,不少中產遭受了堪稱人生折磨的財富損失。2016年的房價上漲,則要分開看。
疫情面前,必須要先救企業,保就業,這是一個底線。但與此同時,疫情也不等于要全面暫停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步伐。
資產價格飆升,肯定會為持有者帶來強大的財富效應。即使只是沒有實現的浮盈,依然能給人信心,持有者會認為自己持有的核心物業,將給下半生帶來更確定的現金流,未來更美好,所以敢于消費。
近兩年消費的增長,很大程度正是源于核心城市(一線城市、省會和單列市)中堅階層由于房價上漲帶來的消費溢出。他們敢于旅游,敢于投巨資給孩子補英文,敢于網購曾經認為奢侈的消費品,敢于知識付費憧憬未來。實際上,疫情之前,旅游、教育、電商和知識付費,正是最火爆的四大產業。
但房價上升也帶來問題的另一面。首先,核心城市的居民其實只占中國人的很小一部分,只靠一小部分人的消費溢出,要提振內需,還遠遠不夠。另外,房價上漲并不是持續性的,當房價上漲停滯,那么資產持有者的消費信心就會隨著時間而遞減。
同時,再加上遭遇疫情,就業市場出現一些不確定性,那么按揭壓力就會浮現。最近,一些國有銀行一線城市的分行承諾按揭者可暫緩月供,政府部門則公告強調租房者不得強迫房東減免租金,這些操作的背景正是監管層認識到房東們的現金流壓力。
現在,中國人民已初步戰勝疫情,但后面的戰斗依然很艱巨。疫情面前,必須要先救企業,保就業,這是一個底線。但與此同時,疫情也不等于要全面暫停經濟結構性改革的步伐。至少,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結為疫情的沖擊。
不喪失審視自我的能力,才能在疫情結束之時,一馬當先。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