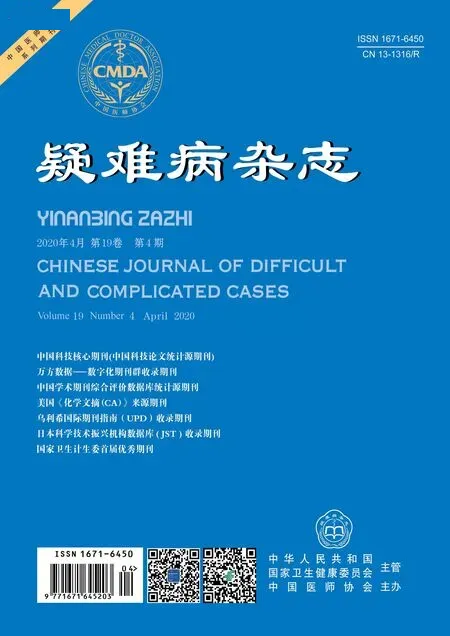肺表面活性蛋白A在肺外疾病免疫炎性反應中的作用研究進展
趙正,楊雪綜述 趙敏審校
表面活性蛋白(SP)是由肺泡Ⅱ型細胞和氣道Clara細胞合成并分泌的一種脂蛋白復合物,是構成肺表面活性物質(PS)的重要組成成分,具有降低肺泡表面張力、提高肺的順應性及促進氣體交換的作用。目前明確的SP共分為4種,分別為親水性的SP-A、SP-D和疏水性的SP-B、SP-C,其中 SP-A含量最豐富,約占SP總量的50%[1]。最初人們對SP-A的研究僅局限于肺組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其在多個組織器官如腸、腎、黏膜組織及中樞神經系統中都有表達,且SP-A含量的變化與肺內和肺外疾病密切相關[2]。因此,SP-A在局部防御及免疫調節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現就SP-A的特征性結構、功能,以及在多種疾病中的表達和免疫調節作用進行綜述。
1 SP-A的結構特征
SP-A是屬于凝集素家族的一種模式識別分子,具有凝集素家族蛋白特征性的多聚體結構,每個單體由4個不同的結構域組成:N-末端區域參與鏈內二硫鍵的低聚反應,膠原樣區域(4CLR)構成多聚化三聯螺旋體結構,α-螺旋結構域維持肽鏈多聚狀態,C端糖識別域(CRD)用于識別并結合碳水化合物[1]。其中CRD是凝集素家族共有的結構,位于肽鏈的羧基端,為球狀結構區,其上有鈣依賴型糖識別位點,在鈣離子參與下,可促使凝集素蛋白與多種病原體的糖結合[3]。3個肽鏈由二硫鍵和非共價鍵連接組成一個穩定的三聚體亞基,構成SP-A的三級結構。SP-A的四級結構是由6個三聚體并聯而成(6×3=18 CRDs),呈“花束”樣排列。其頸部由N-末端區域和CLR的一部分構成,而α-螺旋結構域和CLR的剩余部分構成了“花冠”樣結構,而肽鏈的另一末端CRD則卷曲呈球狀結構域,使得花冠部成為凝集素糖識別部位,見圖1。這種多聚體結構增強了SP-A結合免疫細胞及病原體的能力,是其發揮免疫調節功能的生化基礎[4]。

圖1 SP-A的生化結構
2 SP-A受體
由于擁有特殊的結構,SP-A能夠與多種免疫細胞和病原體表面受體結合,并參與調控免疫細胞功能及免疫炎性反應。SP-A對免疫反應的不同作用主要依賴于參與調節的細胞受體不同,因此了解SP-A的結合受體對研究其免疫調節功能至關重要[5]。Toll樣受體(TLR)是參與非特異性免疫的一類重要蛋白質受體,是一組高度保守的模式識別受體,能通過識別病原相關分子模式(PAMPs)和危險相關分子模式(DAMPs)引發機體的天然免疫反應[6-7]。活化后的TLR能促發細胞內級聯反應并激活一系列轉錄因子,包括NF-κB、AP-1、IRF-3和IRF-7等,并進一步促進多種促炎性細胞因子如TNF-α和IL-1β的產生[8-9]。研究發現SP-A通過Ca2+依賴途徑以CRD結構域與TLR2、TLR4可溶性胞膜外區以及MD-2受體相結合[10-11]。SP-A能抑制LPS與TLR4/MD-2的結合并減弱LPS誘導的炎癥級聯反應[12]。另有研究還證實,SP-A能在轉錄后水平調控巨噬細胞TLR2和TLR4的表達[13]。SP-A雖能上調巨噬細胞TLR2表達,卻又同時抑制了TLR2介導的NF-κB信號通路,SP-A通過影響信號通路中的關鍵調節因子,如IKBα的磷酸化、p65的核異位、MAPK家族的成員磷酸化及Akt的磷酸化減少進而影響NF-κB信號傳導,最終導致TNF-α顯著減少[14-15]。信號抑制調節蛋白α(SIRPα)是一類廣泛表達的糖蛋白分子,屬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結構域受體。SIRPα在多種免疫細胞如巨噬細胞和樹突細胞的表面均有特異性表達[16]。有研究發現SIRPα在維持并調節小鼠T淋巴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的穩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SIRPα還被證實參與抑制巨噬細胞中TLR介導的信號通路,因此也被認為在溝通機體固有免疫和獲得性免疫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17]。研究報道SP-A能通過與SIRPα和CD-91鈣網蛋白復合物相結合調節免疫細胞功能。當接觸病原時,SP-A通過CRD結構域結合SIRPα并抑制炎性介質的產生;當接觸外源性微生物或細胞碎片時,SP-A通過其CRD結構域結合病原,而游離的CLR區域通過CD-91鈣網蛋白活化免疫細胞[18]。此外,研究還發現SP-A還能結合天然和重組的可溶性CD14。CD14是LPS的結合受體,SP-A的α-螺旋結構域與CD14亮氨酸富含區結合,并在LPS/CD14相互作用中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19]。SPR-210(surfactant protein receptor 210 kDa)最初是從巨噬細胞U937細胞株中純化提取的SP-A結合蛋白,在Ⅱ型肺泡細胞及肺泡巨噬細胞中也有表達,SP-A通過CLR區域結合SRP-210,并參與介導結核分枝桿菌的攝取[20]。此外,SP-A還能直接通過CRD結構域和鈣離子依賴途徑結合各種細菌、真菌和病毒表面的甘露聚糖、海藻糖、N-乙酰葡糖胺及脂質來識別它們。還有研究證實SP-A能結合糖蛋白-340(Gp-340)、髓過氧物酶(MPO)、補體蛋白C1q、免疫球蛋白以及補體受體CR3等,并通過多種途徑參與機體的免疫反應[21]。
3 SP-A的免疫調節作用
機體在自然狀態下接觸到很多致病性的病原體及抗原,從而觸發免疫細胞介導的免疫應答,以保護機體抵抗外來刺激的入侵。SP-A作為C型膠原凝集素的一員,能通過多種機制參與免疫調節作用。首先,SP-A的糖識別域能黏合多種細菌、真菌以及病毒等病原體,并通過和免疫細胞受體結合募集巨噬細胞及中性粒細胞參與炎性反應調節,直接殺傷病原微生物[22]。其次,SP-A還能增強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對病原體的吞噬清除功能,而敲除SP-A基因后小鼠肺泡巨噬細胞吞噬病原菌的能力明顯下降[23]。SP-A還能通過上調免疫細胞表面的病原結合受體從而增強免疫細胞對病原的攝取,研究發現SP-A能增強巨噬細胞表面清道夫受體A進而促進其對肺炎鏈球菌的攝入,還能通過上調人巨噬細胞表面甘露糖受體的表達促進結核分支桿菌清除[24-25]。另有研究發現,SP-A能抑制樹突細胞的成熟,并抑制了由植物凝集素、CD3特異性抗體和佛波酯誘導的T細胞增殖[26]。SP-A的CLR和CRD結構域通過Ca2+通路抑制T細胞活化,進而抑制由T細胞活化引發的炎性級聯反應[27]。另有體外研究證實SP-A能增強肺泡巨噬細胞對凋亡細胞的攝取。SP-A能通過鈣網蛋白和CD91依賴途徑結合凋亡細胞并對其產生清除作用[28]。此外,SP-A還能參與調節細胞炎性反應,但不同研究表明SP-A對TNF-α等炎性介質的產生既有上調作用又有下調作用[29]。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SP-A是增強還是減弱炎性反應則主要取決于參與調節的細胞受體不同,而結合的受體又取決于SP-A與免疫細胞及病原體之間的相互作用。SP-A如何在體內外調節多重細胞炎性反應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此,SP-A可以調控免疫調節相關受體和細胞因子的表達,并能通過誘導活化的淋巴細胞凋亡等生理過程來維持免疫穩態,進而發揮其在機體免疫監視中的重要作用。
在呼吸系統中,SP-A在多種呼吸道病原體的先天免疫應答中起重要作用,包括A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結核分枝桿菌、煙曲霉、銅綠假單胞菌和流感嗜血桿菌等。SP-A通過識別和結合各種病原體并觸發各種免疫反應,包括調理作用,增強吞噬作用以及募集巨噬細胞和嗜中性粒細胞殺死病原體,并通過增加細胞膜通透性來抑制微生物的活性等。 SP-A還有助于清除凋亡細胞并調節炎性反應。 SP-A與免疫細胞的相互作用及其啟動清除的機制主要是由SP-A的膠原蛋白區域與這些細胞上的相關受體分子介導的。因此,SP-A的免疫調節功能在維持肺穩態和保護肺部不受感染等方面非常重要。現在已知SP-A的表達不僅僅限于肺部,還在人體其他黏膜表面及肺外組織也表現出廣泛的免疫活性,如消化系統、生殖系統及中樞神經系統等。但其在肺外部位的免疫調節作用還在不斷的研究和探索中[1]。
4 SP-A在肺外組織中的分布及作用
4.1 消化道中的SP-A 研究發現有一種類似于肺表面活性物質的疏水性蛋白位于消化道上皮細胞頂部邊緣和腔內容物之間,并最后認定為消化道表面活性物質[30]。隨后,研究人員又在大鼠腸道上皮細胞中檢測到SP-A的蛋白和mRNA表達,認為該蛋白是由腸上皮細胞自身產生并分泌的。研究發現消化道表面的肺表面活性蛋白不但具有潤滑并維持胃腸道表面張力的作用,促進腸道蠕動,還能有效地抑制腸道潰瘍因素[31]。研究發現,在炎性腸病及壞死性腸炎病例中SP-A表達上調并參與免疫炎性調控。壞死性腸炎的動物模型中,口服SP-A蛋白能有效降低腸內的炎性反應,減少TLR4的表達及促炎性細胞因子[32]。胃腸道中的SP-A能通過結合病原體表面受體減少其黏附于消化道上皮細胞,并通過結合細胞表面的特異性結合受體來抑制其下游炎性信號通路,進而參與宿主的免疫調控[33]。
4.2 女性生殖系統及羊水中的SP-A 研究表明,免疫活性SP-A在女性生殖系統中廣泛表達并參與免疫防御。在人體的子宮肌層、陰道上皮細胞及陰道灌洗液中檢測到SP-A的存在,且在女性月經周期不同階段陰道灌洗液中SP-A的水平存在差異,卵泡期SP-A水平達到峰值,這一變化可能與月經期陰道黏膜變薄,陰道菌群失調導致陰道更易感染有關[34]。此外,女性生殖系統中表達的SP-A能參與抵抗性傳播病原體的侵襲。研究發現SP-A通過結合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的包膜糖蛋白gp120抑制HIV感染CD4 T淋巴細胞,表明其可能具有抗HIV的作用[35]。自懷孕26周開始,人的羊水中就能檢測到SP-A蛋白的表達,而到鄰近分娩時(40周)SP-A水平顯著升高并能達到2~8 μg/ml[36-38]。免疫組化染色發現在孕晚期的羊膜上皮細胞和絨毛膜細胞中都有SP-A表達,SP-A通過羊膜細胞和蛻膜巨噬細胞識別并清除羊水中的病原體,抑制孕期的宮內感染,減少絨毛膜羊膜炎的發生[39]。人的分娩過程與宮內組織分泌的催產素PGF2α和促炎性細胞因子TNF-α密切相關。作為炎性調節蛋白,SP-A能夠有效地抑制巨噬細胞分泌TNF-α并推遲PGF2α合成信號通路[40]。此外,研究還發現SP-A在小鼠分娩早期表達升高,并伴隨著IL-1β和NF-κB水平上升。IL-1β和NF-κB都能刺激PGF2α合成信號通路,并誘發早產[41]。不僅如此,SP-A還能清除子宮平滑肌周圍的凋亡和壞死細胞,從而降低了宮縮引發炎性反應的風險[42]。
4.3 咽鼓管、鼻竇中的SP-A Yamanaka等[43]早期在人類的中耳灌注液中發現免疫活性SP-A的存在,開啟了SP-A在另一組織的研究。此后,另有研究人員發現把天竺鼠的肺表面活性物質、鹽水和混合磷脂灌入大鼠的中耳,發現肺表面活性物質能顯著降低張開咽鼓管所需要的張力。經進一步組織病理和分子生物學檢測證實,成年大鼠的中耳上皮細胞和鼻旁竇黏膜下腺中都表達SP-A蛋白和mRNA,且感染大鼠與未感染大鼠相比,中耳上皮細胞中SP-A mRNA水平明顯升高[44]。此外,在由感染、過敏或其他自身免疫性原因引起的慢性鼻竇炎患者中也發現SP-A表達顯著升高。SP-A蛋白還被檢測到在咽鼓管上皮細胞中表達分泌,并具有抗炎的作用。作為病原體進入中耳的必經之路,咽鼓管黏膜所產生的保護因子對于復發性中耳炎的防護至關重要。研究發現,對復發性中耳炎敏感性不同的兒童表達的SP-A表型存在差異,并認為咽鼓管上皮細胞中表達的SP-A蛋白參與病原體的清除并調節免疫相關反應[45]。
4.4 中樞神經系統中的SP-A 最近,SP-A在中樞神經系統(CNS)中的表達也得到了證實。Luo等[46]最先在SD大鼠的腦組織中檢測到具免疫活性的SP-A表達,且發現SP-A在髓鞘周圍的少突膠質細胞中深染。隨后,Schob等[47]在人腦活檢組織和多種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患者腦脊液中檢測肺表面活性物質的表達變化發現,SP-A在中樞神經系統中廣泛表達,神經元、膠質細胞和室管膜細胞中都有SP-A蛋白和mRNA表達,并認為檢測到的SP-A是由CNS組織自身產生的。此外,SP-A在自身免疫性腦病和腦炎患者的腦脊液中含量較陰性對照組顯著降低,提示其可能與CNS的免疫炎性調節有關。Yang等[48]在研究中發現,大鼠實驗性自身免疫性腦脊髓炎模型(EAE)中SP-A的分布和表達水平在EAE發病初期、高峰期和緩解期隨著炎性反應和膠質細胞的變化而變化,呈正相關。研究還發現SP-A在大鼠腦組織的星形膠質細胞以及體外培養人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中的表達,且在LPS的刺激下SP-A表達水平增加,且外源性加入SP-A能抑制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中TLR4和NF-κB P65的表達,同時減少了TNF-α和IL-1β的產生,由此認為SP-A能通過結合星型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的TLR4信號通路從而參與CNS免疫炎性反應的調節。
除以上組織器官外,研究人員還在胸腺、前列腺、腎臟和脾臟等組織中都檢測到免疫活性SP-A。此外,在胸膜、心包、關節滑膜等細胞中也存在SP-A,且這些部位的SP-A也具有結合并清除致病原的作用,在先天性免疫和獲得性免疫機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49]。
5 小 結
綜上所述,SP-A除了具有降低肺泡表面張力、提高肺的順應性及促進氣體交換的作用以外,還參與機體的免疫防御及調節。SP-A在免疫炎性反應及調節中的作用機制十分復雜且多元,而SP-A在其他組織器官中的表達及免疫調節作用也突破了人們對這種肺表面活性蛋白的狹隘認識。SP-A在不同系統疾病中的表達變化及免疫調控作用得到了廣泛的研究,但其調控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探究。SP-A調控免疫炎性反應的信號通路及其相關分子遺傳調控機制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不同組織器官之間的SP-A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并調控機體的免疫炎性反應是未來研究的重點。因此,對SP-A的免疫炎性調控機制的深入探究能為多種疾病的治療帶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