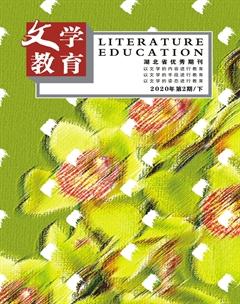關于非遺保護的理論思考

一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儼然是一句常用語了,但細究起來,其間似有不通之處。說保護物質形態的遺產,如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自然毫無問題;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正在其非物質性、無形性、精神性,如何能保護?當然,非遺是以種種物質媒介為載體的,如果這些載體不存,非遺確實無所依附。但若將非遺等同于這些載體,將保護非遺等同于這些物質載體的存續,難免讓人發出孔子的喟嘆:“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云”。所以,保護非遺這句流行語,還是值得再細究一番。
非遺的絕大部分屬于藝術范疇,這是我們立論的出發點。國內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十類,分別是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曲藝、民間美術、雜技與競技、傳統手工技藝、傳統醫藥、民俗。其中前面六類都屬于藝術,最后一類民俗也與藝術息息相關。剩下的三類大約可以歸于技術的范疇。無疑,技術是可以保護的,只要相關的知識能得以傳遞,所需的條件能得以保存,技術類非遺就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但是藝術類呢,藝術能夠保護嗎?
二
藝術是人類價值的彰顯,這是藝術的本質,并規定了藝術與人的關系,人回應藝術的方式。而且,我們不是說藝術是有價值的,或者有用的;我們說,藝術是價值的彰顯。這兩種說法有著根本的區別。因為人類是以價值維系其本質的,價值是一個高于人的范疇,就像古人說的“道”。那么道就不是一個我可以把玩的東西,而是規定我、成就我的“天命”。這就是《中庸》所謂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只有遵從這些規定,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即使不同的民族、時代對這些道的體認會有具體的差異。但無論如何,人離不開價值,“道,不可須臾離也”。
作為藝術的非遺,同樣是人類價值的彰顯,在其中蘊涵著人的規定、理想、尺度。其中有些是過往時代的價值,有些是今天還適宜的價值,有些甚至是永恒的價值。正是由于其價值性,它們作為遺產被傳遞、甚至遺留至今。比如國風楚辭傳承了兩千年,唐詩宋詞流傳千年,水磨昆腔也傳唱了六百年。正由于其價值性,作為一種對人性的啟蒙,一種呼喚,遺產才與不同時代的人們相對,這無論對古人還是今人,情形都一樣。
但是,我們不是懵懂的遺產傳遞者,也不能是自覺的遺產保護者。不如說,首先正是(偶然地)通過遺產,一代代人才發現了自己。正如林黛玉從《牡丹亭》中聽到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生命之急迫,我們也能在《桃花扇》中聽出故國興亡。遺產、傳統、經典的意義,正在于其對于人之生命的啟悟。而正是首先由于遺產的啟蒙價值,遺產才在這個過程中被偶然地或自覺地傳承——因為一代代人被唐詩宋詞打動,唐詩宋詞才一代代地流傳。換句話說,首先是“道能弘人”,然后人才能弘道。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說法不一定對。因為真正地接受遺產,接受真正的遺產,首先是種內在的實現,而不是外在的使命。所以,我們不是遺產的保護者,而是受贈者。因為人不是價值的保護者,而是價值的體認者,實現者。人甚至只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人根本不是價值的外在保護者。
所以,非遺作為藝術,作為價值的彰顯,是無從保護的。而且,號召保護非遺的理由,也應該是個價值層面的理由,而且是種比非遺本身的價值更高的價值。但無論如何,不應出于價值之外的理由來號召保護。可是在今天的流俗話語中,保護傳統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擁有更高的價值呢?比如,能不能出于“傳統”、“民族”、“認同”的理由來號召非遺的保護呢?僅僅因為是“國粹”,所以人人都要保護京劇嗎?因為是“傳統文化”,所以要保護種種地方性、小眾性的文化技藝嗎?
三
但反過來,人一旦感知到了遺產中價值的召喚,自然會走近非遺,體味非遺,以至被此一文化所化,而最終成為遺產的傳承者。當然,時移世易,世事無常,并非所有的遺產都能幸運地被傳遞。比如,無論好之者多么惋惜,像秦腔、花兒、賢孝、小曲、說書等這些西北的古老民間音樂,恐怕難以再現昔日的輝煌。對于日新月異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們,號召他們保護這些傳統是需要理由的,但有時候也不需要另外的理由。蘇陽,一個60后的時尚搖滾歌手,卻在人到中年,開始了與西北大山里的說書藝人、秦腔班主、花兒歌手們的廝混。張尕慫,一個90后的民謠歌手,開始在都市的彈起三弦,唱起西北的小調;甚至拜訪了100多位民間藝人,采錄民歌,學習表演。但是,不是他們發現了遺產,而是遺產發現了他們。我們也無需慶幸非遺因為他們而得到了保護,而應慶幸他們以及我們的生命因為這些非遺而變得更為深沉。在這個意義上,外在的保護其實是多余的。
所以,遺產復興的含義和意義,并不是遺產本身的外在延續,而是為傳統所化之人的內在生成。這也意味著,遺產的復興從根本上依賴于人被遺產所感動這樣一個內在的過程。一種藝術的興衰,從來都與藝術家的涌現與消失息息相關。人存,則藝興,人亡,則藝息。被視為項目的非遺,其背后實際上都是一位位的藝術家甚至大師,或如日本所謂的“人間國寶”。大師故去,新秀不起,即使非遺項目能夠以影像等形式被記錄,藝術本身的復興仍然是未知數。
所以,遺產的復興從根本上依賴于藝術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依賴于某種藝術家的“氣質”。所謂藝術家氣質者,就是對遺產中的價值最為敏感的人;而所謂藝術家者,是不僅對這種價值敏感,而且能激活價值、在新的情境中有所創造,從而延續了價值者。這就是古人所謂的“腹有詩書氣自華”。所以,遺產的再生依賴于被價值所感的人,至少是好之者和樂之者,而不是站在價值之外的無動于衷者,比如管理者和研究者。因為這兩種姿態,都設定了與遺產中所涵價值的距離。當然,如果管理者和研究者亦能感受、尊重種種遺產中的價值,一個社會中渴慕價值者日眾,塑造出溫柔敦厚、廣博易良的藝術氛圍,則確有助于藝術家的誕生和遺產的復興。
四
當然,這樣說也不是將遺產的復興寄托于渺茫的天才的降生。因為天才也不是渺茫地降生出來的。不如說,天才不過是將價值的召喚、內在的召喚貫徹到底的那些人。所謂不瘋魔,不成活,藝術家異于常人者,正是由于他們將這些價值貫徹到了甚至不合常情、不正常的境界。但這種堅守也不應是出于外在的理由和責任。藝人常說“藝大于天”,那首先是因為他們在藝術中發現了自己值得堅守的內在的天命,這樣他們才愿意克服“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艱辛。所以,對于非遺而言,首先是藝術家在拯救自己,傳統才隨之甦生。而且,這種投入,根本不是一般所謂的匠心——沒有緣由的匠心。因為匠心不是外在的功夫,而是內在的救贖。匠心不等于苦心,奴隸再辛勞也不會有匠心。因為藝術的本質應是成就生命,成己以及成人。
而且,藝術的成就不單單需要外在的鍛煉,更需要內在的磨煉。這種磨煉也不只是痛苦,而是真正的喜悅。但是,生活的痛苦往往是成就藝術和藝術家的必要的催化劑。真正的藝術誕生于困頓,古人早就知曉了這其中的悲愴的玄機。所以司馬遷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詩人里爾克則說,“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因為只有當生命沉淪到命懸一線,藝術——作為拯救才能迸發出異常的力量。所以,讓大師成為大師的,往往是那些意外的、無人愿意遭受的艱難悲苦。
許多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不同領域的大師,其命運軌跡往往有著極為驚人的相似。比如天賦異稟,少年成名,中年遭遇波折,經年困頓,而到暮年往往藝術更上層樓,以至爐火純青,正如杜甫所謂“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秦腔界被譽為“小生泰斗”的任哲中先生,就是如此。因為中年演出頻繁,任先生的嗓子變得沙啞,又經社會動亂,精神更遭到了很大的傷害。然而復出后的他,卻以誰也學不了的蒼蒼之聲,使得《周仁回府》終成絕唱。1995年先生在西安去世后,據說吊唁隊伍致使交通堵塞,甚至喜歡他的觀眾從咸陽組成百人的樂隊,前往表達哀思。正如當時有媒體以“梨園至情”稱頌的,任先生正是以深情投入藝術,進而感動萬千大眾,并成就了秦腔藝術的高峰。
非遺作為藝術,就是如此悖論、悖情、悖理,它是無法在安穩、安全的位置去保護的。在韓國導演林權澤描寫朝鮮傳統說唱“板索里”的電影《悲歌一曲》(1993)中,有這么一個情節,師父為了讓女歌手成為最優秀的“板索里”演唱者,而不惜弄瞎了她的眼睛。導演在2005年重拍了同題材的作品《千年鶴》時,又保留了這一情節。這自然是一個寓言,一位資深的電影藝術家也深諳的寓言,但這也是一個危險的寓言。因為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危險,它要求人放棄某些現世的安穩才能實現——必須首先失明,然后才能看見。林導的這兩部作品所涉及的都是韓國傳統藝術在當時(1950年代)的困境與藝術家的悲情堅守,其話題一如中國當下的流行輿論,比如電影《百鳥朝鳳》。但內里的邏輯值得深究。從表面看,這些民間藝術家的困境是由于傳統與現代的張力;再往深里看,是吃飯與藝術之間的兩難;但在根本上,是人性在流浪與回歸、凡俗與神圣之間的永恒跌宕。若不敢臨危涉險,就無從得見山高水長。沒有現世安穩的位置,讓人可以輕言藝術,輕言非遺,輕言保護。而能輕易保護的,一定不是最偉大的藝術。
五
非遺所謂無形者,正在其為道,而不是器。老子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所以,不可以為器之法來“為道”。當然,“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朱熹),但能保護的,始終是器,而不是道。因為如上所論,為道之途,其艱辛如是,悖論如是。
而如果沒有這種悖論的自覺,沒有投身于非遺之內在價值的勇氣而昌言保護,注定是一種裝點門面、捕風捉影。今天的非遺,多出現在旅游的場合。這不啻是一種寓言。游客式的非遺愛好者,不過浮光掠影,驚嘆一番而后轉瞬即忘。這還無關緊要,如果管理者和研究者以保護心態從事非遺事業,其結果注定是南轅北轍的。可能資料增加、活動頻繁、研究繁榮,非遺之精神卻不見得有所弘揚。當然,如果管理者和研究者,至少能識得遺產之價值,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盡心保護非遺之物質載體,虛己以待來者,也堪成就一樁謙遜而平實的事業。最可怕者,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又指點江山,無畏大人,只能為真正的事業徒增障礙而已。
總之,如果遺產是個小于我的概念,那么遺產確實可以保護,但需要一個價值上的理由;如果遺產是個大于我的概念,那么它就是價值本身,我則無法置身其外予以保護。價值層面上的遺產,如同孔子所講的禮,對我而言是“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它要求我們的內在轉變,而容不得我們旁觀取舍。更進言之,得道者,必將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在常理上是人所唯恐避之不及的。如此焉能輕言保護?不知其中險峻,而試圖不動聲色地實施外在保護,要不就是買櫝還珠,寶山空回,要不就是附庸風雅,葉公好龍,終與遺產之精神相隔膜。
胥志強,文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