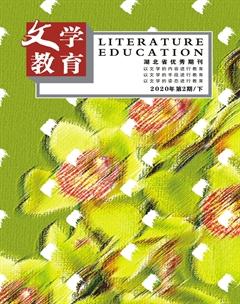逍遙莊子逍遙游
包翠萍
莊子的思維在曠野之外的一棵大樹下無所事事地漫游。“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在溫暖的陽光下做著化蝶的美夢,沉迷于“到底是莊子夢中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夢中變成了莊子?”這樣有趣的思索之中;或者坐在一個用奇大無比的葫蘆做成的小舟里在江湖中飄搖。
于是乎,見識了一條叫鯤的巨大怪魚悠閑自得地游弋在浩渺無邊的大海。這怪魚是如此之大,也許動一下都會翻起巨大的波浪,可是因為有廣闊無邊的大海和深不可測的海水承載,大鯤可以游得無比的愜意和舒適。大鯤轉化為大鵬之后,憑借著大風的力量,翱翔于九天之上,“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大鵬在海運之時都要飛往南溟:“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這是一幅多么壯觀的景象,浩渺的天空里,大鵬憑借著風力極力舒展著自己的羽翼,先是“水擊三千里”,然后是“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在振翼的同時探索著宇宙的浩闊,猜測著這天地到底有沒有盡頭,從天上望地下,那蒼蒼的顏色是不是天地的正色。這哪里是大鵬,分明是他不著邊際的狂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這樣奇特靈動的語言,這樣瑰麗多姿的想像,只屬于逍遙的莊子。這是一種十分愉悅的逍遙,然而這種逍遙受到了自然物質條件的束縛,受水和大風的制約,不能算作逍遙的極致,只能算作相對的逍遙。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莊子認為這是世人的成見。因為他覺得“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意即像大年之大年的彭祖,不知自己本性的“眾人”卻非要去“匹之”,這不是很可悲嗎!
列子御風而行,飄飄然很是快樂,走了一旬又五日,然后回來,這在精神上已是很高的逍遙了,但是還需要憑借外力。只有到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的境界,才無可借待,可以任意逍遙。“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則是一個人內心修持脫離了功利枷鎖,不為外物左右,超出凡俗而漸漸與道相合的境界。“而宋榮子猶然笑之”,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自得,表現出了站在高處俯看眾人在名利之間爭持的不屑與志得意滿。即便到了這樣的境界――不為形體、功利枷鎖束縛,還不能算是逍遙的最高境界,還有需要樹立的,即從“有待”到“無待”。
怎樣才能無待呢?“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無己才無所待,無功才無所依,無名才無所求,眼中無物,目中無人,心中無己,心便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虛室,虛室可以生出光明,由此洞察萬物,生命的意義也便在這里顯現出來了。“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并非實有其處,只不過是我們在精神境界里創造的一片空明,以心的空明游于無窮,達到自由自在的理想境界。所以,真正的逍遙還要注重內在的修行。
堯讓天下于許由,一方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盡,思退位讓賢;另一方不貪圖名利,認為“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表現的就是一種不貪圖人世功名、不為功利枷鎖束縛的豁達、淡泊。“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 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使自己的精神境界突破凡俗的束縛,不以天下為事,最后與自然融合,與宇宙同化,達到一種極盡逍遙的境界。個人修行達到這個境界,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當他神力凝聚之時,可以做到任何想做的事:萬事萬物都傷不了他,也不能動搖他堅如鐵石的心志。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所害,”有什么困苦的呢?“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只有任其自然,隨變是適,無乎所待,以游無窮,“無己、無功、無名”這才是逍遙的境界――極致的逍遙。
飄飄天地間,隨風任逍遙,惟莊子是也!
(作者單位:甘肅省岷縣第三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