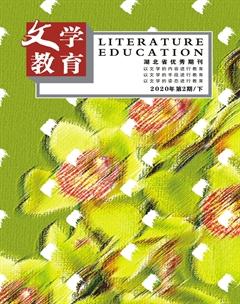分析《羅曼蒂克消亡史》之逃離
鄭世琳
內容摘要:通過分析《羅曼蒂克消亡史》,筆者發現該片建構出了一場又一場的逃離。本文力圖通過內容與形式雙層維度的探析,并且以《羅曼蒂克消亡史》之內的細節、整體作為具體文本,之外的程耳其它作品作為廣闊坐標系,以及創作者的歷史背景作為深入途徑,加以證明。并表達了對程耳電影非常規敘事結構,在多部影片中重復使用,心意漸不足,易最終淪為程耳式常規套路的擔憂。
關鍵詞:《羅曼蒂克消亡史》 逃離程耳 非線性敘事 套作
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用典雅精致的氣質建構出一場又一場的逃離,無論內容,還是形式。后文將對此展開論述,并希冀著能對未來的中國電影研究有所啟發,有所幫助,且有所裨益。
1.內容
首先,《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每一個人物,每一條敘事線索都蘊含著渴望逃離,或正在逃離的內容。
人物方面,小六在逃,她想與王先生離婚,逃離無愛的生活,期盼著“掙脫這種藩籬去追求追尋自己所謂的真愛”①,因而她會對陸先生輕聲訴說道:“這樣的日子究竟有什么意思?那么多人,到處都是人。有沒有人少的地方呀?你帶我跑了吧,就我們倆個。”“回去跟老板講一講,放過我吧。”婚還是離不了,她就用招搖過市的花癡,四處留情的風流,十三點來象征性逃離行尸走肉的無愛婚姻。最后小六終于在茫茫月色中離開了上海,卻中遇變故陷落到了無盡的黑暗囚牢里。民國三十年,隨著一扇又一扇打開的房門,小六拼命地跑,拼命地逃,終于離開了那座囚禁她七年光陰的密室,回到了地面,回到了她早已認不出模樣的上海。在內心深處的“本我”②層面,陸先生也是想和小六一起逃的,只是他的身上負著太多的責任,他逃不了,“我要照顧的人太多,我沒有辦法隨心所欲,我沒這個命。”時代的風云變遷里,陸先生也確實在歷經著一場又一場的逃離:因日軍屠門,從上海到香港;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從香港到重慶;因解放戰爭,從上海到香港。而渡部也是想逃的,他想逃離這種偽裝到人格分裂的間諜生活。雖然“他終年質地考究的長衫,說著地道的上海話,跟滬上時髦的中產者一樣又是喝茶又是泡澡堂子,經年累月,再看不出日本人的樣子。”但他從心底里確實更喜歡日本,更喜歡日本菜,卻不得不假裝喜歡上海菜,喜歡上海。他早已厭倦這種生活,渴望“掙脫束縛”③,即使以死亡的方式,所以當小六拿槍指著他時,他會那樣若無其事,淡定從容,畢竟死對于他何嘗不是一種解脫,一種逃離。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時,渡部終于想逃離戰爭了,“怎么會走到這步田地?從來沒有希望過戰爭會結束,從來沒有希望過能夠活下去,現在我卻想活下去,你能去幫我找到兒子嗎?把他們帶到日本的橫濱,我在那里有房子,有土地,可以種莊稼養活你們。等這一切結束之后,我會想辦法去找你們。”吳小姐也想逃,起初她想用鼓勵丈夫演戲,營救丈夫的方式逃離為妻,為明星的尷尬處境。被戴先生看上之后,她退回鉆戒,拒絕游說,挽留丈夫,努力想逃離金絲雀般的豢養。在歷經三年的幽禁之后,1945年,隨著戴先生飛機墜毀,她終于逃離了禁錮,能放心地說:“大概是不喜歡這個地方,所以不想吃。喜歡上海,所以想吃上海菜。不喜歡重慶,所以不喜歡吃重慶菜。”管家王媽在逃離中被槍打傷,終究沒有逃亡成功,但她用死前體面尊嚴地解鎖,端坐,象征性地逃離了暗殺。小張十幾歲一個人劃著只小船,從貧窮的寧波逃到了上海。他渴望逃離貧寒的底層,所以老板的女兒成了他的獵物,他處處小小維護,不動聲色地打動著芳心,并試圖用“只要有感情,丑的沒錢的都沒關系”的話來騙取老板的信任。生命的最后,他逃出了車廂,試圖換取王媽的逃生,最終身中數刀而亡。在程耳所寫的小說集《羅曼蒂克消亡史》里,童子雞最終拋棄了妓女,“他擺了擺手,打發卡車趕緊開走。”④但影片卻特別刪去了這樣的殘酷,將故事定格在“我養你”的溫暖諾言處,逃離了羅曼蒂克的徹底消亡。
電影里的喝茶也喻指著打斷,成為逃離的“能指”⑤。比如開場陸先生與周先生的談話中,陸先生想讓周先生攤牌,但周先生就是不承認,一副油鹽不進的樣子,“綁架的事真不是我們做的,您說讓我怎么幫您?我可以發誓。以我太太的名義,以我母親的名義。”陸先生知道他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就直接用喝茶打斷了不悅的談話,逃離了禮,開啟了兵。再比如當日本軍方表示想與王、陸、張合作開設東亞共榮銀行時,對合作絲毫不感興趣的陸先生再一次用喝茶進行了打斷。而當張先生有意想與日本軍方合作,“你剛剛講的這個股份,是多少啊?”陸先生再次說,“喝茶。”以此符號來對合作話題進行阻隔,斷離。
而且本片有去歷史化的傾向,影片中很多人物都有歷史原型,但創作者又逃離著歷史原型,比如將他們的姓改掉,名抹去,卻又使姓的韻母部分相同,比如“陸先生”與“杜月笙”,“王先生”與“黃金榮”,甚至“吳小姐”的“吳”,與“胡蝶”的“胡”用滬語念起來是同音的。這種在歷史原型與藝術虛構間的雙向逃離暈染出了曖昧的浮生若夢。
2.形式
影片所蘊含的逃離氣息不僅彌漫在內容層面,也同樣融合在形式層面,使內容與形式構成內在呼吸的勾連。
電影的重點配樂逃離了慣常的上海片配樂,沒用《夜上海》《玫瑰玫瑰我愛你》《天涯歌女》等,反而用了兩首英文歌,《Take Me to Shanghai》《Where Are You,Father》,卻由此流淌出一種別致的優雅。此外,該片的配樂明顯過多,有些地方甚至根本不必要,比如殺周先生之前的背景配樂,再比如童子雞走向妓女房子的那段音樂等,偏離了適量。
《羅曼蒂克消亡史》雖然在類型上屬于黑幫片,但它又逃離了很多黑幫片的經典元素,比如“固有的混亂空間與影片快節奏”⑥等。《羅曼蒂克消亡史》整體節奏優雅舒緩,仿佛一首宛轉流長的抒情詩。比如荒野里去往蘇州的小六,落寞,悵惘,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姿態。這是渡部的視角,他在觀察著身旁這個女人,靜靜地,氣氛緩慢而微妙。而影片的主角陸先生,更是始終氣定神閑著,連在日本餐廳遭遇襲擊,也是在用慢鏡頭呈現他的離去,呈現槍戰,絲毫不見以往黑幫片槍戰的快速剪輯。這種淡然如煙的抒情風格在《邊境風云》中就已顯露。黑幫片歷來的空間造型多為凌亂,而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空間則以整齊為主,比如影片開場的那段城市俯拍鏡頭里,一座座整齊有致的高樓安詳排列著。還有影片中大量的對稱性構圖,比如車內各居一側的陸先生與小六,王媽游說吳小姐的對話,妓女與童子雞的餐桌對談等。這種“二元對立”⑦式的整齊對稱甚至出現在影片段落間。比如鏡頭俯拍陸先生回到滿門被殺的家中,與鏡頭再次俯拍若干年后陸先生走過荒涼破敗的公館。其實在程耳的其它早期電影中,就已經常出現這種對稱,比如《第三個人》里,肖可向林先生傾訴,與何偉向肖可傾訴構成首尾對稱。可以說,這種舒緩、整理的處理方式已經成為程耳的習慣,也成為了他逃離黑幫片類型因素的有效路徑。
就連該片的劇情介紹都在逃離著常規,“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輪船,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車。沒有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待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過是下意識的拖延。不久他就死在香港,死前再沒有值得記述的事件或說過的話,他基本沒再說話,這沒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終于走向自己的沉默……”
其它方面,如取景,這部呈現上海三十年代氣質的電影并未在上海取景,完全是在北京搭棚取的景,卻不經意間勾勒出一種疏離感。該片簡化畫面,甚至避免拍攝群眾演員,以此來讓畫面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是有腔調的,有姿態的。依據第二電影符號學,電影制造銀幕幻覺的前提之一是隱藏攝影機的存機,因而傳統電影的成規之一就是“演員決不應當看觀眾=(攝影機)”⑧。但《羅曼蒂克消亡史》卻多次出現演員凝望觀眾的畫面,比如童子雞俯視坑里的周先生,小六演戲時批判博愛,胡小姐和丈夫最后的談話等,由此逃離了銀幕幻覺世界的封閉與自足,形成了獨特的間離藝術,喚醒觀眾的清醒思考。此外,《羅曼蒂克消亡史》后現代的拼貼敘事結構明顯逃離了傳統線性敘事方式,挑戰著普通觀眾的觀影習慣,違背著常規,形成“一種思考”⑨。
綜上,通過從內容到形式的分析,并且以《羅曼蒂克消亡史》之內的細節、整體作為具體文本,之外的程耳其它作品作為廣闊坐標系,以及創作者的歷史背景作為深入途徑,本文得出結論:《羅曼蒂克消亡史》建構了一場又一場關于逃離的敘事美學,輕煙裊裊,如夢,似幻,亦似花。
但筆者也不禁隱隱擔憂,擔憂程耳的電影敘事結構走向僵化,甚至套作。程耳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之前的所有作品,從《犯罪分子》,到《第三個人》,再到《邊境風云》,都是這樣的非線性碎片敘事。這樣的敘事,《犯罪分子》時期,初看驚艷,但當導演一再重復這種非常規敘事,心意流盡,這種非常規敘事,也易成為一種程耳式常規敘事,甚至淪為套路,再難散發出羅曼蒂克式的才華,再難燦爛如初。
注 釋
①馮宣凱.有差別,又沒差別評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7(01):24
②[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車文博等譯.弗洛伊德文集[M].長春出版社,2010,第125頁
③李盛.精致的囚籠——評《羅曼蒂克消亡史》的敘事美學[J].南腔北調(周一刊),2017,(2):26
④程耳.羅曼蒂克消亡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第75頁
⑤[英]特倫斯.霍克斯著,瞿鐵鵬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第16頁
⑥張懷強,李倩. 程耳電影研究:從形式到風格[J/OL]. 四川戲劇,2017(11):111[2017-12-26].http://kns.cnki.net/kcms/de
tail/51.1087.J.20171213.1414.052.html
⑦[美]恩伯(Ember,C.),恩伯(Ember,M.)著,杜杉杉譯.文化的變異——現代文化人類學通論[M].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頁.
⑧[法]克里斯蒂安.麥茨著,王志敏譯.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第59頁.
⑨程耳,郝建.《羅曼蒂克消亡史》:復雜敘事、時代畫卷與類型對話——程耳訪談[J].電影藝術,2017(02):68.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