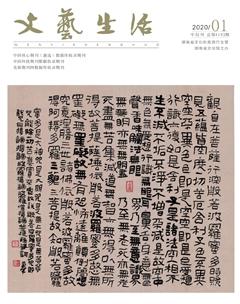《苔絲》中的神話原型解讀
余佳遙
摘要:《苔絲》是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后的小說家”托馬斯·哈代創作的著名小說,小說講述了美麗純潔的少女苔絲曲折悲劇的一生。從人物設置到結構安排、主題升華無不顯現了《圣經》中神話故事的影子,不同時代的人們都能從書中找到契合與共鳴。本文從神話原型理論視域對《苔絲》中的人物原型及價值進行探討。
關鍵詞:神話原型;苔絲;人物塑造
中圖分類號:1561.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02-0063-01
一、神話原型批評理論
神話原型批評理論起源于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是二十世紀最具活力的文學批評流派之一。神話原型批評最有價值的是把“原型”這一角度引入了文學批評領域,擴充了文學批評的方法。在這一視域下可以把作品的主題、人物塑造、結構等放到廣義的文化背景下進行探究,探尋作品的神話根源。人類學家弗雷澤闡釋了眾多的神話和宗教儀式,發現這些不同地方形式各異的神話和儀式的本質都是代表生命的循環,人們希望通過干預自然實現生命延續的愿望。而這些神話和儀式中所展現的死亡和復活實際是在西方文學中普遍存在的原型。
二、《苔絲》中的人物形象神話原型探析
(一)苔絲——被撤旦引誘偷食禁果的夏娃
作者對塔爾波特斯奶場的描述和圣經中的伊甸園極為相似。伊甸園中有豐盛的花草果木,有知識之樹、生命之樹,有源源的河流,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原本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而塔爾波斯特奶場土壤肥沃、空氣馨香。佛魯姆河靜靜流淌,有群群的奶牛和遍地茂盛的牧草。苔絲覺得每一陣風都是一片欣欣的笑語,每一聲鳥鳴都蘊藏著歡樂。塔爾波特斯時常氤氳著霧氣,而安奇像陽光一般耀眼的存在。正如作者寫到“她只知道安奇在身邊,別的便是一片燦爛的霧。”安奇的形象和希臘神話中象征光明的阿波羅頗為相似。
伊甸園中惡魔撒旦引誘亞當和夏娃偷食禁果的情節在《苔絲》中也有對應之處。亞雷喂苔絲草莓、把鮮艷的玫瑰放在她采摘果子的籃子里,單純善良的苔絲一步步走進了亞雷設計的“惡魔圈套”。鮮艷的草莓就像伊甸園智慧樹上誘人的蘋果,在苔絲咬住亞雷拈著的草莓的那一刻就種下了她悲劇人生的種子。
夏娃偷食禁果她為此付出了代價,由美好的伊甸園貶入塵世,遭受了無盡的苦難。夏娃是女性純潔美好的化身,而苔絲原本也是純潔無暇的形象,穿著白裙在草坪上起舞的她仿佛是一切圣潔美好的代表。如果說苔絲在塔爾波斯特牛奶場與安奇的夢幻邂逅如伊甸園般美好,那她離開牛奶場并遭到新婚丈夫拋棄受盡折磨則對應了上帝對夏娃的懲罰。
(二)安奇——太陽神阿波羅
被眾人承認“福伯斯”的阿波羅在希臘神話中象征著熱烈和光明,作為帥氣美好男神形象的代表,小說中哈代對安奇的描寫也正是對應了阿波羅。傳說在阿波羅出生時有天鵝繞了七個圈,金色的光環環繞著他。安奇給苔絲的第一印象便是溫暖燦爛如陽光,他們相遇在五旬節游行的下午,哈代寫道“他們每個都有自己獨有的小太陽,曬著她們的靈魂。一種夢想,一種愛情,一種心思,至少一種渺茫的希望。”村里的女孩兒穿著白裙翩翩起舞,苔絲和安奇對視,希望之光縈繞著苔絲。
在阿波羅神廟的石柱上刻著一句話——認識你自己。這是阿波羅精神,也是安奇的人生箴言。安奇注重自我精神世界的構筑,他對未來有清晰的藍圖。這如同尼采所說的“夢境”一一一種精神的沉醉。“那個擠奶的女工,是多么鮮亮,多么純潔的大自烈女兒喲!”沉醉于自己精神世界的安奇用神話中女神的名字稱呼苔絲,在他心里,苔絲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女神形象。安奇苦苦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女性,絲毫沒有關注到苔絲精神上的痛苦。新婚之夜苔絲對過去的坦白讓安奇的幻境徹底崩塌,過于理想化的安奇無法接受女神形象的裂痕,促使他做出了拋棄苔絲遠走巴西的決定。把安奇和太陽之神阿波羅相聯系起來,可以更好的理解安奇的形象內涵。
三、《苔絲》原型移用的價值
哈代所創作的《苔絲》是對神話原型進行再創造的產物,人類遙遠的原始幻覺被喚醒。正如榮格所說“藝術作品的本質在于它超越了個人生活領域而以藝術家的心靈向全人類心靈說話”優秀的作品是集體無意識的體現。《苔絲》中哈代把小說中的人物和神話原型相結合,經典原型人物的典型性擴充了文本的時代價值,豐富了人物內涵。
重生主題多次在作品中得到體現,哈代讓自己的女主角一直處于“路”上,讓她的人生經歷了春夏秋冬也經歷了人生酸甜苦辣的波折。在神話原型的映照下《苔絲》的內在意蘊和深刻內涵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引起了讀者的共鳴,激發讀者的想象,文學價值和美學意義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現。
哈代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個批判家,運用自己豐富的想象力,以眾多神話原型為依托向人們展示殘忍而真實的社會現實,而神話原型則賦予了《苔絲》更強盛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李永燊.文學賞評[J].文學概論,2003.
[2]葉舒憲.神話一原型批評[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3]榮格.心理學與文學[M].馮川(譯).北京:三聯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