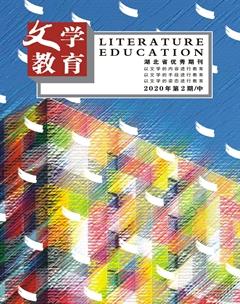《達洛維夫人》中女性身體與身份的塑造
內容摘要:本文從身體與身份的關系分析《達洛維夫人》中女主人公一角,發現克拉麗莎身份的消亡在于她放棄了通過經濟政治獨立而獲得話語權的途徑,最終讓達洛維夫人的身份禁錮了她作為獨立個體女主人公的身體。小說反映了伍爾夫對女性身體與身份的深刻見解,以及當時英國社會對女性主體性造成壓抑。身體既是生命物質存在的基礎,也是主體精神生活的場所,兩者相互依存。女性唯有在經濟上取得獨立,才能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生活。
關鍵詞:《達洛維夫人》 伍爾夫 身體 身份
維吉尼亞·伍爾夫是20世紀乃至今日極具影響力的英國女性作家。《達洛維夫人》是一部風格特色的長篇意識流小說,以克拉麗莎·達洛維一天內的生活做為小說背景,講述了克拉麗絲從準備晚宴、晚宴開始、到晚宴結束的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國內對《達洛維夫人》的研究成果不少,趙冬梅認為,“闡釋維多利亞時代男權制社會中女性的尷尬處境以及作者期望靠女性的撫慰力量拯救人類、實現雙性和諧境界的女性主義觀點”(趙冬梅,2014:130)。崔潔瑩則指出,在二十世紀初英國的父權社會里,上層社會女性的生活局限于家庭空間,宴會成為女性抗爭和退縮的場地(崔潔瑩,2016:136)。近年來,國外女性裸體抗爭不斷增加,人們的視野再次拉回到女性身體上,女性的覺醒強烈表現在對身體的認知上。本文試圖分析作品中女主人翁身體與身份的建構關系,理解作者對于女性身體與性別身份的關系問題所持的態度。
一.身體與身份的建構
《達洛維夫人》中,女主人公同一身體上刻畫兩個社會身份,一個是克拉麗莎,充滿活力的少女;另一個是達洛維夫人,議員理查德·達洛維的夫人。身體是人類的生物特征,屬于自然范疇,從一開始,個體分成雌雄兩性(Beauvoir, 1949:29)。而身份屬于社會活動范疇,人類通過各種社會活動,獲得一個或多個身份,這樣的身份自然而然地帶著社會性的烙印。
克拉麗莎成為了達洛維夫人,身份的轉換帶來責任的變化。女主人翁終日以舉辦聚會為自己的主要消遣活動,但背后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與建立丈夫的社會交際圈,維護丈夫作為國會議員的身份。表面上,舉辦聚會是上層階級的貴婦人的身份象征,但是其本質上還是為男性主導的政治話語服務,女性活動屬于從屬地位,失去了原有身份的獨立性。
克拉麗莎由天真浪漫的鄉村少女,轉變成上流社會的貴婦人,從自由不受束縛,到如今只能孤獨地活在光鮮亮麗的皮囊之下。達洛維夫人“得病以來變得異常蒼白”,“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輕,卻又難以形容地老邁”(Woolf, 1925:4)。“蒼白”、“老邁”,都形容人的生命接近末端,與過去“一下子推開落地窗,奔向戶外”(Woolf, 1925:3)的克拉麗莎不一樣,失去原有的生命活力。
小說中女主人公由克拉麗莎的身份轉換成達洛維夫人的身份,身體經歷生命常態變化,促成了角色的建立與演變,而身體與身份在發展的進程中也同時相互影響,女主人公角色研究進入到了二者相互影響的板塊。
二.身體與身份的影響
身體與身份是相互影響的關系,身體是身份的載體,身份的變化會在身體上呈現。當身份經過自然化、本質化的過程,會和身體融合為一體,身體變成了新的身份的外部表現。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的兩個身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身體的變化同樣有跡可循。在達洛維夫人自己的回憶和皮特·沃爾什的回憶中,年輕的克拉麗莎是充滿活力的,會和伙伴們談論詩歌文學,討論政治問題;會乘車到遙遠的地方,追求心靈的自由;會無所顧忌地考驗異性的感情,還能綻放自己獨特的魅力(Woolf,1925:54-59)。那時候的克拉麗莎正值花樣年華,女性生理剛剛成熟。因此,年輕的克拉麗莎獨立地在身體上和心理上擁有自己,作為一個獨立人擁有自己的個人身份。
女性更年期的達洛維夫人,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失去了本質上的女性特征,不完整的身體帶來了焦慮、絕望與痛苦。皮特·沃爾什的再次出現,讓達洛維夫人想起了從前,但是礙于身份,達洛維夫人并沒有向皮特顯露出任何的“異樣”,只是帶著高貴而又平庸的氣質,禮貌性地招待了皮特。達洛維夫人身上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靈氣,取而代之的是平庸的氣質。失去了女性特征的身體,達洛維夫人開始思考死亡和逃避。躺在床上的達洛維夫人像是躺在棺材里一樣,對于她來說,女性身體的缺失也是女性身份的缺失,達洛維夫人只想“不再畏懼太陽,不再畏懼暴風”,從現實世界中消失,企圖利用死亡來停止身體特征的丟失。相同的話語在小說中重復出現,體現了角色內心對生命意義究竟是什么的焦慮以及想要擺脫機械的現狀的急切。女性把自己的生命價值限定在生兒育女之上,完成了社會與歷史“賦予”她們的“使命”,失去了生存的動力,在達洛維夫人身上,沒有了生存的動力,沒有可以支撐自己走出自己的道路的實質上的幫助,即經濟獨立的基礎。達洛維夫人的身份是女主人公當下能夠生存的屏障。
在面對身體與身份的壓迫之時,女主人公的女兒,伊麗莎白,讓達洛維夫人再一次看到了自己身體的衰老。達洛維夫人嘗試著把希望寄托于和自己曾經一樣年輕的女兒的身上,企圖尋求一種“重生”的方法。但是達洛維夫人意識到通過自己女兒的身體來實現自救是不可能的,女兒伊麗莎白作為另一名女性同樣將面臨著女性身體特征的產生與消失,對于達洛維夫人來說只是重溫了一遍身體的變化,并不會產生任何不同的結果。一戰后的英國社會,尚未對女性身體放開束縛,女性身體仍然履行著社會的契約而充當男性的附屬品與生育后代的工具,通過女性來解放女性,獲得心靈上的寄托是無法實現的。因此,達洛維夫人想要“重生”,必須跳出身體的約束,重新定義女性身份。
三.身份的選擇
性別身份是社會性建構的,社會具有發展性,因此,性別身份可以被挑戰和被改造。伍爾夫的雌雄同體說,是尋找兩極的平衡,而不是屈服于任何一邊(Selden, Widdowson, Brooker, 1997:121- 149)。雌雄同體說體現了人類思想突破生物界限,陰陽相通,單一個體,雌性或雄性,滿足兩性融合的心理需求。《達洛維夫人》中,究竟是否是尋找平衡,需要進一步分析。作為女性角色達洛維夫人的對應男性角色,小說用了相當的篇幅描寫了退伍軍人賽普迪莫斯·史密斯這一角色,體現了小說發人深省的敘述角度。
小說中,與女主人公共時記敘的是一戰退伍軍人賽普迪莫斯·史密斯與妻子露西亞的故事。賽普迪莫斯由于狂想癥的困擾,因強制隔離,選擇跳樓自殺。賽普迪莫斯的描寫,或多或少反映了伍爾夫本人的生活經歷。伍爾夫精神受到困擾時,同樣在療養院接受“隔離治療”,禁止與他人接觸。
賽普迪莫斯的死亡對伍爾夫的命運結局是一種預示,而對女主人公反而是一種解脫和提醒。宴會上,聽到消息的達洛維夫人認為賽普迪莫斯也許找到了最后的自由,他不需要再畏懼太陽的炙熱照射,不需要再畏懼暴風的猛烈吹打,而是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庇護所。在思考了生與死的問題之后,達洛維夫人隨即回歸到了宴會中,但是對于宴會上討論軍人自殺的消息感到不滿。達洛維夫人心理上允許自己思考賽的死亡,但是在宴會等公眾場所談論有關政治的問題不是女性的“正當行為”,這是當時英國社會女性身份的另一種表現。當時英國社會的女性,已經把政治話語權讓給男性,達洛維夫人表現出了當時典型的上流社會女性的“修養”,在這一層面上,達洛維夫人的女性身份已經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內化為他者。
盡管達洛維夫人明白自己身體內的獨立精神正在一天天地腐爛、消失,但是作為女性的她,在英國籠罩在一戰過后的巨大陰影中,基本上無法實現自我獨立。一戰后,人們物欲的膨脹,追求金錢享受的欲望遠遠大于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皮特的到訪喚醒了達洛維夫人內心沉睡的自由向往,但高居上流社會的身份讓達洛維夫人妥協。小說的最后以賽普迪莫斯的死亡作為高潮,作者試圖用身體死亡來替代達洛維夫人思考的死亡,從而讓達洛維夫人得到一種救贖。女主人公選擇了達洛維夫人這個身份。
身份的選擇體現女主人公失去了主體性。達洛維夫人沒有選擇死亡來結束思想的禁錮,重回上流社會中,這種無力感來源于當時社會對女性的壓迫,甚至達洛維夫人自身都沒有意識到物質上的追求早已超過精神上的追求,固有的身份使得達洛維夫人失去選擇死亡的自主性。雌雄兩極的平衡沒有實現,《達洛維夫人》中的女主人公是時代的犧牲品。
四.結語
《達洛維夫人》表達了當時英國社會對女性主體性造成壓抑。身體既是生命物質存在的基礎,也是主體精神生活的場所,兩者相互依存。女性唯有在經濟上取得獨立,才能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生活。。女主人公的不斷掙扎與妥協,暗示著女性受壓迫下渴求自由的真實寫照。男性主導的話語模式,使得女性無法真實地講述自己身體的體驗,進而無法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女主人公最終選擇了達洛維夫人的身份,禁錮了克拉麗莎的身體。女性身體與身份的建構對女性角色的研究帶來不一樣的視角,從而對女性角色以至女性文學有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參考文獻
[1]伍爾夫著,達洛衛夫人[M].蘇美,孫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1-185.
[2]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25-76.
[3]劉巖,馬建軍等編,并不柔弱的話語——女性主義視角下的20世紀英語文學[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23-25.
[4]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5]Goldman, Jane.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M]. Shanghai: Shanghai Foriegn Le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作者介紹:許田鳳,廣東財經大學在讀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