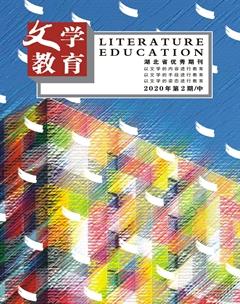淺談《溜索》中的風流
內容摘要:阿城的《溜索》作為新筆記小說《遍地風流》中極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以客觀、平靜、原生狀態的敘述口吻,以簡潔直白不事雕琢的文字,以一種潛隱了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視角,描摹了相較我們遙遠的偏遠土地上所發生的世俗中的人和事,于其中蘊藉著極具陽剛和野性之美的民族民俗之美。
關鍵詞:阿城 《溜索》 風流
阿城在七十年代流浪于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時,隨手寫下了一些文字,有關一些情緒、場景、和對一些人物和事物的印象,正是這些簡短的文字,匯聚在一起向我們展示了各個土地上不同的風俗、風貌與風度,盡顯中國大地之別樣風流。部編版九年級下冊中的《溜索》一文便是選自阿城的《遍地風流》,因此,文本將從其中的三重“風流”來詳細分析《溜索》一文中的豐富內蘊。
一.物之風流
《溜索》中寫了很多物象,有人物,一是位于顯處的剛強精悍的馬幫漢子們,一是位于隱處的敘述者;有動物,有勃發矯健凌厲的雄鷹,有靜如偉人傲然的馬,也有抖抖索索的牛;有景物,奔騰呼嘯森氣凜然的怒江,萬丈陡峭的崖壁和峽谷,邈遠的天;有風物,一直隱隱悶悶的雷聲,慌慌后復郎朗的牛鈴,還有堅若磐石的索……
悶雷聲和牛鈴聲貫穿全文始終,從溜索前初聽雷聲的不在意,到疑惑,到明了原來這悶雷聲并非天公作響,而實則是自己萬丈壁頂下那滾滾怒江敲擊崖壁所喧騰上來的聲音,方覺驚顫和抖索,再到戰戰兢兢的過溜索期間,由于過分的驚遽和身臨其中,不復覺察到雷聲,直到終于過了溜索,吊著的心松了下來,方又覺出悶雷一直響著,這一隱隱悶悶的雷聲,將整個事件的過程、所有的人物與動物的行動與表現,都籠罩在一個及其險峻的環境中,一個極其緊張戰栗的氛圍與基調中。而三次牛鈴,則分別對應著不同的發展過程和人物心理情狀。第一次寫牛鈴是馬幫們快到怒江山口時,鈴鐺們慌慌響起,作者用筆及其簡省,一個“慌慌”使我們仿佛能透過這個雜亂的聲音,看見牛隊因遭遇了漢子們“連珠脆罵、拳打腳踢”而慌亂躁動起來的情貌,又似乎隱喻著一絲不同尋常的使人心中不由惶惶的氛圍,為接下來的情形作了一個小小的鋪墊。第二次寫牛鈴,是在即將過溜索前,漢子們對著絕壁吼叫著,回聲撞擊著,在高聳萬丈的崖壁、滾滾喧騰的怒江構成的邈遠宏闊的自然之前,顫顫地、向扯在兩岸石壁間細細的索移去的馬幫,是顯得如此渺小,如此微弱,牛鈴隨著步伐的移動,一步一響,如擊在心上,之前慌亂嘈雜的鈴聲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步一響如此清晰而緩慢的牛鈴,恰恰襯托出這一步一步踏的多么的顫巍巍,多么的令人心生懼怕。第三次寫牛鈴,是馬幫們全體過了溜索,因溜索而皮肉亂抖驚惶不已的牛們終于歇整好,重又上了馱,這時的牛鈴是“郎朗”的響著,從這郎朗的響聲中,現出牛們離開這驚險之地的急切心情,而這也正是潛隱著的敘述者內心想迫切離去的心理的映射,除外,這“郎朗”還有絲清脆悅耳的意味在其中,使得這整個氛圍和基調從之前的緊張驚險稍稍變得輕松下來。
作者在描寫人物和動物時,可以發現作者所用筆墨繁省的不同,寫鷹,僅用了三句話,僅用了數個動詞“旋”“歪”“扎”等以及將鷹與瘦小的漢子構成互襯,顯出了鷹和人面對這一波瀾壯闊卻又奇險詭譎的大自然,同為無所畏懼的翱翔沖擊之態。既是對大自然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食物鏈的彰示,也是對于對此情狀波瀾不驚淡然自若的漢子們的贊意。而寫牛們過溜索,作者則相對花了較多的筆墨,既有對牛的形態舉動的正面描寫,如“兩眼哀哀地慢慢眨”“軟了下去”“失了神”“皮肉瘋了一般抖”“嘴咧開”“叫不出聲”“屎尿盡撒”等,細致而具體,極其觸動人心。
寫人也是如此,寫首領和漢子過溜索,只用寥寥數筆,便將他們的那種勇猛矯健、無所畏懼、硬朗剛健的情態勾勒至盡,他們沒有過多繁冗的語言與對話,沒有過多的心理情感的流露,只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一聲笑,一只煙便可見他們之間的默契與和諧,他們對于險峻而危及四伏的自然的適應與熟悉,這種淡然和鎮定,這種熟稔和從容,不由得讓我們想象是怎樣一種生活方能磨礪至此?而對于潛隱著的敘述者的描寫,也是花了較多筆墨的,甚至會覺得敘述者過溜索的情態和牛幾乎有異曲同工之處,“戰戰兢兢的”“僵著脖頸”“欲嘔”“慎慎的”“腿子抖得站不住”“肚子脹”“眼睛澀”這一連串的身體的自然反應與心理極度驚懼的渲染,
因此,在這組人物和動物的描繪中,馬幫漢子們和敘述者形成對比,鷹馬和牛隊形成對比,而鷹馬又和漢子們形成對照互襯,敘述者和牛形成對照類比,這樣的對舉不禁讓我聯想到,在我們傳統的文化語境中,鷹始終被視為是不受拘束搏擊長空的猛禽,而老牛則是一輩子賴以土地為生,體型敦實,行動遲緩,卻勤勉憨厚老實的勞動者形象,可過溜索,卻意味著它們被迫與四只腳一輩子踩著的堅實的土地分離,正如慣于踩在厚實土地上而從未騰躍于滾滾江水之上的敘述者一樣,兩者的驚惶可想而知。
二.事之風流
阿城的《溜索》屬于典型的新筆記小說,筆記小說往往多寫飲食起居,日常交往等一些不被所謂的“正規”小說所正視和納入的內容范疇,延續于筆記小說的新時期新筆記小說同樣取材“瑣”“小”“雜”,多記錄一些世俗瑣碎之事,而正是這些看似不入流的世俗瑣事,才是在民族生活和精神里亙古存在著,蘊藏著民族常存的長存的既普遍又恒久的心態世相,而這些民族文化素質與中國民族美學精神有時恰好構成一些內在的溝通和契合。
《溜索》一文記錄的便是不為我們普通人日常中所熟悉的風貌人情,雖然文章中并沒有寫明事件發生的地點與人物的具體身份,但是通過考證相關的資料,可以發現溜索多為過去生活在金沙江、怒江、瀾滄江一帶的少數民族所日常使用的過渡工具,這樣一群人這樣艱險的生活方式以及這樣的極具異域風貌的事件,是很難以在大眾化的文本中看到的,阿城則為我們展示了那不為我們所熟知的相較我們遙遠的另一些民族的生活與精神風貌,他們雖然生活的微渺,但卻以一種極具原始野性陽剛的氣魄存在著,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溜索已逐漸被現代化的橋梁所取代,但是溜索作為少數民族由來已久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他們改造自然和戰勝自然的象征,他們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精神氣質值得世代傳頌。這樣一種野性陽剛之美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青年們所缺失的。
三.言之風流
作為新筆記體小說,《溜索》一文的語言極具特色,首先是大量疊詞的使用,例如寫雷聲,多次出現“悶悶”,凸顯出聲音的沉悶,側面烘托出峽谷崖壁的高,和怒江水流的洪大。寫首領,“懶懶說是怒江”、“穩穩坐在馬上”、“緩緩移下馬”,一系列形容動作的疊詞與敘述者的“戰戰兢兢跨上角框”“慎慎地下來”“眼珠澀澀的”形成鮮明的對比,寥寥數語便勾勒出剛毅冷峻的首領和惶恐無措的敘述者的具體可感的形象特征。其次是短句的運用,使文章讀來急促,有節奏感,極具張力,非常巧妙地與整個文本驚險緊張的氛圍融為一體,短促的語言作為文學的一種形式,與其所敘述的充滿硬朗剛強氣魄的風物內容,相得益彰,熠熠生輝。
再次是文言句法的使用,這也是新筆記小說語言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諾埃爾·迪特萊在《冷靜客觀的小說》中評價阿城小說的語言是“非常精煉的語言本身接近非常文學性的古漢語”。
王蒙也評價阿城的語言是“美不勝收——口語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過‘土”,從《溜索》一文的語言來看,阿城的語言可以說的確是將多種不同風格的語言形式雜糅在一起而又顯得十分的統一和諧。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之一,我認為便是作者用一種近乎古漢語但又并非古漢語的語言形式,以致形成一種文白間雜的風格,使得即便是口語的語言也讀來具有一種簡約蘊藉的古典美。例如敘述者在初見峽谷峭壁時的描繪“山不高,口極狹,僅容得一個半牛過去”,便極易讓人聯想到《桃花源記》中的“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雖然語言形式幾乎一致,但所描繪的風物和氛圍卻截然不同,使得語言在與傳統文言的悖反中更具張力。再如寫怒江的水流喧騰之貌,“隱隱喧聲騰上來,著一派森氣”,一個“著”字,極其儉省但又盡得風流。就如同潑墨畫一般,隨意的一個點染,便能感受到其中無比豐富的意蘊。
最后,總而言之,阿城的《溜索》猶如一幅寫意畫,寥寥數筆便傳盡了對象的神韻,他語言的精煉簡介恰恰是不事人為雕琢加工的痕跡,正是這樣寫意、留白、古典化的語言讀來耐人尋味,呈現出一種“言有盡而意無窮”的中國傳統美學風貌。
四.結語
阿城在寫給諾埃爾·迪特萊的信中談到筆記小說可以具有詩、散文、筆記和小說的特點,有大量的遺產可以繼承,同時又可以進行各種敘事實驗,例如節奏、語音、句法、視角等等,于是開始一段一段的寫《遍地風流》,作為新時期筆記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溜索》中的物象風貌、敘事風度與語言風格,仍有著無盡的待挖掘的別樣“風流”。
參考文獻
[1]阿城.阿城選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2]鐘本康.關于新筆記小說[J].小說評論,1992(06):14-19.
(作者介紹:潘雨菲,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學科教學(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