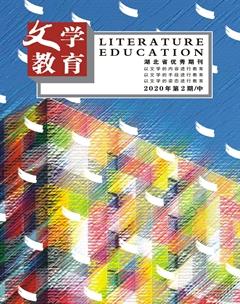制度化譯者的愛國倫理探究
高洋
內容摘要:制度化譯者具有“被贊助人”、“公務員”、“社會人”三重身份,這三重身份要求制度化譯者必須遵守愛國倫理,做出愛國行動。這種愛國倫理適用于國家翻譯實踐環境下,是政治要求和個人倫理訴求的統一。
關鍵詞:制度化譯者 愛國倫理
1.引言
如今,中國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與全球各國交往日益頻繁,國家翻譯實踐也在不斷增長,對“制度化譯者”的研究便顯得更加迫切。但縱觀中西方翻譯倫理研究,給予譯者愛國倫理這一話題的關注尚且不足。諾德的“忠誠”概念,切斯特曼的“服務倫理”模式似乎與之相似,但終究是西方學者立足于西方翻譯實踐的基礎上抽象歸納而得出的理論。中國的國家翻譯實踐屬于輸出型翻譯,夾帶政治目的,具有一定特殊性,而且中國的國家翻譯實踐下的“制度化譯者”與西方國家的自由譯者或職業譯者又大不相同。因此“制度化譯者”的愛國倫理與“忠誠”、“服務理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本文摸索性探究國家翻譯實踐中“制度化譯者”的愛國倫理,其意義也就不言自明了。
2.制度化譯者的愛國倫理訴求
“倫理訴求是人的眾多訴求之一,是人社會性的體現。當人按照某種行為規范行事而獲得外界認可時,人的倫理訴求便得到實現,其社會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李穎,2018)將倫理訴求運用到國家翻譯實踐活動中,可以觀察到不同翻譯主體(贊助人,翻譯機構、譯者、譯審等)的倫理訴求。倫理訴求以價值取向為基礎,國家翻譯實踐的倫理訴求反映的是制度化譯者對翻譯實踐價值的追求,制度化譯者的倫理訴求則是譯者在翻譯活動中遵循某種倫理關系規范,進行具有產生價值功能的翻譯選擇。制度化譯者是國家翻譯實踐活動中的翻譯主體之一,具有多重身份,這一特性決定了其在翻譯過程中所遵守的倫理關系規范也定然不止一種,所追求的翻譯選擇也必定具有不同價值。因此,對制度化譯者愛國倫理訴求的探討,便不得不剖析制度化譯者的多重身份。
制度化譯者具有“被贊助人”的身份。國家翻譯實踐由主權國家自主發起,具有較強的政治性、目的性和自利性,要求參與各方具有愛國的價值追求。制度化譯者作為國家翻譯實踐的翻譯主體之一,在接受國家贊助的同時,也受到政治約束,在這些制約下,制度化譯者必須處理好自身與國家的關系,遵守“被贊助人”與“贊助人”的倫理規范關系規范,考慮國家利益,滿足國家要求,實現國家目的,本著對國家負責的態度,做出每一個有利于國家的翻譯選擇。
制度化譯者具有公務員身份。這一身份會淡化其譯者身份,而國家翻譯實踐的性質在此時也更傾向于是一項國家任務,制度化譯者則變成了國家任務的執行者。在執行這項任務時,制度化譯者的一切行為選擇都會受到政治意識的影響和國家公務員行為規范的制約,而其中一條便是“維護政府形象和權威,遵守外事紀律,維護國格、人格尊嚴”。制度化譯者為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安全上的要求,選擇放棄選材,決定翻譯策略,裁定翻譯選擇,參與譯后編輯、譯本署名等原本屬于譯者的權利,甚至對某些原文的理解,都無權闡釋,還需向上級領導請示。既定的制度化翻譯流程也呈現出政治特征,譯者、譯審、最終裁定人之間也存在著行政級別上的差異。制度化譯者所有的譯者行為都與政治行為高度重合,變成極具政治意識的選擇。在行政體系中,制度化譯者將公務員身份視作主要身份,并以此身份為準繩開展相關翻譯工作。
制度化譯者具有社會人的身份。社會人最基本的一層解釋便是中國社會的一名成員。在中國社會,自古便有“忠君愛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如今愛國更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愛國主義既是一種意識形態,體現中國社會對公民的期待和規范,又是一種政治原則,表明國家對公民的強制要求。而生活居住在中國的公民,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沉浸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并接受著中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內容,愛國是制度化譯者作為社會人必然的倫理訴求。歷史上,翻譯一直與中國社會的興衰息息相關。佛經翻譯維護社會秩序,科技翻譯提升科學文明,五四期間的翻譯開啟民智,五四后期的翻譯奠基改革。在社會大背景下,翻譯本身的價值十分明顯,而譯者通過翻譯報國、強國所產生的價值也同樣不可忽略。與普通譯者相比,制度化譯者雖然受到諸多制約,但譯者身份使之仍然在語言性層面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面對當今時代西方對中國的歪曲理解和文化壓制,制度化譯者會不自覺產生將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使命感和通過翻譯報國、強國和興國的責任感,其社會人的身份也會驅使制度化譯者在翻譯工作中呈現出“尋求中華文化榮耀的譯者姿態”(汪寶榮,2018)。
3.制度化譯者的愛國倫理行為
制度化譯者供職國家機構,接受國家贊助,服務國家目的,是國家向外傳達聲音的話筒,雖然其譯者行為受到諸多制約,但這并不表明制度化譯者就是單純的“翻譯機器”,其“翻譯過程中的語言性選擇仍依賴譯者(任東升,朱虹宇,2019)。只不過,此時譯者的語言性行為選擇是在愛國倫理訴求驅動下,以表達中國立場、說明國家政策、展現社會風貌,弘揚中國文化、實現國家目的等為主要考量的愛國倫理行為,其所譯文本具有“明顯宣傳性質甚至濃重政治氣息”(同上)的特點。
3.1美化國家形象
由于政治制度和核心價值觀的不同,西方對中國的政治路線、中國執政黨、中國領導人都有一定的曲解,而且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長期受到西方霸權主義和西方話語體系的壓制,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被動局面,“他塑”國家形象的被動狀態,這往往會導致國家形象的失真,使中國失去有利的國際環境。面對這一窘境,中國主動出擊,通過國家翻譯項目積極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達中國聲音。作為“被贊助人”的制度化譯者,自然應遵守“贊助人”與“被贊助人”的倫理規范,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在國家翻譯實踐中糾正錯誤的西方認識,樹立真實的中國形象。
制度化譯者沙博理編譯的《中國古代刑法及案例故事》一書中,收納了許多古代斷案故事,有官員受賄錯判案,也有個人專權獨斷等封建社會的腐朽思想。為了避免該書的西方讀者將中國古代社會的狀況遷移到現代中國社會,對中國社會產生誤解、歪曲,沙博理在后序中提供了基于中國價值觀的解釋:“他雖然是老百姓渴望的清官。但他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崇拜權威和男權占主導地位的人際關系的另一種體現”(Shapiro,1990,272頁)。除此之外,還說明“近些年,現代中國已經開始努力清除封建思想在司法系統和整個社會中的殘余”(同上)。
在建國十七年期間的國家翻譯實踐中,有許多革命題材的作品,其中不乏反動派血腥暴力的情景描述和浪漫的情愛故事。“但過度的血腥場面及情愛描寫會縮小小說的讀者群、有損革命人物的高大形象,違背國家翻譯機構組織譯者翻譯革命歷史小說的初衷,譯文需要對其刪減或者雅化,使其更適合對外傳播”(任東升,連玉樂:2019)。這種“萃譯”方法雖然沒有說明具體發生在翻譯前、中、后哪個階段,但其理念仍然是制度化譯者在愛國倫理訴求驅動下可以做出的語言性翻譯選擇。
《習近平治國理政》(兩卷)的翻譯也體現了這一點。制度化譯者將其中一個標題——《“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記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翻譯為“Man of the People:profile of Xi Jinping,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這種譯法高度靈活,且符合目的語規范,但這一翻譯行為背后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有助于彰顯習近平的平易近人、親民的形象”(陳雙雙,2019)。《習近平治國理政》(兩卷)的翻譯使用了“異化、顯化、簡化、信息重組等翻譯策略”(趙祥云,2017),這也是制度化翻譯的一種新趨勢,制度化譯者的愛國倫理訴求也有了更廣闊的發揮空間。
3.2突出文化因素
韋努蒂(2008)曾指出“歸化”、“異化”是一種倫理態度或倫理效果。這種倫理態度或倫理效果體現在制度化譯者身上便是愛國主義行為。因為國家翻譯實踐的選材大多極具中國特色,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文化方面,中國都有自己的獨特性,想要在翻譯中保留本國特色,建構國際化與體系,讓國外讀者知曉中國、了解中國、愛上中國,便不得采取以英語為共核,以中國特色為依托的翻譯手段,強調原文本中所包含的中國特色文化。而具有愛國主義倫理訴求的制度化譯者,在國家翻譯實踐中承載文化責任,持有文化立場,進行文化比較、履行文化使命,并會采取直譯為主,兼帶意譯的翻譯手段,以求最大程度地做到文化翻譯保真,使譯文在譯語環境下具有較高的辨識度。這種做法既是響應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著重宣傳中國成就,大力弘揚中國文化,也是滿足譯者自身的文化榮耀姿態,將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文化輸出層面,自覺承擔傳播中國文化的重擔。
4.結論
制度化譯者愛國倫理存在于中國國家翻譯實踐的語境之下,產生于國家政治要求與譯者自身價值訴求的有機統一,作用于帶有功利性目的的外向輸出型文本。這一愛國倫理是國家翻譯實踐的核心倫理,是實現翻譯目的的重要保障,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助力,也是制度化譯者實現自身價值訴求的重要途徑。制度化譯者愛國倫理本身就帶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也屬于適合中國自己的譯學話語,其研究對當今中國致力于走向世界舞臺的國家戰略和中國譯學話語體系建構都有一定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陳雙雙.翻譯副文本對原作者的形象塑造——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譯本為例[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2.洪捷.五十年心血譯中國——翻譯大家沙博理先生訪談錄[J].中國翻譯,2012.(4):62-64.
3.任東升,連玉樂.《紅巖》、《苦菜花》萃譯比較研究[J].外語與翻譯,2019.
4.任東升.“萃譯”之辯[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8.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