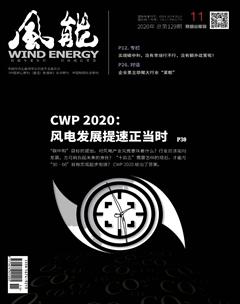打通海上風電“創新鏈”
孫一琳
今年8月,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發布《2020年全球海上風電報告》,預測隨著全球能源轉型步伐的加快以及更多國家進入海上風電領域,2020―2030年全球海上風電裝機容量將新增2.05億千瓦以上,海上風電在全球風電市場的占比會在2025年達到20%左右,為能源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關鍵支撐。
協同創新——海上風電的著力點
2019年,英國政府設定了到2030年實現4000萬千瓦海上風電裝機容量的目標,同時投入約720億英鎊(約合人民幣6231億元)用于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蘇格蘭則是發展海上風電的主要地區。目前,該地區有4.65萬余人從事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產業。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蘇格蘭地區成立了深海風電協會,以促進整個北部地區海上風電產業的發展,包括22家開發商、1家整機企業、375個供應鏈企業和相關協會、大學、港口的成員參與其中。除了深海風電協會,蘇格蘭還擁有海上風電協會和海上風電能源協會。蘇格蘭國際發展局投資部中國區總監趙莉表示,“無論是政府,還是產業,都投入了大量精力以保持海上風電行業的創新活力。”
挪威擁有100多年的海事以及造船歷史,并積累了超過40年的油氣開發經驗,使得這個國家對海洋工程有著極深的理解,從而為持續降低海上風電各環節成本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該國專為滿足海上風電開發需要而建造的安裝船,已經服務于20%~30%歐洲海域的項目,成為挪威發展海洋經濟的又一發力點。
在中國,海上風電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同樣為實現突破不斷展開創新。
整機企業利用整機架構設計與平臺化、模塊化快速降低成本;利用整機系統數字孿生與多目標的尋優,提升產品迭代速度;研發碳纖葉片,同時在超柔葉片方面研發出高升阻比、低噪聲的翼型,進一步降低發電成本;在智能控制技術方面,通過設計環境自適應控制、全生命周期疲勞控制,最終實現風電場發電性能的最優;在海上風電固定式基礎載荷方面,一方面,通過設計優化,突破現有基礎類型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通過精細化分析優化,降低載荷,做到系統最優。
隨著海上風電機組的大型化、水深的增加,海上風電機組基礎的重量也在迅速增加。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上風電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寧巧珍提出了5個需要突破的關鍵技術點:一是深水低頻單樁基礎設計優化方面,在地基剛度精確計算、樁長魯棒性優化、突破樁身D/t限制等方面實現技術創新;二是導管架基礎設計及制造工藝優化,鑄造管節點以及桁架模塊化設計方面進行創新;三是嵌巖及軟弱覆蓋層下新型低成本基礎創新,包括復合筒基礎、多筒負壓筒導管架基礎、單筒負壓筒基礎、摩擦盤基礎等優化;四是建立適用于我國環境條件和地理條件的設計規范;五是推進塔架與基礎的一體化設計,使整個系統形成閉環,通過精細化分析剔除設計中的冗余部分。
此外,未來可通過葉片疊放和塔筒立放等實現單船多套部件的運輸,降低成本。針對福建和廣東浪涌比較大的區域存在吊裝效率低下的問題,寧巧珍指出,研究適用于風電機組吊裝及基礎施工的風電安裝船自運自吊技術是提高吊裝效率的最有效途徑。為實現技術的應用,現階段有需求的港口應主動獲得相關部門和機構的建設許可,提供可插樁接貨的港口以及超寬運輸航道等條件。
金風科技對該技術展開了不同里程、不同設備套數以及用具的評估,據保守估計,它的應用可降低30%~50%的單臺機組吊裝成本。
創新是廣義的,除了圍繞技術和產品,還有必要進行商業模式與組織模式上的創新。以諸多整機廠商和開發企業的經驗來看,長周期乃至全生命周期運維服務的統一外包是目前提升風電場發電效率的有效合作模式。為快速推廣這一模式,寧巧珍指出,需要投資方和服務商盡快就相關技術標準以及合作分成標準形成明確的合同關系。
“當然,某環節的單一改變帶來的效果終究是有限的。”寧巧珍補充說,“只有集全產業鏈的廣泛創新,才能賦予行業以顛覆性的力量。我們需要思考全產業鏈上的創新如何進行有效組合才能達到效率的最大化。”
制氫——海上風電的下一個窗口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對現有的能源消費結構進行轉型升級是必然的趨勢。當前需要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提升全球各個經濟體的整體能源效率,將能源總消耗量控制在與2018年持平的水平;二是進行大量的電氣化改造,特別是推進傳統工業生產的電氣化改革,輔以清潔能源電力;三是推動清潔能源取代傳統化石能源。
彭博新能源財經風電分析師汪子越表示,氫能在這一過程中大有可為。可與氫能結合發展的能源種類眾多,絕不限于海上風電,但海上風電無疑是這一跨界技術的最佳合作伙伴。
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開始海上風電制氫示范項目的建設。荷蘭建造了全球首個海上風電制氫示范項目—— PosHYdon。在英國,——rsted公司的140萬千瓦Hornsea 2海上風電場將與Gigastack項目連接生產綠色氫氣,為英格蘭東北部的一家石油和天然氣精煉廠提供動力。德國制定了最新的海上風電制氫戰略,考慮在海上風電競標中指定部分海上風電場專門用于生產綠色氫氣。
海上風電制氫的成本居高不下成為這一綠色發展路徑尚未得到推廣的根源,但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制約因素”。未來,可再生能源電力制氫成本還有較大的下降空間。
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在不斷下降;另一方面,電解槽設備的成本在持續下降。以歐美市場為例,電解槽成本在過去的5年中下降了40%~50%。在中國,受益于較低的原材料價格、人力成本,以及較高的工廠利用率,這類設備成本的下降將更加明顯。另外,由規模化發展帶來的成本效應,也有助于推動未來氫能產業的騰飛。據估算,2030年,全球電解槽設備平均成本有望下降至少30%,2050年下降50%以上。此外,電解槽利用率也有很大的提高空間。
汪子越認為,未來10年內,全球仍需要約15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9807億元)的補貼,可再生能源電力制氫的成本才能降至2美元/千克(約合人民幣13元/千克)。這一補貼數額乍一看非常大,但實際上每年全球各國政府用于化石能源的補貼接近于它的2倍。由此看來,只要推進能源轉型的意愿足夠強烈,可再生能源電力制氫就能夠成為一個絕佳的選擇。
漂浮式——海上風電的未來
自2009年世界上第一臺兆瓦級漂浮式海上風電機組并網以來,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范圍內已安裝了6.6萬千瓦的漂浮式海上風電。全球風能理事會(GWEC)基于全球主要國家現有的漂浮式風電規劃預測,未來10年內將建造620萬千瓦的漂浮式海上風電項目,但2020―2025年的裝機容量將不到預測值的10%。從2025年開始,小型商業性的漂浮式海上風電項目會開始建設;2030年,漂浮式海上風電有望通過大型項目招投標而陸續開工并投產。可以說,走向深遠海代表著海上風電的未來。
DNV GL―能源首席執行官Ditlev Engel提醒,未來漂浮式海上風電將面臨來自技術、監管和競爭等方面的挑戰。在技術方面,涉及新型設備需要認證、應對極端天氣情況等;在監管方面,新興市場缺乏政府監管框架、輸電/電網容納量有限或老化、本地化占比要求嚴格等均值得關注;最后,還有與全球化和競爭有關的挑戰,包括對當地市場規模經濟合理性期望過高,以及沒有認識到需要靈活的全球供應鏈來實現規模經濟和度電成本的降低等。
在CWP 2020上,有眾多關于漂浮式海上風電發展經驗的分享,已經細化到各個環節,如在設計環節,漂浮式海上風電機組耦合設計面臨的挑戰,漂浮式海上風電機組模型試驗及驗證;在運輸環節,不同類型半潛型漂浮式海上風電機組拖航技術的優劣,以及海上物流管理及標準化認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