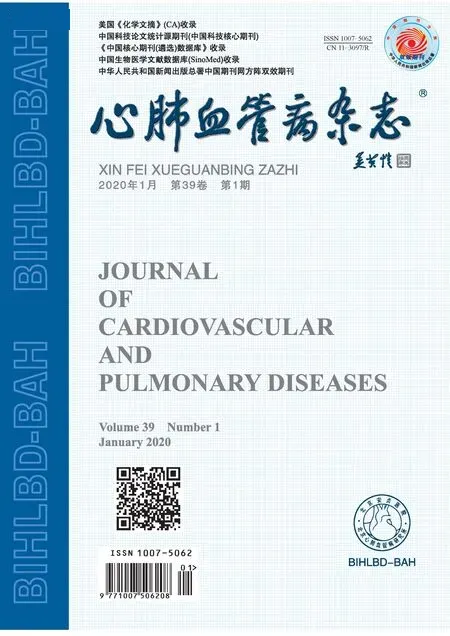二尖瓣脫垂與猝死的相關性研究進展
陳菲菲 趙誼昶 夏云龍
二尖瓣脫垂(mitral valve prolapse,MVP)是指二尖瓣瓣葉(前葉、后葉或兩葉)在心室收縮期脫入左心房,經典MVP定義為在長軸切面上單個或雙葉二尖瓣瓣葉在收縮期移向左心房>2 mm,且1個瓣葉厚度≥5 mm,目前MVP發病率約為1%~3%,男女比例相近[1]。盡管研究發現大多數MVP為良性,但MVP預后差異性較大,其中一些嚴重并發癥包括二尖瓣嚴重反流(mitral regurgitation,MR)、感染性心內膜炎、卒中和心臟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預后較差[2]。近期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某些類型的MVP與SCD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具體機制尚不明確,推測可能是MVP患者發生室性心律失常(ventricular arrhythmias,VAs)[3]所致,估計發病率0.2%~1.9%[4]。目前許多研究發現,惡性MVP患者具有一些特異性的危險因素,本文從發病率、臨床特征、超聲心動圖、心臟磁共振、電生理特性、危險分層、治療、預后等幾方面綜合闡述,以提高惡性MVP患者的檢出率,指導臨床醫生做出正確判斷及做好猝死預警。
1.MVP患者SCD的發病率
Framingham研究數據發現,1980年代總人群中SCD的發病風險為130次/10萬人/年[5];Hua 等發現總人群的SCD發病率由1990年代的94~97次/10萬人/年,逐漸減少至2000年代的42~53次/10萬人/年的,發病率下降可能與心肺復蘇的普及相關[6];而Han等研究發現,MVP中SCD的總發生率約為217次/10萬人/年,二尖瓣瓣葉冗長的患者SCD風險可能更高[7];Nishimura等估測,瓣葉冗長患者SCD發生率約為998次/10萬人/年[8];在弗拉明翰總體人群研究中,MVP患者SCD發生率為2.4%[9]。
2.前驅癥狀與臨床特征
MVP患者發生SCD前驅癥狀有心悸(58%)、暈厥(29%)、胸痛(31%)、頭暈(23%)和疲勞(8%),僅21%患者SCD發生前無任何癥狀。
多個研究總結發現,MVP患者發生心搏驟停(cardiac arrest,CA)或SCD的平均年齡為30歲,其中女性為28歲,男性為39歲;年齡-性別分布提示女性發生SCD集中在20~30歲,而男性一般在各個年齡段均有SCD發生[10];47%的患者發現SCD與自身壓力狀況相關,包括身體、情緒、駕駛、懷孕和住院等,可能與腎上腺素分泌升高、復雜VAs發生均相關,提示自主神經系統可能是MVP患者發生SCD的機制之一。
3.電生理特性
體表心電圖發現51%患者有室性期前收縮(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s,PVCs),24%下壁導聯T波倒置和19%T波改變[11];32%患者心電圖正常。Holter發現63%的患者有PVCs,且29%合并非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ventricular tachycardia,VT);8%患者無異常;CA患者81%為心室顫動(ventricular fibrillation,VF),11%為VT,4%為尖端扭轉型室速(torsades depointes,TdP),4%為心臟停搏[7]。MVP患者典型PVCs常起源于乳頭肌和流出道,由于直接機械力或觸發活動導致損傷組織Ca2+處理異常和去極化后延遲激活所致[12]。但單形或多形PVCs不能足夠提示MVP患者為猝死高危,但PVCs異位起源點可能是SCD發生的一個重要標志。在6例雙葉MVP行導管消融的患者中發現,浦肯野起源的PVCs均被發現為VF誘發點且均有CA病史[13]。因此,惡性MVP電生理特征為起源于束狀肌和乳頭肌的PVCs易誘發VF從而導致SCD。
4.超聲心動圖
MVP發生SCD者70%累及雙葉,其次后葉(26%)和前葉(4%);嚴重MR占17%。雙葉MVP被認為是SCD的一個高風險特征,但這些患者的長期預后存在差異性。梅奧診所對1 200例不明原因的院外CA患者進行了研究,發現在24例年輕的特發性院外CA幸存者中,雙葉MVP的患病、率為42%[10]。但是另一項大型回顧性研究亦來自同一研究機構,發現孤立性雙葉MVP(除外其他危險因素)與單葉MVP相比,似乎并沒有顯著增加SCD的風險或需要安裝置入式心臟自動轉復除顫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提示惡性MVP可能存在其他危險因素[14]。MVP患者常發生MR并且反流程度與MVP發生VAs有顯著相關性,盡管這一結論也存在相互矛盾的數據。1項研究發現中重度MR是VAs發生的預測因子(RR=8.42)[15];但另一項研究發現MVP相關SCD也發生在輕度MR患者中[16]。
近期研究發現一種容易獲得的預測VAs發生的超聲心動圖下的標志物為心肌速度的測量。應用多普勒組織成像技術對多發性粘液瘤性MVP患者定量測定二尖瓣外側環形速度,有“Pickelhaube征”的患者惡性VAs發生率較高[17]。Pickelhaube征定義為收縮期外側二尖瓣環速度峰值為≥16 cm /s。
超聲心動圖可用于MVP的診斷、隨訪和是否干預進行評估。經典MVP定義為在長軸切面單個或雙葉二尖瓣瓣葉在收縮期移向左心房>2 mm,且1個瓣葉厚度≥5 mm;非經典MVP定義為瓣葉移位>2 mm且一個瓣葉厚度<5mm[18]。
二維經胸超聲心動圖(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和經食管超聲心動圖(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OE)均可用于評估二尖瓣結構;TOE更易評估左心房并且能夠評估MVP所有情況,此外,還應額外評估小葉厚度或冗余度、環狀擴張和腱索長度;多普勒成像對評估MR嚴重程度非常重要。MR后續效應如左心室、左心房和右心室擴張、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肺靜脈倒流、肺動脈高壓和三尖瓣反流對評估MR嚴重程度非常重要[18]。劉曉寧等[19]發現二維TTE+二尖瓣反流類型+血流匯聚定位二尖瓣的脫垂部位準確率達91%。
5.心臟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MR)
CMR能夠幫助確定心肌成分和識別VAs特異性的危險因素,例如心內膜纖維化。Basso等[11]對43例年輕的MVP發生SCD的幸存者進行CMR和組織病理學檢查,發現SCD和復雜VAs患者局灶性左心室乳頭狀肌纖維化(88%)或下基底纖維化(93%)發生率較高。延遲釓增強(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LGE)與組織病理纖維化相關。上述結果在另一項3 680例尸檢患者中得到證實,其中MVP占62例(1.7%)[20],其中74%患者發現包括1個或個乳頭肌(主要是后內側乳頭肌)和相鄰的左心室壁(主要是后下左心室壁)心肌纖維化;與非MVP相關的MR相比,MVP患者CMR顯示左心室纖維化較為顯著,且纖維化隨著MR的嚴重程度而增加,往往發生在左心室的特定區域,并與持續性VT或VF相關。其中,MVP患者左心室纖維化發生率為36.7%,而非MVP患者僅為6.7%。此外,在MVP患者中,纖維化心肌最常見于基底下側壁(31.1%)。在隨訪期間,4.5%的MVP患者發生心律失常事件(包括SCD、自主或誘發的持續VT),其中MVP合并纖維化心肌發生率最高7.7%,其次為MVP無心肌纖維化(2.7%),而非MVP患者僅為0.6%[21]。
Perazzolo等[22]調查了36例(女性27例,中位年齡為44歲)CMR顯示左心室LGE的心律失常型MVP患者,和16例(女性6例,中位年齡為40歲)無左心室LGE的MVP患者,發現二尖瓣環分離和收縮中期雜音較響的患者與左心室纖維化相關。二尖瓣環分離是心律失常型MVP合并左心室纖維化的常見特點。收縮期后卷曲引起的小葉過度移動導致下基底壁和乳頭肌機械拉伸,從而導致心肌肥厚和瘢痕形成。這些二尖瓣環異常,再加上收縮期中期雜音,可能發現惡性MVP患者。
6.心臟結構
75例SCD患者尸檢有73例發現MVP,73例中72例二尖瓣瓣葉冗長;15例患者二尖瓣周長為126 mm,2例瓣環擴張;二尖瓣前葉和后葉平均長度為30 mm和25 mm;瓣葉厚度與SCD無明顯相關性;有45例腱索異常,包括整體異常(62%)、斷裂(33%)及外觀正常(4%);30例患者中有12例(40%)出現左心室組織異常,其中3例出現乳頭肌纖維化[23]。27例存在其他心臟結構表現,17例(63%)無其他異常表現,5例(19%)為右心室纖維化,3例(11%)為三尖瓣脫垂,2例(7%)為心內膜炎。對MVP患者進行尸檢發現左心室纖維化,尤其是在乳頭肌附近,這可能為VAs的發展提供電生理基礎[24]。上述發現提示MVP患者左心室彌漫性和局灶性改變可能是MVP患者發生VAs的基質(表1)。

表1 MVP與SCD相關的特點總結[7]
7.VAs發生機制
MVP患者發生SCD存在兩個常見現象:左心室心肌纖維化(基質)和復雜室性異位點(觸發),纖維化可能為脫垂瓣葉機械牽拉的結果,最常局限于左心室下外側基底部或乳頭肌,因為這些部位最易受瓣葉機械牽拉[25];隨著脫垂小葉的持續機械牽拉,支撐二尖瓣結構的部位—基底和下外側心室、乳頭狀肌可發生心肌肥厚和纖維化[26]。此外,腱索與左心室心內膜之間的摩擦可導致“摩擦損傷”,其特點是乳頭肌和二尖瓣環心內膜纖維化;機械誘導的左心室纖維化為基質,導致持續性VT進展和維持的觸發活動或折返易感性增加[27]。
大多數經歷過SCD的MVP患者都有復雜PVCs病史,急性心肌拉伸導致動作電位持續時間縮短,靜息舒張電位下降,以及在去極化后早期發生牽拉激活[28]。瓣葉脫垂時乳頭肌發生急性牽拉,并且遠端浦肯野纖維容易發生去極化和自動化異常。實際上雙葉脫垂的患者發生CA之前,浦肯野纖維纖維化先于VF出現,常已經觸發PVCs[10]。
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包括交感神經張力升高和迷走神經張力降低,已發生在MVP患者中。這種高腎上腺素能狀態增加心室異位的頻率,以及心室肌對這種異位活動的易感性。脫垂的二尖瓣牽拉乳頭肌,激活局部牽拉受體,導致神經末梢膜去極化,異常的機械電活動反饋到中樞神經系統,導致VT或VF。此外,兒茶酚胺水平升高導致下游離子通道調節和肌漿網Ca2+負荷,導致延遲后去極化進而導致VAs(表2)。

表2 MVP發生SCD病理生理機制總結[34]
8.危險分層
雖然MVP中存在多種預測SCD的危險因素,但沒有一種單一的危險因素被證明是惡性VAs和SCD的預測因子。此外,目前還不清楚哪些危險因素的組合會使患者面臨更高的風險。MVP危險分層的挑戰是在大量低風險患者中識別隱藏的高風險患者。如前所述,大多數MVP相關SCD患者有復雜PVCs(觸發)和心肌瘢痕(基質),因此針對上述特征進行重點評估。多個研究表明女性、雙葉MVP、復雜心室異位點和CMR表現為LGE可用于區分低危或高危患者[11]。關于非持續性VT的檢測,在無心律失常癥狀的MVP患者中,12導聯心電圖、運動平板心電圖和Holter的靈敏度分別為17%、50%和83%。有學者建議無論患者是否有癥狀,均應延長心律監測時間(24 h或7d)以評估VAs負荷情況。對于MVP和不明原因暈厥患者,建議進行詳細全面評估,以確定患者是否存在真正心律失常導致的暈厥。臨床上提示心律失常性暈厥的特征包括劇烈運動時的暈厥、坐位或仰臥位時的暈厥、暈厥前突發心悸和暈厥前無任何先兆癥狀。對于MVP患者,懷疑為心律失常性暈厥和存在心肌瘢痕的證據,可以考慮進行心臟電生理學檢查。如果未行電生理學檢查或結果陰性,強烈建議患者置入長程心律監測儀,尤其是存在MVP高危因素的患者(如雙葉MVP、復雜PVCs)[29]。
對于有復雜VAs或超聲心動圖顯示乳頭肌或心室肌機械牽拉的患者(如Pickelhaube征),建議行CMR評估心肌瘢痕情況,建議對合并在多種危險因素的患者進行電生理學檢查進行風險分層研究。電生理檢查陽性結果定義為最多由3個室外刺激誘發的持續性單形VT或最多2個室外刺激誘發的多形VT或VF。對于陽性結果的患者,建議置入ICD。
9.導管消融
建議對電生理檢查誘發VT或VF的患者進行標測并確定瘢痕相關折返性VT,并進行導管消融[30],常見部位為乳頭肌或束支傳導系統。Syed等[13]對14例雙葉MVP患者進行電生理檢查并對心室異位點進行消融(常見部位為浦肯野系統),結果顯示即刻成功率較高(89%),癥狀明顯改善并且ICD適當放電顯著減少。
10.二尖瓣外科手術
二尖瓣修復理論上能夠減輕乳頭狀肌的張力,改善心室重構,從而減少VAs發生。目前關于二尖瓣修復或換瓣對減少VAs發生的意義多來自病例報道或單中心小樣本研究:Naksuk等[31]對32例雙葉MVP行二尖瓣手術的患者進行研究,發現年輕患者(42歲以下)術后心室異位點負荷顯著減少,而年長患者(62歲以上)無上述發現,提示早期外科干預能夠改變潛在的電生理基質;Vaidya等[32]對8例惡性MVP患者的回顧性分析顯示,手術修復雙葉MVP后惡性心律失常和ICD恰當放電均減少。老年患者可出現彌漫性纖維化(非局灶性纖維化)和額外的心肌基質如特發性流出道異位點且不能通過二尖瓣修復而改善。對于VAs患者二尖瓣修復時行外科冷凍消融結果已有報道,但無長期臨床隨訪數據。手術最佳決策需要由心臟外科醫生、電生理學家和影像學專家組成的心臟團隊的共同制定。
11.心臟自動轉復除顫器置入
目前尚無足夠的證據支持在MVP猝死高危人群中預防性的置入ICD,部分學者建議對存在觸發(多源PVCs)和基質(心肌瘢痕)的MVP患者進行電生理學研究以進行危險分層,如果患者存在持續性VT建議置入ICD進行一級預防[33]。
MVP在人群中較常見且大多數患者無臨床癥狀,關于MVP與VAs和SCD相關性目前有部分文獻報道。MVP高危SCD風險特征為女性、雙葉MVP、下壁導聯雙向或倒置T波、室早二聯律或VT、起源于乳頭肌或浦肯野纖維的PVCs。超聲心動圖和CMR能準確地描述二尖瓣的結構和功能,乳頭狀肌和下基底部左心室纖維化為SCD高危特征,并且與VAs發生相關;CMR能夠確定患者心律失常基質。早期二尖瓣修復和導管消融可以減輕心律失常的負擔,但數據來源于小型單中心研究。目前認為應設計大型前瞻性研究,評估影像學和遺傳學評估在這些具有挑戰性的患者中SCD風險分層中的作用,以及抗心律失常藥物治療、靶區導管消融和外科手術在MVP患者室性心律失常治療中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