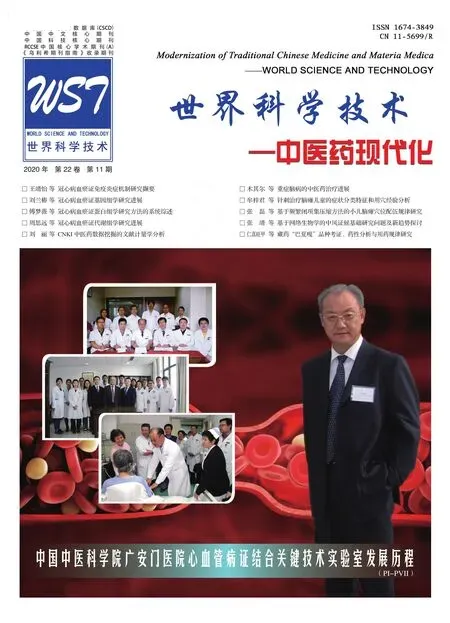針刺治療腦癱兒童的癥狀分類特征和用穴經驗分析*
牟梓君,何麗云,鄭琪光,成 秋,舒梓心,楊 杰,周雪忠,劉保延
(1.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 北京 100700;2. 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北京 100044;3. 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西安中醫腦病醫院 西安 710032;4.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藥數據中心北京 100700;5. 北京中騰佰脈醫療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北京 100022)
腦性癱瘓(Cerebral palsy,CP)簡稱腦癱,是一組持續存在的中樞性運動和姿勢發育障礙、活動受限癥候群,這種癥候群是由于發育中的胎兒或嬰幼兒腦部非進行性損傷所致[1]。因主要腦損部位的不同,腦癱兒表現為不同的臨床類型,又因腦損傷并不一定局限于腦的某一部分,多同時伴有其他神經精神異常病證,所以在運動功能障礙之外,常伴有感知覺、認知、交流和行為障礙,以及癲癇和繼發性肌肉、骨骼問題。根據我國2013年12 省市32 萬1-6 歲兒童腦癱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我國腦癱的發病率為2.48‰,患病率為2.45‰[2],略高于發達國家2.1‰的發病率[3]和患病率[4]。據此估算我國每年仍有約4 萬名新發腦癱,該病已成為兒童最常見的致殘疾病之一且康復需求巨大。
腦癱在中醫歸屬“五遲”“五軟”“五硬”等范疇,但中醫辨證分型缺乏統一性[5,6],給治療方案制定和辨證施治帶來影響,令本就復雜多樣的腦癱治療愈加缺乏精確性和穩定性。腦癱臨床表現的難治程度決定了治療方案制定和多措施綜合并行的必要[7,8],治療措施的多元化亦可影響具體方案的療效評價和改進優化。因此,找到一種清晰準確的辨治方法、探討各種治療措施的最佳適應癥具有重要意義。中醫針灸經過歷代醫者的實踐和創新,已融合解剖學、現代生物醫學、神經生理學等理論形成各種新的治療經驗和措施[9,10],在改善腦癱患兒肢體功能和認知、語言障礙方面有顯著療效[11,12]。本研究不拘泥于西醫臨床類型和中醫證型的固有分類,借鑒《傷寒論》中辨方癥論治的辨治模式[13],從癥狀出發試圖尋找可劃分腦癱人群的特征性表現及對應針刺治療選穴,以提升腦癱中醫辨治的準確性和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西安中醫腦病醫院2016年1月-2019年4月間入院的7歲以下腦癱患者住院病歷,共1584份。
1.2 西醫診斷標準
參照《中國腦性癱瘓康復指南》編委會于2015年4月通過的我國腦性癱瘓的定義及診斷標準。
1.3 中醫診斷標準
參照普通高等教育中醫藥類規劃教材《中醫兒科學》第六版[14]制定中醫診斷標準。
1.4 納入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年齡7歲以下的患兒;②主訴及癥狀符合上述中西醫診斷標準;③首次病程記錄中有明確主訴、刻下癥、辨證、針灸處方和針刺方法。
排除標準:①合并有其他嚴重的心、肝、腎等重要臟器的器質性疾病者;②病歷記錄不完整。③排除連續多次住院者首診外的診次病歷。
1.5 數據規范化
將符合研究需求的臨床病歷數據從數據庫導出到電子表格(Excel)中,從刻下癥中提取陽性癥狀、合并同義詞并進一步規范整理。遵循《針灸學通用術語》[15]、《中醫獨特療法-頭針療法》[16]、《中醫兒科常見病診療指南》[17]規范腧穴名稱、腦癱癥狀體征等相關術語。
1.6 數據分析方法
以患者為節點,患者間的癥狀相似度為邊,構建腦癱患者癥狀相似性網絡。相似度采用杰卡德系數[18](Jaccard coefficient)衡量,定義為:Jaccard′sim(A,B)=P(A∩B)/P(A∪B),其中A、B分別為兩個患者的癥狀集合。系數的取值范圍為0-1,取值越大表示兩個集合越相似,即兩患者病情越相似。為0 表示兩個患者癥狀完全不同,為1則表示兩個患者癥狀完全相同。
應用BGLL 高效社團發現算法[19]對患者癥狀相似性網絡進行非重疊社團劃分,將患者劃分為若干個亞組。
本研究采用相對危險度(RR)值來評估患者亞群的癥狀特征。我們將特定亞群中的病例作為暴露組,將剩余患者病例作為非暴露組,將某個癥狀作為事件。RR=(Cij/Ci)/((Cj-Cij)/(N-Ci)),其中Ci指的是腦癱亞群i中的患者數量,Cj指的是出現癥狀j的患者數量,Cij代表亞群i中有癥狀j的患者數量,N指的是本研究中的患者總數。如果RR>1,則代表亞群i中癥狀j 的分布高于其他組的分布情況。此外,我們通過卡方檢驗(P<0.05)來過濾出真正的特征性癥狀。尋找特征性穴位的方法與之相同。
2 結果
2.1 人口學信息及患病情況
根據納入排除標準最終納入701 份腦癱病歷,男性432 人(61.6%),女性269 人(38.4%),男女比例為1.6∶1。嬰幼兒期患者281 例,學齡前期患者420 例。其中,痙攣型腦癱占78%,其余依次為不隨意運動型(12%)、混合型(8%)、共濟失調型(2%)。701 份病歷的中醫診斷包含10 個中醫辨證,頻次統計10 次以上的證型是肝強脾弱證、肝腎虧虛證、脾腎兩虧證、痰瘀阻絡證,其中肝強脾弱證占比79.86%。
2.2 病例中的常見癥狀和針刺選穴情況

表1 小兒腦癱常見癥狀
對701 個腦癱患兒入院時的陽性癥狀進行統計,得到7歲以下腦癱兒的常見癥狀及覆蓋率(表1),其中頻數>200、覆蓋率>30 的癥狀有7 個,分別是反應遲鈍、尖足、不能行走、抓握不利、不會獨站、言語簡單、行走不穩,反映此階段腦癱兒的主要癥狀或主訴。
對患兒入院后的首個針刺處方予以分析,701 個腦癱針刺處方中含80 個(組)穴,涉及十四經穴、經外奇穴及焦氏頭針和靳三針4 類穴位,每組“靳三針”視為一個進行統計,獲取701 個處方中的高頻用穴及其覆蓋率(表2)。表中是所有腦癱針刺處方中使用率超過55的高頻用穴,即半數以上的患者治療都會選用這些穴位,可視作西安中醫腦病醫院治療此階段小兒腦癱的主要用穴。

表2 小兒腦癱常用穴位
2.3 腦癱患者相似性網絡及亞群劃分情況
以患者間共有癥狀評估指標Jaccard 系數≥0.4 為患者關系網絡的構建條件,計算后得到一個包含636個節點、5305 條邊的患者相似性網絡。在此網絡基礎上,利用社團劃分算法挖掘網絡內相應社團,最終獲取模塊度為0.587的17個社團(圖1),可將其視作不同腦癱患者亞群。本研究選取包含了75%以上患者的4個較大社團,即社團1、社團4、社團3、社團9(表3),對其深入分析以便觀察此人群分類方式下各腦癱亞群的癥狀分類特征,進一步總結相似腦癱患者人群的臨床針刺取穴經驗。

圖1 腦癱患者社團劃分圖

表3 腦癱患者社團劃分結果
2.4 腦癱亞群的代表癥狀群和特征性選穴
選取上述結果中的4個較大腦癱患者亞群相關癥狀、針刺處方數據,分別統計不同亞群中的癥狀、穴位富集情況,即各個亞群內具有顯著性的癥狀和穴位。
按照P<0.05,RR >1.5 篩選各亞群特征性癥狀,作為各類腦癱人群的特征,現將各亞群中出現頻次占總頻次60%以上的特異性癥狀和各亞群中前2位的高頻特異性癥狀列舉出來(表4)。同理,按照P<0.05,RR >1.5篩選各亞群特征性選穴并總結如下(表5):亞群1-照海、完骨、風府;亞群4-承山、環跳、腰陽關、曲池、足三里、舞蹈震顫控制區;亞群3-大椎、四神聰、百會、言語一區、腰陽關;亞群9-智三針、風市、言語區、伏兔、髀關。

表4 腦癱亞群的特征性癥狀

表5 腦癱亞群的特征性穴位
3 討論
本文從具體的癥狀出發,在現有的腦癱臨床分型和中醫辨證之外,以共有的癥狀群為依據對患者進行分類,尋找臨床常見腦癱亞群分類中的特異性癥狀群及其針刺穴位,總結院內的腦癱診治經驗。
3.1 腦癱類型及高頻癥狀、高頻穴位分析
治療手段的選擇與腦癱的類型或臨床特征之間有一定的關聯性。現代醫學腦癱臨床分類中,痙攣型和以痙攣為主的混合型患者約占全部腦癱病例的2/3左右,有文獻指出這2種類型是外科手術方式的主要受眾[20]。那么,針刺治療的腦癱受眾又是什么情況呢?本次研究納入病例皆根據個體情況接受了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針刺治療,其中痙攣型占比78%,用真實世界臨床數據證明:痙攣型腦癱并非不可針刺,而要辨證看待,并且也是針刺的主要腦癱類型。臨床中,除全身肌張力顯著增高、僵硬的強直類患兒外,肌張力增高程度在適宜范圍內的患者仍可在拮抗肌、主動肌辨證選穴施治,平衡主動肌和拮抗肌的肌張力控制痙攣,并有研究指出針刺拮抗肌側穴位對痙攣性偏癱的療效優于主動肌側[21]。中醫證型方面,根據研究數據中的辨證情況發現肝強脾弱證多見,與王氏等[22]學者認為痙攣型腦癱多歸屬中醫肝強脾弱證的認識一致。中醫針灸在治療腦癱方面也應有最佳適應癥,為減少不必要的衛生資源浪費、實現精準施治,還需要研究針灸與臨床表現之間的關聯,以達到最佳治療效果。
有研究者[23]分析腦癱患者的中醫癥狀分布情況,指出半數以上的腦癱兒有頭頸四肢軟弱、筋脈拘攣、智力低下、語言障礙、發育遲緩的表現。本研究納入的患者中1/3 以上患者都有以下7 個表現:反應遲鈍、尖足、不能行走、抓握不利、不會獨站、言語簡單、行走不穩,結合既往研究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來院接受針刺治療的腦癱患兒的癥狀特征,及其所處的生長發育階段和疾病情況,若與相關療效評價指標結果結合便能刻畫出適宜針刺治療的各類腦癱人群癥狀特征,從而提高治療效率。對不合作和多動不安的患兒可采取速刺不留針,今后可以進一步討論應用何種針刺補瀉手法有助于提高療效。
在本次收集的針刺處方中,常用穴位有15 個,足運感區、平衡區、運動區是結合神經生理學認識改善大腦皮質血液循環,繼而緩解腦癱癥狀的頭針選穴,其他常用高頻選穴以多氣多血的陽經穴居多,如肝俞、脾俞、陽陵泉、豐隆、委中、外關、手三里、懸鐘、承扶。且肝俞、脾俞、陽陵泉使用率較高,體現出肝脾兩藏在腦癱患者診治中的重要性,亦考慮到小兒“肝常有余”“脾常不足”的生理特點。三陰交既可滋陰養血,又為肝脾腎三經交會穴,三藏同調,故成為應用率最高的腦癱常用穴。行間、血海疏肝行氣、補血活血,經絡氣血暢達必然是腦癱康復的要義。
3.2 腦癱癥狀相似亞群的特征性癥狀
本研究基于患者刻下癥構建患者相似網絡,借用社團分析方法對腦癱人群進行社團模塊劃分,由此獲取小兒腦癱亞群,是對新的腦癱分類方式的探索。
在這4個亞群中,各自有不同的癥狀,代表了不同的疾病階段,或者病情特點:①亞群1的特征癥狀是足內收、易摔倒、不能書寫、步態異常、偏癱步態、行走不穩等以行走功能異常為主的運動障礙和姿勢障礙,以及不能書寫的手精細動作的發育障礙,雖伴有言語簡單,但與其他幾個亞群相比障礙程度較輕,功能狀態較高。②從亞群4的患者癥狀群可見其運動發育遲緩或運動障礙嚴重,豎頭、翻身、坐、爬尚不能完成。③亞群3 患者站立、行走功能受限,運動障礙程度較重,特征癥狀四肢痿軟伴流涎和精神呆滯問題,有心、脾兩虛之表現。④由亞群9患者的癥狀可知其有一定的運動能力,但有姿勢障礙和步行或自我移動能力受限,伴有斜視等視覺障礙。
在亞群特征癥狀中雖然有個別癥狀在701個患者中的占比不高,但卻是亞群內的高頻癥狀,暗示相應亞群的患者這方面的癥狀問題相較于其他人群更突出,因此對針刺處方選穴有很大影響。
以上4 類腦癱亞群有較清晰的特征差異,尤其在運動發育延遲程度和相關伴隨癥狀方面,而這也是腦癱預后的影響因素,其他相關因素還包括腦癱類型、病理反射存在與否和智力、感覺、情緒異常的程度[24]。由此可確定這個分類有利于腦癱患兒的辨證治療和預后的判斷。
3.3 腦癱亞群的特征性穴位
特征性穴位之特異,從701 個處方的使用頻數統計即可得出:大部分穴位被選用的頻次不高,但卻相對集中于某一個亞群中。說明亞群患者的某些癥狀特征令針灸醫師在中醫理論知識和經驗的指導下作出如此選穴,因而這些選穴與亞群的特征癥狀緊密相關,這也是探索辨方癥論治過程的一個切入點,由此可初步識別癥穴對應關系和醫生臨床施治時隨癥加減的思路、動機。
亞群1 的癥狀以行走功能和足部姿勢異常為主,伴有言語簡單,亞群1 特征穴中位于足內踝下的照海穴既可以發揮近治作用,又可循經遠治咽喉病癥,與完骨、風府共治構音、吞咽障礙和癲癇等。亞群4的特征性穴位承山、環跳、腰陽關、足三里可治腰骶疼痛、下肢痿痹等運動感覺異常,曲池可治上肢活動障礙,足三里又是胃經下合穴,可健脾益氣補后天之不足,諸穴相合共治豎頭、翻身、坐、爬等運動發育落后表現。舞蹈震顫控制區可治震顫等風動之證,對應亞群中豎頭不穩、點頭癥狀。大椎、腰陽關可治療頸項和腰部等軟癱,對應亞群3中不能獨站、行走及肢軟等直立姿勢障礙和運動障礙;百會、四神聰常合用以治療神志異常和智力低下,對應特異癥狀中的目光呆滯問;頭針言語1 區位于運動區的下部,主治流涎、運動性失語、發音障礙等。亞群9 中有步行受限和姿勢異常,對應選穴有風市、髀關、伏兔。
研究之初便欲尋找不同腦癱患者癥狀群所對應的針刺處方或常用腧穴,故篩選病歷時即按照有針刺處方者納入,亦可實現對醫院的腦癱相關針刺治療經驗進行挖掘和總結。
4 不足與展望
局限性:①腦癱的治療不僅有針刺的參與,還有康復、推拿、中藥或中成藥等多種治療方式,雖然患兒治療方案的選擇有眾多因素的影響,但主要因素仍是患者的病情。本次納入研究的腦癱兒皆是接受針刺治療的患者,故亞群分類更多反映的是運動發育障礙等適合針刺或可針刺患兒的癥狀特征,尚且缺乏未接受針刺治療者的癥狀特征和人群特點。②本次納入的僅是一家腦病專科三甲醫院的患者,病例數量尚不豐富。③本研究采用癥狀相似網絡和數據挖掘方法對患者進行了新的分類嘗試,因而更關注癥狀層面,證型方面體現較少。今后可在此研究基礎上進行全腦癱人群的社團劃分,豐富患者數和中心數,完善對腦癱患者亞群特征的描繪,使這種分類方式更具普適性,提高腦癱辨證施治的準確性,同時對腦癱亞群進行長期隨訪,觀察各組預后差異以驗證分類的正確性并進一步調整。
因中醫臨床辨證受醫生經驗、知識背景、醫學流派等因素影響,對同一類患者的證型診斷存在不一致的情況,所以從癥狀出發總結真實世界腦癱亞群的典型特征癥狀群及其針灸治療經驗,可為腦癱的診療實踐提供參考。本文的腦癱分類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腦癱患者的人群特征,且依據癥狀群的辨證診療更具針對性,便于推廣使用,有助于提升臨床小兒腦癱辨證施治的準確性和腦癱針刺治療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