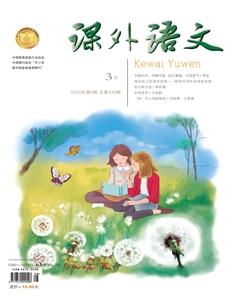節氣之美
梅玉榮


我們聰慧的祖先,創造了美麗絕倫的歷法,根據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潛心研究構成獨特的時間知識體系,將一年劃分為二十四節氣。在漫長的農耕時代,二十四節氣被人們奉為圭臬,它不僅是文人雅士吟花弄月的詩化方式,更是老百姓有滋有味的恒久生活。
清朝趙翼在《陔余叢考·二十四節氣名》中寫道:“二十四節氣名,其全見于《淮南子·天文》及《漢書·歷志》。三代以上,《堯典》但有二分二至,其余多不經見,惟《汲冢周書·時訓解》,始有二十四節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順天時,作《時訓解》。則其名蓋定于周公。”看來,二十四節氣的確立,是從周朝開始的,可見其歷史悠久。
二十四個節氣,恰似一幅幅古樸的畫卷,一張張馥郁的詩箋,一朵朵靈動的音符,在歷史的回廊里旋轉,蕩漾,久久不絕……
節氣之美,美在實用。節氣中有反映季節的,如立春、立秋、夏至、冬至等;反映氣候特征,如小暑、大暑、小寒、大寒等;有反映物候現象,如驚蟄、谷雨、小滿、芒種等;有反映降水情況,如雨水、小雪、大雪等。千百年來,老百姓依季候特點,據以安排農事、調理衣食等。從小我們就聽到長輩們念叨“未到驚蟄先動雷,四十八天云不開”“立夏不拿扇,急煞種田漢”“處暑白露節,夜寒白天熱”“大寒見三白,農人衣食足”等。相伴而生的還有《月令·七十二候》,從中更可以窺見包羅萬象的古代物質文明與精神世界。
節氣之美,美在詩意。每一個節氣名,都清簡如詩,雙音節,讀來朗朗上口,易記于心。谷雨,天清地明的春天里,谷和雨,兩種事物結合在一起,便有一種樸實動人的內涵;白露,晶瑩,略有涼意,與桂花共同散發清芬,于是中秋至,明月圓,佳人共,天倫樂。中國是詩的國度,詩的光芒穿透歷朝歷代。從陶淵明在南山下種的菊,到李白吟哦過的月光,杜甫居住過的草堂,蘇軾在赤壁東坡植的梅,大都可從節氣里找到相應的佐證或依據。姜夔詞中“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分明是雨水時節綠意滿眼的景致;晏殊詞里“燕子來時春社,梨花落后清明”,則是一派清新田園春光;“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小雪之時邀友小酌,豈獨白居易一人?而在冰封雪蓋的大寒之夜,不僅有凌寒而開的梅花,還會想起杭州湖心亭看雪的張岱,想起雪夜訪戴安道的王子猷,想起寒江獨釣的柳宗元,也會想起紅樓夢里錦帽貂裘大啖鹿肉的一群癡男嬌娃。那人,那景,都詩意滿滿,詩香盈懷。
節氣之美,美在哲理與禪境。簡樸自持,從容淡靜,傳統文化體現在節氣中是這樣花木扶疏,風月琳瑯。天地不言,人為過客,順應自然之理。像清明,宜祭掃,踏青,一面是用淚水追思逝者,一面是用笑容迎接春光,生死互為映照,讓人多添了悟。小滿,意為“小得盈滿”,豈不是告訴我們“太盈則虧”的道理么?處暑,又為“去暑”,不是說明要心平氣和、祛除浮躁么?“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看取蓮花凈,方知不染心”,“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些詩句,既應和了季節與節氣,也暗含了融身自然、閑適孤清的禪意。
臺灣知名美食家洪震宇從美食的角度詮釋道:“節氣是一種慢食與智慧,順著大自然的節奏、土地的心跳,加上農家人虔誠的巧手與耐心,吃到最飽滿的靈魂風華。”這樣詩意深情的表達,足以讓我們為節氣這個中華民族詩意棲居的獨創而驕傲,并永續綿延。
花知時而開,人順勢而立,與天地唱和,與萬物相諧,節氣中所體現出來的“天地人”合一的共生之觀,是中華兒女共有的文化基因,靜水流深,蘊藉厚重。而在今年11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通過審議,批準中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每一個節氣都如此豐盈潤澤,飽滿芬芳,將光陰之變、民俗之味統統融匯其中,繪成一幅優美蘊藉的畫卷,其味雋永,其美綿長。撫摸著節氣的清晰紋理,可以將每一年的時光過得有序有味,風情萬千。
(選自《湖北日報》2016年12月19日)
【賞析】
春夏秋冬,雨露霜雪,兩千多年前的先人觀天時萬物,總結出二十四節氣。花知時而開,人順勢而立,與天地唱和,與萬物相諧——節氣中所體現出來的“天地人”合一的共生之觀,是中華兒女共有的文化基因,靜水流深,綿延至今。天地之間充滿了氣,這不僅是今天人們的常識,而且早已被我們的先民認識。古人以為,風就是氣,所以對于氣的認識實際來源于人們櫛風沐雨的感受。而人作為天地間的一員,其身體內也自應充滿氣,人的呼吸可以很自然地使人懂得這個道理。將這種觀念推而廣之,便會產生宇宙萬物都充滿著氣的認識。這些認識使先民感悟到氣既為生命之本,更是萬物運動的源泉,從而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以氣為核心的獨具特色的人文內涵,并促進了古代天文、歷法、醫學、哲學的形成。本文從“節氣之美,美在實用”“節氣之美,美在詩意”“節氣之美,美在哲理與禪境”三個不同角度來給我們詮釋了中國二十四節氣之美,讓我們對中國節氣之美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與認識。
(張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