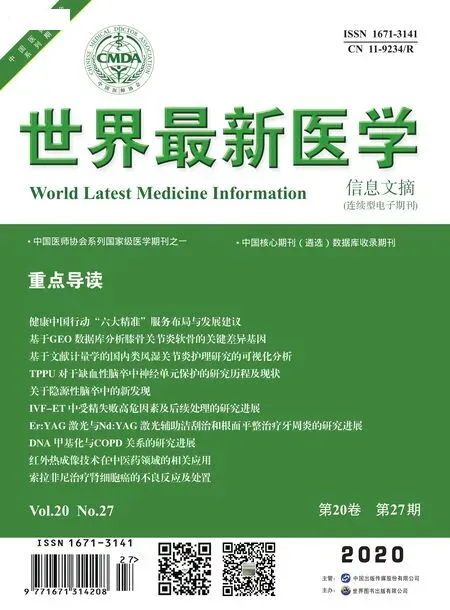經肛全直腸系膜切除術中細菌培養的結果分析
謝楊,張宏宇
(重慶醫科大學 胃腸外科 ,重慶)
0 引言
直腸癌是消化道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手術為主要治療方式。1982年,英國Heald教授[1]提出全直腸系膜切除術(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多年實踐證明TME在降低盆腔局部復發率、提高腫瘤R0切除率、增加標本環周切緣(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CRM)安全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已獲得廣泛共識并成為直腸癌根治術的標準。2010年,美國Sylla教授[2]報道并提出經肛全直腸系膜切除術(transanal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aTME),這種“自下而上”的逆行操作使直腸癌根治術進入一個全新發展的階段;taTME在男性、骨盆狹窄、腫瘤較大、直腸系膜肥厚、低位直腸癌患者中,展現出卓越的操作優勢;國內外關于taTME的大宗數據報道[3-5]也層出不窮。但taTME仍存在一些爭議,如無瘤接觸(no touch)、無菌原則等;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如有不低的吻合口漏發生率,原因可能與不使用吻合器吻合及未行預防性造口等有關[6]。而關于taTME術后吻合口漏及腹腔感染與術中術區積液中細菌是否相關的研究尚少。本研究通過分析行taTME手術直腸癌患者的術中培養結果,旨在發現該結果與吻合口漏及腹腔感染的關系,為術中操作及圍手術期治療提供更多的臨床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1)確診年齡 30~85歲;(2)病理活檢為直腸癌;(3)腫瘤下緣距肛緣2-10cm;(4)術前臨床分期Ⅰ~Ⅲ期(以MRI為主要分期依據) 或可一期聯合切除的Ⅳ期肝轉移;(5)無嚴重基礎疾病,心、肝、肺、腎功能可耐受手術;(6)患者及家屬理解并愿意接受該手術。
排除標準:(1)肛門狹窄或損傷;(2)行局部切除或腹會陰聯合切除術;(3)腫瘤遠處轉移不可切除;(4)術前合并其他部位感染如肺部感染、泌尿系統感染。
1.2 臨床資料
根據上述標準,回顧性收集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胃腸外科2017年9月至2019年8月期間,行taTME手術的56例直腸癌患者的臨床資料。男性42例、女性14例,平均 年 齡(57.77±11.82)歲;體 質 指 數(body mass index,BMI)(23.27±2.61)kg/m2,腫瘤下緣距肛緣距離(5.54±1.65)cm。根據術前CT 及MRI進行腫瘤TNM 臨床分期:Ⅰ期18 例、Ⅱ期16例、Ⅲ期20例、Ⅳ期2例(均為可切除的左肝轉移)。本研究經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患方術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術前腸道準備
包括機械性腸道準備(mechanical bowel preparation,MBP)和抗生素腸道準備(antibiotic bowel preparation,AMP)[7]。MBP包括術前2-3天行半流質飲食、術前1天口服瀉劑聚乙二醇(PEG)、術前當晚甘油灌腸一次。AMP為術前一天口服甲硝唑(2片 tid)、鏈霉素(1支 bid)。
1.4 手術方法
分為經腹組和經肛組進行,參照中國經肛全直腸系膜切除專家共識及手術操作指南(2017版)[8]。
1.4.1 腹腔鏡TME 組: 全麻建立氣腹壓力10-12 mmHg(1mmHg=0.133kPa),無菌棉簽蘸取腹腔初始積液記作1號培養。游離乙狀結腸及直腸系膜(兩側不游離直腸側韌帶神經血管束(Neurovascular Bundle,NVB)),束帶結扎近端腸管后圍直腸一周放置小紗布(gauze mark)。
1.4.2 taTME 組:稀碘伏水沖洗消毒直腸,無菌棉簽蘸取荷包縫合后的直腸腔積液記作2號培養。按“先前或后側銳性切開進入間隙,兩側迂回分離切斷組織”的原則并循“神圣平面”(holy plane)游離直腸系膜與腹部操作平面會合。
1.4.3 標本移除及消化道重建:經肛拖出標本并離斷腸管,根據情況選擇手工或器械吻合。重建氣腹后無菌棉簽蘸取盆腔積液記作3號培養,并放置盆腔引流管。
1.5 觀察指標
1.5.1 術中情況:手術時間、出血量、吻合方式及高度、是否預防性造口、術中并發癥(包括直腸穿孔、骶前出血、尿道損傷等)。
1.5.2 術后病理:遠近切緣陽性率、CRM陽性率(根據Quirke等[9]的定義評估CRM,CRM<1 mm定義為陽性)、淋巴結檢出數、TNM分期。按第八版TNM分期系統[10]對腫瘤進行評估。
1.5.3 術中3 次培養結果。
術后并發癥:吻合口漏、吻合口出血、腹腔感染或局限性膿腫、腸梗阻、切口感染、尿潴留、肺部感染。并發癥分級采用Clavien-Dindo(CD)分級標準[11],吻合口漏根據國際直腸癌研究組(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f Rectal Cancer,ISREC)嚴重程度分級標準進行分級[12]。
1.6 統計方法
采用SPSS軟件進行統計學數據處理。符合正太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手術情況
全組56例患者均成功完成taTME手術,無中轉開腹及直腸穿孔,1例(1.8%)發生骶前出血約 500mL,1例(1.8%)發生輸尿管損傷,預防性造口29例(51.8%),器械吻合41例(73.2%)。全組手術平均時間(345.50±84.83)min,術中平均出血量(125.71±82.28)mL,吻合口平均高度(3.00±0.89)cm。
2.2 術后病理
遠近切緣陽性率及CRM陽性率均為0%,淋巴結檢出總數(14.59±7.91)枚。TNM分 期:0期 2例(3.6%),Ⅰ 期 23例(41.0%),Ⅱ期14例(25%),Ⅲ期15例(26.8%),Ⅳ期2例(3.6%);其中,粘膜內癌1例,新輔助化療后病理完全緩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1例。
2.3 培養結果
3次培養結果中,所有1號培養結果均為陰性,2號培養陽性6例(10.7%),3號培養陽性7例(12.5%)。在培養陽性的11例(19.6%)中,有8例(14.3%)發生腹腔感染和或吻合口漏,占比高達72.7%(8/11)。具體資料見表1。
2.4 術后并發癥
全組患者中有16例(28.6%)出現術后并發癥,其中CD分級Ⅰ級 4例(7.1%),Ⅱ級 8例(14.3%),Ⅲ b級4例(7.1%)。無吻合口出血、切口感染、肺部感染及圍手術期死亡發生。具體并發癥情況如下:
吻合口漏7例(12.5%),包括A級漏2例,B級漏1例,C級漏4例。(1)2例A級漏患者2、3號培養均陽性,術中均行預防性造口術,術后均無發熱、腹痛等臨床癥狀,經引流、抗生素等治療后好轉。(2)1例B級漏患者術中未行預防性造口術,3號培養陽性,術后有低熱、輕微腹痛等臨床癥狀及少許膿性引流物但無腹膜炎體征,經營養支持、抗生素及加強引流等保守治療后好轉。(3)4例C級漏患者,2例3號培養陽性,另外2例培養陰性;均二次于全麻下行近端腸管造口術,再經營養支持、抗生素、加強引流等治療后好轉出院。
腹腔感染或局限性膿腫4例(7.1%),2例2號培養陽性,2例3號培養陽性,術后盆腔引流液培養均見細菌生長,證實腹腔感染存在。2例(第5、14號病例)患者術后CT提示腹腔局限性或包裹性積液,感染輕微,無發熱腹痛等癥狀,經敏感抗生素、加強引流等治療后好轉。1例(第6號病例)患者術后CT提示骶前間隙片狀滲出,無發熱腹痛等癥狀,經抗生素、加強引流治療后好轉;1例(第10號病例)患者術后盆腔引流管見膿性引流物,合并B級吻合口漏,有低熱、輕微腹痛等臨床癥狀,主要經抗生素、營養支持及加強引流等治療后好轉。
有2例(3.6%)患者發生小腸不全性梗阻。影像學檢查(X片、CT)均提示為小腸梗阻,予禁食禁飲、營養支持等治療,逐漸恢復腸內營養并出院。
尿潴留5例(8.9%)。1例(第18號病例)合并術后尿路感染,經抗感染治療好轉。經合理規范訓練膀胱排便功能后均已成功拔出尿管。
3 討論
自taTME這一新概念新術式的提出至今,已有近10年的發展歷史,它已成為結直腸外科領域關注的焦點之一。相比于腹腔鏡TME,taTME操作優勢主要體現在肥胖男性、腫瘤大及困難骨盆的中低位直腸癌患者中,減少了前列腺、盆腔神經的損傷,降低了CRM陽性率,能獲得更好的遠切緣長度[13-17],為患者更良好的預后帶來了福音。一項關于腹腔鏡TME和taTME這兩種術式的國際性多中心隨機研究COLOR Ⅲ[18]正在進行中,旨在為臨床提供更高的循證醫學證據;筆者團隊也有幸參與此研究,望盡綿薄之力。
外科領域依然重點關注并發癥,所以taTME這一新技術同樣面臨著老問題。如taTME術后吻合口相關并發癥包括吻合口漏、出血、狹窄等,打破無菌原則帶來的感染性并發癥包括腹腔感染、膿腫,以及逆反操作是否帶來更多的術中并發癥。一項來自英國牛津大學關于全球多達23個國家66個中心的回顧性研究表明,在所有720例taTME中,吻合口漏發生率為6.7%、腹盆腔膿腫為2.4%、術中并發癥(包括盆腔出血和臟器損傷)為8.4%[3];隨后Penna報道了更大樣本量的國際taTME研究結果[4],總體吻合口并發癥達到了15.7%,其中吻合口漏發生率為9.8%,盆腔膿腫為4.7%,同時術中不良事件達到了30.6%。本研究吻合口漏占12.5%,腹腔感染或局限性膿腫占7.1%,均略高于上述研究;而術中并發癥為3.6%則較低。筆者認為上述差異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納入排除標準存在差異,本研究事先剔除術前合并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而行taTME的病例;二是囊括不易被發現的A級吻合口漏;三是重點關注細菌培養結果并定義術后引流液細菌培養陽性則為腹盆腔感染,包含部分無臨床癥狀而被忽略的感染病例以及考慮引流管細菌定植的病例;四可能也和本研究為單中心、病例數量較少有關。

表1 培養陽性及16 例并發癥具體情況
國內探討分析術后吻合口漏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多,如池畔等[19]關于直腸癌保肛術后吻合口漏的影響因素及預后分析發現腫瘤下緣距肛緣≤5cm和新輔助放化療是吻合口漏的獨立危險因素;而劉牧林[20]關于直腸癌前切除術后吻合口漏危險因素的薈萃分析納入6454例患者,結果表明男性、貧血、Duke’s分期及腫瘤下緣距肛緣距離等是吻合口漏的主要危險因素。英國Penna教授的taTME研究[4]也提示術后吻合口漏的獨立危險因素包括吸煙、男性、肥胖、糖尿病等。本研究著重關注術中細菌培養結果和吻合口漏、腹腔感染等術后并發癥。結果顯示,2號培養陽性率為10.7%,這表明約十分之一的taTME手術是在有菌環境里進行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幾點:部分患者術前腸道準備不充分,腸腔內殘留少許稀便;完成腸道準備至手術的間隔時間中,腸道分泌物成為細菌繁殖基地;腫瘤距肛緣近,開放切開腸壁法增加了腸腔暴露長度和時間;荷包縫合阻斷腸腔后的操作過程中依然存在上方腸液流出的可能;術中直腸腔無法徹底消毒。同時吻合后3號培養陽性率為12.5%,2號培養存在陽性表明taTME“自下而上”操作在游離直腸系膜至吻合前未達到嚴格無菌,所以3號培養陽性也在合理之中。但2、3號培養是否陽性之間并無明確關聯,筆者認為這可能與經腸道準備和常規消毒后存活細菌數量急劇減少、無菌棉簽所能吸附積液量有限以及微生物實驗室檢驗標準有關。針對這一問題,筆者體會:分別收集足量的荷包后直腸腔積液和吻合后腹腔積液應是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有望提高2、3號培養結果的一致性。
有文獻表明[21],直腸癌前切術后有54%的吻合口漏是通過吻合口周圍引流液性質來確定的;而Velthuis等[22]發現,在taTME術畢經腹所取3個部位(前列腺或陰道后壁、后盆壁和骶岬處)的培養中,9例(39%)細菌培養陽性,其中4例(44%)術后發展為盆腔膿腫。本研究共11例培養陽性,有8例發生術后腹腔感染和或吻合口漏,占比高至72.7%;4例腹腔感染,術中培養陽性率為100%;而7例吻合口漏,術中培養陽性率為71.4%。根據以上結果,筆者團隊建議:(1)taTME應嚴格腸道準備,盡量減少糞便殘留;(2)術中嚴格無菌操作,尤其是經肛部分,可多次使用碘伏消毒;吻合后足量滅菌水沖洗腹腔;(3)術畢盆底安置螺紋虹吸引流管,術后囑患者半臥位,盡量早期引出腹腔積液使盆腔粘連閉合;(4)當術中培養結果陰性時taTME常規使用抗生素至術后第三天,并根據血常規及感染指標決定是否繼續使用;當術中培養結果陽性后,積極根據培養藥敏結果決定是否更改抗生素,同時加強腹腔引流,做好預防工作;(5)術后前3天每日取引流液細菌培養、之后隔日培養,并結合術中培養制定后續治療措施。
綜上,本研究認為taTME術中培養是否陽性與術后腹腔感染和或吻合口漏存在關聯,圍手術期需要積極治療處理。但本研究為單中心小樣本回顧性研究,尚需更嚴謹縝密的實驗設計和更多的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來提供更高級別的循證醫學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