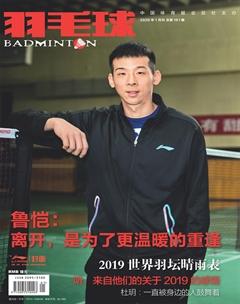這一年,3D打印、生物打印與羽毛球行業的距離
天堂有羽
步入2020年,在這一期內容中,我們會盤點這五年來被我們曾經多次提及的熱點技術-3D打印、生物打印,是否降臨到了羽毛球行業。同時,我們會涉及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新技術——人造肉、合成生物學,有哪些已經在為我們的行業帶來曙光。
關于救贖
去年9月,為了紀念影片《肖申克的救贖》25周年,這部經典電影在美國院線重新上映。
作為這部影片的擁躉,我18年前剛看的時候,引發我思考的是逆境后的重生,宛如王渝燕等前輩創刊《羽毛球》雜志的過程。18年后再次重溫,我再一次想到了救贖。
救贖行為對應的是原罪,Andy坐了19年牢后,終于認識到是自己—一“a hard man to know”,因自己冷漠,間接殺死了他妻子,那一刻他精神上得到了救贖。從這里,我聯想到了羽毛球運動因“Hard feather to get”而仍存的兩項原罪:動物保護與貴族運動。

羽毛球跟其他持拍類運動一樣,可能還有一項“原罪”——單側運動。以右手持拍為例,會讓身體右側變得過于發達,從而把脊柱往左邊擠彎。查詢了很多資料,因缺乏相關權威證明,所以在這里我只是提供一個參考。針對這一點,我個人防患的措施是平時揮拍時也加上左手,并一直保有以后可以左右開弓打球的夢想。
最后的原罪
羽毛球運動從一百多年前誕生開始,就背負著傷害動物的“原罪”。如羽毛球線使用動物腸衣,球拍手膠使用牛皮,羽毛球頭使用羊皮,羽毛球鞋使用袋鼠皮等等。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現在這些已經被尼龍、聚酯纖維、PU、聚氨酯、TPU、KPU、超纖布等新型人造材料替代。如今“原罪”內容只剩下最后一項——使用禽類毛片,且獲取毛片時常用的活撥方法,使動物在臨死前經受痛苦。

人們用“帶血的GDP”來形容沒有底線的生產行為。無可回避的是,我們羽毛球運動的樂趣,一定程度上也建立在上面這種“帶血的羽毛”上。標題
在一些動植物保護理念較深入的國家,他們甚至對使用天然木柄的球拍進口都設了很多規定。羽毛球的這些“原罪”,影響了其更大程度上向這些國家的推廣,導致“功能返古”——羽毛球仍然像百年前在英國伯明頓莊園發明出來時那樣,被當成一種酒足飯飽后的庭院休閑娛樂,而不是一種你爭我奪的競技體育。換位想一下,環保與手感如魚與熊掌,你有多不喜歡尼龍球與碳柄球拍的手感,競技羽毛球運動就有多難在環保理念強的國家取得受眾。
再退一步,如果這些感情因素并非普遍的話,那經濟因素——高昂的羽毛球開銷,即“一個球的費用相當于一個飯盒”,打一場球就是掀掉了一個食堂餐桌,加上見漲的訂場費用等,也讓羽毛球不得不背負起了“貴族運動”之名,讓一些人望而卻步或淺嘗輒止。對羽毛球工業來說,成本最高的就是這些天然羽毛的毛片資源與建構之上的人工成本。人造材料之碳素羽毛球如“碳音”,在高開低走后,顯然并沒有撬動傳統天然羽毛球行業的冰山一角。
回顧2019年,世界羽聯這一年開始試推戶外羽毛球。世界羽聯的意圖是想擴大運動的人口基數,這是場地端的“降維攻擊”。話題回歸到我們的器材端,如果解決這兩個“原罪”,也一定有助于降低我們運動的門檻。
相信大多數羽毛球迷聽說過一個段子:“當初你說打羽毛球不燒錢,現在全家都以為我吸毒。”這句話其實說的就是羽毛球是一種容易讓人上癮的運動,而且貴了點。
救贖的曙光
多年前,“紙餡包子”的新聞是假的,今年成熱門話題的人造肉卻是真的。2019年,眾多餐飲食品巨頭集中推出了人造肉產品,如漢堡王推出人造肉漢堡,美國泰森食品公司開始銷售替代肉,宜家也準備在餐廳中銷售人造肉做的瑞典肉丸。我國也不甘落后,首款人造肉產品已于9月面市,用在了鮮肉月餅當中。國內首家亮相的人造肉公司Stanfield在深圳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家餐廳。這家餐廳離我不遠,我特意去品嘗過。品嘗的時候,受他們“兼得美食與大愛”的口號感染,我就萌發了好奇心,很想知道這種“兼愛”究竟什么時候可以在我們羽毛球運動上實現。
在科技界,人造肉技術是這幾年全國最熱的發展趨勢之一。2018年《科學美國人》把它選入了“十大新技術榜單”,2019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又把它評選為“十大突破性技術”之一。
就在我籌劃這篇文章的時候,2019年11月18日上午,中國第一塊人造培養肉,在南京農業大學國家肉品質量安全控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誕生。這一事件被業內認為意義非凡。這些新聞無不觸動著我的神經,人造肉來了,人造羽毛還會遠嗎?我認為,至少科技給我們了一線曙光。
技術的復盤
2014年,當年最熱門的話題是號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3D打印。在美國MarkForged公司突破了碳纖復合材料的3D打印技術后,我曾在《漫談3D打印技術將如何改變羽毛球器材》一文中做了很多想象。雖然我的一些科技浪漫主義情懷至今仍未落地,但在那一年后,雙刃拍框的球拍上市,印證了文中提到的設計觀:對單側手持拍、有正反手技術差別的羽毛球運動而言,對稱其實是一種設計上的將就與生產上的妥協。
盡管雙刃拍框不是由3D打印實現的,但至少“不對稱”的設計理念已經開啟。總有一天,最善于制造復雜不規格外觀的3D打印技術,會在球拍行業上實現真正的邊緣創新與顛覆性改造。同樣的道理,不應該對稱的球拍一直對稱,應該對稱的羽毛球毛片一直分左右手。由此看來,即便已經到了2020年,對稱真是羽毛球運動目前還沒過去的—個坎。
在我拿著3d打印的概念去咨詢一些科技達人的時候,他們提供給我的思路卻是另一個概念:生物打印。當年,這種技術的主要研發方向也是人造肉、人造皮革等,樣品已經在實驗室里被生產出來。而“超人”李嘉誠先生也曾揮金千萬美元,投資了美國這家叫Modem Meadow(現代牧場)的初創公司。
5年后回頭盤點3D打印與生物打印技術,我們看到羽毛球行業仍未沾邊。3D打印盡管突破了碳纖復合材料,但是如羽毛球裝備達人Kumache的評價“因為商業打印的缺點很要命拉伸與模量強度都太低,羽毛球拍能打印出來,成品也只能當擺設或給小孩當玩具。它的優點可做復雜件,對羽毛球拍這種模具簡單的產品來說又一點用不上。不過,換個思路,也許打印球拍連釘這些小配件會有用。”也就是說,目前的3D打印“低強而復雜”,羽毛球拍“高強而簡單”,技術與需求截然不同,所以至今未有交集。
對比而言,生物打印在當年的那個思路里,其實是一種培育肉技術,而不是能夠打印生物器官的科幻技術。生物器官這么復雜,是完全不可能用3D打印做出來的。蝦米前輩當年評價碳素羽毛球時就曾提及,禽類羽毛這東西只有上帝才做的出來,哪天人造材料毛片扔水里,跟禽類羽毛一樣能浮起來,才算入了門。我們聽說的生物打印,其實是立體的細胞培養、生物組織培養技術,成熟度不高,離禽類羽毛這種低附加值的東西還仍然遙遠。
曙光與現實總是有著骨感真實的差距,不過有一句話說得好—一“敢夢敢為”。只有有了理想,現實才會逐漸接近我們。如今,我們盤點過去一年的羽毛球裝備技術趨勢,也是為了能夠印證更多的“期待”。正如我們曾經期待人工羽毛球,如今也已經嘗試到了一些人工羽毛球的成品。
[參考資料]
1、《邵恒頭條1中國首款人造肉9月將面市》,邵恒,2019年8月17日2、《熱點:人造肉會讓世界變得更好嗎》,李翔,《知識內參》,2019年5月21日3、《盤點:目前幾家知名的碳纖維3D打印企業》,3D打印在線,搜狐網,2016年2月2日4、《AI改變設計:人工智能時代的設計師生存手冊》,薛志榮,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5、《為啥3D打印做不出人的腎臟?》,“前哨王煜全”專欄,得到APP,2016年8月6日6、《李嘉誠斥資千萬美元投資“3D打印肉”》,《新京報》,2014年6月25日7、《羅胖精選1人造肉是一門好生意嗎?》,羅輯思維,2019年10月6日8、《中國第一塊人造培養肉誕生,具有怎樣的意義?》,蘇澄宇,《知乎日報》,201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