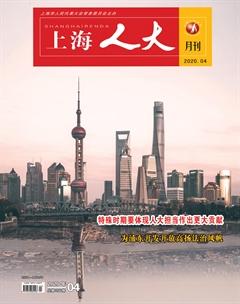對“高空拋物”行為的懲處應明確責任
宋箐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在一座座高樓鱗次櫛比而立時,也產生了來自高空的安全隱患。比如高空拋物現象,曾被稱為“懸在城市上空的痛”,不但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而且帶來很大的社會危害。近年來,高空拋物墜物造成他人損害的事件屢有發生。在社會各方熱議之時,這一社會問題也引起了司法、立法部門的高度重視。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有效預防和依法懲治高空拋物、墜物行為,提出了關于刑事和民事審判的16條具體措施。
同年底,民法典草案侵權責任編對高空拋物的熱點問題也給予了回應,聚焦公眾安全,明確“禁止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的,由侵權人依法承擔侵權責任”。
由此,高空拋物行為既有了入刑標準,也有了民事侵權責任的承擔。但這是否可以讓高空拋物的受害人依法維權,真正獲得賠償了呢?現實未盡然,可以從以前的案例中看案件的爭議點。
2018年4月,在廣州市發生了一起從天而降的狗直接擊中樓下一路過的中年婦女的案子。該婦女后經醫院搶救,命是保住了,但高位截癱。事發后,受害人一家和法院曾全力征集狗主人線索,但至今仍遍尋無果。
這個案例中,受害人維權時,遇到了幾個爭議點:
1、“拋落”還是“墜落”?此案中,既找不到狗的主人,也找不到監控,對于“從天而降”的狗,很難判定是“拋”還是“墜”。
2、狗是“物品”嗎?按照侵權責任法規定,只有“拋擲物品”或者“墜落的物品”才適用高空拋物的責任法則。本案的一個爭議焦點是:狗是活的,是否屬于“物品”?
3、全樓的人都要“連坐”嗎?根據侵權責任法規定,當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時,同一樓的所有住戶都要擔責,除非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本案中,同一棟樓的業主如果不能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則需要一同為受害人的損失買單。但現實中,往往無法執行。
上述案例說明,現有的規定仍有可以補足的空間。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修改之際,筆者認為:
“拋落”“墜落”難界定時,應有原則。前述最高院的意見中強調,要明確區分高空拋物和墜物,二者在責任人主觀方面、社會危害性方面有很大不同,在刑事定罪和民事追責方面也要予以區分。但此案提出了“拋”“墜”難分時如何適用的問題。法院的區分原本是為了刑民有度,更加公平公正,但在難以區分時,恐怕應有原則性適用規定。
“物品”界定應當明示。原先的侵權責任法并未明確“活物”乃“物品”,新修的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也未明確。筆者認為,從廣義看,除了“人”之外,其他的都屬于“物”,包括“活物”。而且動物本身也屬于民事行為的客體。從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目的來看,擴大“物”的范圍,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避免受害方的巨大損失。所以本案中,狗作為“物品”是可以推理出來的。但反觀之,若法律的界定更準確,則可以避免適用中不必要的爭議。
賠償落地,應有新路徑。關于“連坐”的規定,看似不近人情,卻是無奈之舉,是為了保障侵權行為發生后,在沒有找到具體侵權人時,受害方也能得到一定的補償,以避免更大的不公平。但現實中,這一規定缺乏執行力。從目前的侵權責任編草案看,這一規定并未改變。
筆者認為,“連坐”執行不到位,是因為缺乏執行手段。如若是參考保險制度,讓身處高樓林立的人們都有“避險”意識,在購房的時候,就繳納一筆類似物業維修基金的保險基金,對高樓中產生的危害進行預先儲備,則真正遇到類似情形發生時,就可以通過基金的賠償,來解決現實中無法確定加害人而使問題無解的情形。事實上,越是城市建設繁榮,每個人就越有受到高空拋物侵襲的可能。設立一種保險基金,作為一種避險機制,從長效機制上保障受害方的利益,不失為解決賠償落地的新路徑。
民生無小事,字句總關情。衷心希望侵權責任制度能在此次民法典草案修改中愈加完善。
(作者單位:市人大常委會信訪辦公室綜合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