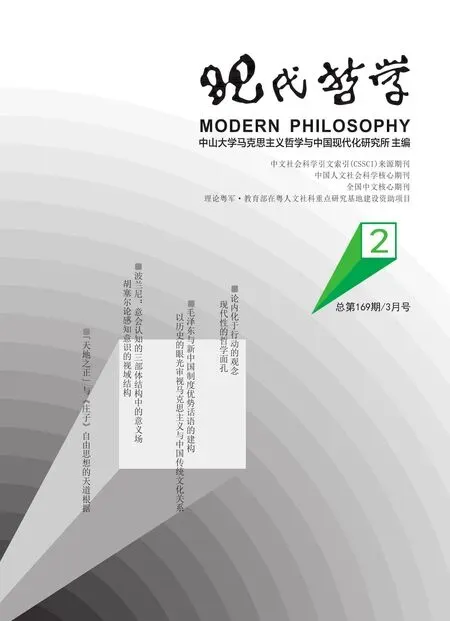“天地之正”與《莊子》自由思想的天道根據
陳 赟
自晚清顧如華、嚴復以“自由”詮釋《莊子》的“逍遙”之后,自由問題就成為《莊子》哲學的最重要論題,甚至被視為其宗旨所系(1)陳赟:《自由之思與莊子哲學的出發點》,《齊魯學刊》2017年第5期。。然而,對《莊子》自由思想的通行理解,往往較強調自由思想的主觀化向度,這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由于忽視了對《莊子》自由思想而言具有本質性的“天地之正”,因而是不充分的,必須進一步從“天地之正”的視角,重新發現自由與天道的關聯。
一、《莊子》自由思想的主觀化解釋之反思
《莊子》對自由的正面論述集中在《逍遙游》,其核心是如下文本:“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這一論述包含相互聯系的兩個層面:一是“乘正御辯”的問題;二是“三無”(即“無己”“無功”“無名”)的智慧。“三無”本身并不是目的,毋寧說它意在通過融化對己、功、名的執著,消解主體對“天地之正”的主觀遮蔽,換言之,對己、功、名執著之消解指向“天地之正”的回歸。對《莊子》而言,“天地之正”是自由的本質所系,它與各正性命的自然秩序密切相關。耐人尋味的是,“天地之正”似乎并沒有成為《莊子》自由思想研究的主導進路(2)楊國榮先生已注意到“天地之正”的問題,精到地強調“天地之正”“不僅僅意味著與存在法則的一致,而且表現為合乎人自身的天性”。《莊子》自由理解的主觀化已成為主流,但仍有必要以天地之正為切入點,重審《莊子》的自由思想。(參見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261頁。)。事實上,《莊子》的自由觀念更多地被置于主觀性領域,譬如被歸結為心理自由、審美自由、精神自由或境界自由。這當然有其合理性,《莊子》的自由哲學本來就有其心理化、審美性、精神性、境界性的向度。但若僅以此定位,限定《莊子》的自由,進而否定《莊子》自由哲學包含著的對建立客觀秩序的要求及其所內蘊著的政治與社會關切,則似有未安。愛蓮心(Robert E.Allinson)斷言《莊子》的主旨在于心靈轉化,這固然不錯,但卻將這一轉化局限于意識內部的主觀性變化:“《莊子》關注的自我轉化模式是主觀理解的轉化的模式;換一種方式說,主觀理解的改變是達到主觀轉化的小徑。”(3)[美]愛蓮心:《向往心靈轉化的莊子:內篇分析》,周熾成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頁。作者在第30頁還進一步確認:“《莊子》的基本目的在于自我轉化:我們必須最終改變我們的理解。”在此,自我轉化并不涉及自我與存在自身的客觀變更,“審美的或前概念的心靈如何參與是準確理解《莊子》信息的一個先決條件”,“《莊子》通過非常強烈地支持審美理解模式的首位性”(4)同上,第29—30頁。。在此,自由與固然之天理、自然之秩序不再相關聯。
自由之主觀化解釋取向的另一表現是,《逍遙游》自由構思中的另一條線索,即“無己”“無功”“無名”。對于《莊子》而言,本來是達到“天地之正”的方式,但往往被作為目的本身加以理解,這就發生《莊子》的自由之思被單向度地理解為無我、自我意識的消解等,其極致是《莊子》的自由思想被誤認為“虛假的自由”,更下者則以其為阿Q式精神勝利法。劉笑敢先生正確地指出了將《莊子》的自由視為阿Q的精神勝利法之不當(5)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8—161頁。,但又將《莊子》之自由化約為與現實無涉的“無心無情”:“如果就精神與現實的關系來說,莊子的精神自由就主要表現為無心無情,無心即無思無慮,無情即無好無惡……就是超然于世外,也就是絕對不動心。”(6)同上,第154頁。劉先生斷言《莊子》“所追求的是現實之外的自由”,自由主體被限定在心靈上,其“所游之處是幻象中的無何有之鄉……歸結起來卻不過是思想虛構的幻化之境,是一種神秘的自由的精神體驗”(7)同上,第158頁。。換言之,自由被歸結為“自由的心境”,“所謂自由的心境要做到‘喜怒哀樂不入于胸次’,即摒絕一切感情意志和思維活動”。這樣,《莊子》的自由就被完全理解為無心式的主觀自由,由于脫離了與現實的關系,故而《莊子》的“精神自由是在命定論的基礎之上幻演出的海市蜃樓……并不能掩蓋他的精神自由消極虛假的本質”(8)同上,第158頁。。《莊子》中的“無情”本意是指“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莊子·德充符》),現在卻被理解為情感的摒棄;《莊子》所謂“無心”本來是指消解意識的妄作,現在卻被理解為意志與思維活動的排除。這種理解最終導向的是《莊子·天下》在討論慎到的“離知去己”思想時所批評的東西:“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這樣的“無心無情”即便作為主觀的審美體驗或境界也不可能,其被視為“虛假”就理所當然了。
《莊子》自由思想的主觀化解釋的后果是,自由完全可以在去政治化、非社會化的情況下被理解,政治社會本身變得無關緊要。對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筆下的《莊子》而言,“政治秩序并不能拯救深深扎根于人類個人心靈之中的人類困境。政治領域正是這種虛假意識的反映,它仍然是不可救贖的世界的一部分擺設”,《莊子》的真人在政治領域“只須適應情境提出的任何要求,并且‘走走過場’”(9)[美]史華茲:《古代中國思想的世界》,程鋼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1頁。。這就無視《逍遙游》中“無功”“無名”“無己”的主體并不是常人而是圣人、至人的事實,這些人格具有不僅自化且能化人的政治向度。在《莊子》中,“無功”“無名”“無己”并不是日常意識中的“功”“名”“己”的消解,而是指有功而不居功、有名而不自居其名、有己而不執著于己的更高境界。但在今天主流語境中,這卻被視為消極地、不加辨別地拒絕一切功、名、己。于是,《莊子》通過無功、無名、無己所表達的相對于有功、有名、有己更高的主體成就,就被措置為一切成就的取消(10)陳赟:《“圣人無名”與自由秩序———兼論〈逍遙游〉中堯與許由的象征意義》,《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進而,《莊子》的取向被誤解為從現實世界的轉化與改變的完全退出,甚至是對人間社會的絕望性放棄。然而,《莊子》中神人的“凝神”,同時具有客觀化的效果——“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莊子·逍遙游》),它意味著現實世界的轉化與改變,一旦這一取向被取消,那么《莊子·天下》以“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11)例如,《大宗師》《天道》將自由主體之“游”與“萬物”“澤及萬世”“覆載天地”“刻雕眾形”等關聯在一起;《應帝王》將“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關聯在一起;《天地篇》闡述自由主體主觀上的“無為”“淵靜”與客觀上的“萬物化”“百姓定”關聯在一起。這些都表明最高自由主體的政治品格,以及內蘊在《莊子》中內圣外王的向度。這一向度要求在主觀的精神修養與家國天下的治平關聯在一起。當然,《莊子》所說的“內圣外王”本來就意味著對圣與王或者教與治兩種事業的以內與外加以結構化的方式。關于內圣外王之道,參見陳赟:《〈莊子·天下篇〉與內圣外王之道》,《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等所表達的“內圣外王”之向度就被消解了(12)陳赟:《論〈莊子·逍遙游〉中藐姑射山神人出場的方式》,《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5期。。
歷史地看,《莊子》自由思想的主觀化解釋,有其社會歷史的背景。隨著六經體制化以及儒學的獨尊,對政治與倫理秩序的思考越來越由儒家壟斷,而《莊子》則以民間思想的形式參與士大夫精神人格而不是客觀秩序的建構。這造成在接受領域《莊子》更多地進入內在領域,成為主觀心靈的符號化表達。于是,在中國文學與藝術世界中,常常看到《莊子》哲學精神的鏡像。這一歷史現實為《莊子》的主觀化解釋提供了條件。更重要的是,伴隨著現代性而產生的“視域下移”,構成現代人理解《莊子》潛在但卻未被顯明的視域。在世俗化時代的今天,“天道”被祛魅,于是對自由思想的理解發生了從“天人之際”到“人人之際”的“視域下移”:自由主體越來越被錯位為“社會人”,而不是“天地人”或“宇宙人”。正是這個“視域下移”,遮蔽了對自由思想之基底的反思能力,自由主體被限制在人與人關系的水平視域,而非人與天之間關系的縱向視域。一般而言,古典時代的自由之思是在人與天道(在西方是上帝)的關系中展開的,可以說它的基軸是縱向性的,以此縱向視域為背景,再去面向政治社會中指向人與人、人與團體或機構之間的橫向關系。然而,在世俗化的現代,自由之思僅僅被置于人類社會歷史的水平性視域之內,天道隱蔽,不再構成自由思想的背景與根基(13)漢斯·昆(Hans Kung)精準概括了在笛卡爾那里所發生的視域轉換:“由于笛卡爾,歐洲思想在一種批判的發展中達到了一個時代的轉折點。原本的確定性已不再寄予上帝,而是寄予人。換句話說,中世紀從上帝確定性推到自我確定性的方式被近代的道路所取代:從自我的確定性到上帝的確定性。”與此相應,海德格爾指出:現代意識其實是把古典世界觀中上帝承擔的角色移植到人的存在中去,于是創造者不再是上帝,而成了人自身,創造在以前是圣經的上帝的事情,而現在則成了人類行為的特性。([瑞]漢斯·昆:《上帝存在嗎?——近代以來上帝問題之回答》,孫向晨譯,香港:道風書社,2002年,第29頁;[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774頁。)。當滿足于人間社會的橫向視域成為思考一切的出發點時,人對自身的理解與界定也就不再求助人類社會、政治及其歷史之外的視野,于是,“社會人”即生活在社會關系及其體制中的存在就被視為人的本質。與這一思想圖像相應,自由不再與超出人間社會善惡價值的至善、與天道秩序(或上帝的恩典、救贖等)相關,而更多地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事物”而被看待。這也正是尼采在所謂“宇宙學價值”的衰落中所表述的東西,而泰勒所謂的世俗化的第三種內涵,即對宗教信仰的價值化,也是與這種自足的人文主義相伴生的(14)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對世俗化的內涵進行了區分:其一,世俗化的公共空間,在所有政治與社會的公共空間,上帝或終極存在的指涉都被清除了,行動所憑借的考量轉變為內在于各個領域的合理性;其二,宗教信仰及其實踐的衰落;其三,對上帝的信仰變成眾多選項之一,而且還是一個不斷受到挑戰的選項。正是在這一發端于拉丁基督教世界但其意義又不限于這個世界的世俗化運動,造成一種自足的人文主義,即不接受任何超越人間福祉的最終目標,亦不熱愛這一福祉之外的任何事物。([加]查爾斯·泰勒:《世俗時代》,張容南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第3—28頁。)。只要在“人人之際”的視域內觀看自由,對于《莊子》自由思想具有本質性的“天地之正”自然就無足輕重。一旦回到《莊子》所處的“大時代”(既是周秦之變的過渡時代,也是中國思想的“軸心奠基”或“哲學突破”時代)語境(15)陳赟:《莊子對孔子的消化:以中國思想的軸心奠基為視域》,《中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就會發現,《莊子》哲學所具有的宏大規模與高遠意境,是在神、明、圣、王四者的連接中重建天下秩序的努力,而絕非僅僅從政治社會與天地宇宙退守到內在主觀領域尋求意識滿足的體驗所可范圍。
二、“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辯”的關系
就《莊子》而言,自由的核心在于“無待”,而“無待”之所以可能在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歷代解釋,紛紜淆亂,難有共識,焦點集中在對“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辯”的關系的理解。歷史上存在兩種理解方式:一是將“六氣之辯”視為“天地之正”的正面展開,一是將六氣之辯視為天地之正的變異或偏離。
第一種理解方式以郭象為代表。郭象以“游于變化之途”來理解“六氣之辯”,是為了承接其“與化為體”的構思(16)郭象云:“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涂也。”此即以其“與化為體”的思路詮釋“六氣之辨”。“與化為體”參見郭象《莊子序》:“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又郭象注《大宗師》“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章時云“與化為體者也”;注《大宗師》“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章亦云“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21、210、223—225頁。)對此的詳盡討論,參見陳赟:《從“無體之體”到“與化為體”》,《船山學刊》2014年第2期。。但郭象對“六氣之辯”的解釋內涵并不明確,經過張默生的闡發,其意義則至為顯白:“御六氣之辯,即是游變化的坦途,大自然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著,我亦隨其變化而變化,即是所謂物來順應,因物付物。決不作執一守故的妄行。如此,則與大化為一,也就是與道為一。”(17)張默生原著、張翰勛校補:《莊子新釋》,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第79頁。顯然,這一思路的重點在于“與化為體”。“與化為體”被視為“與道為一”的方式,也呼應了《天下篇》對圣人的“兆于變化”特點的把握。但這種解釋忽視了《莊子》思想中與“化”的觀念并行的另一面,即“不化”的思想,如《知北游》謂“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則陽》同樣強調“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這里的“不化者”正如《大宗師》所說的“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不化者”不僅與“化者”伴隨,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乃是“化化者”,是使得化成為可能的東西。
第二種理解以郭慶藩為代表,“六氣之辯”被視為“天地之正”的乖變、偏離或悖離。關于“六氣之辯”的“辯”,郭慶藩特別指出:“辯與正對文,辯讀為變。《廣雅》:辯,變也。《易·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荀本作‘變’。辯、變古通用。崔訓和,失之。”(18)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2—23頁。這其實是將“辯”(變)視為“正”之反義詞,則“變”為乖變,是對正、常的變、異。蔡璧名指出,郭慶藩對“六氣之辯”中“變”的理解,值得注意之處“在于他所認為的‘變’,不是五行之氣本身的變化與流轉,即非‘變化’之‘變’;而是‘乖變’之‘變’,即指‘和’的對立面。郭氏同時主‘好怒惡喜樂哀’屬‘北東南西上下’六方之情,認為所謂‘變’所指乃情感失‘和’(平和、調和)之狀態,而非‘好怒惡喜樂哀’本身的變化與流轉。換言之,郭氏之說與前釋‘六氣’為‘陰陽風雨晦明’(或‘風寒暑濕燥火’或‘四/六時之氣’)等殊異。其前所謂‘變’者,均就‘陰陽風雨晦明’(或‘四/六時之氣’)本身的‘變化’更迭而言;而郭氏釋‘變’作‘乖變’之‘變’。”(19)蔡璧名:《莊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新詮》,《大陸雜志》第102卷第4、5期,第196—197頁。六氣之運化有和有乖,和為“天地之正”,意味著萬物皆順遂其本性;乖為“六氣之辯”,意味著六氣的失和、失調,這種失和與失調所形成的結果,是對“天地之正”的偏離,具體落實為本性的非正常變異。“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辯”之間具有一定的張力,就像健康與疾病的關系一樣,健康是人的正常狀態,而疾病是對健康的偏離。正如對疾病的治療,其目的在于恢復健康的常態;對“六氣之辯”的駕馭,其目的在于回歸“天地之正”。如果說“天地之正”道及的是萬物各循其“天守”(“天守”在內篇中相當于事物之“德”,在外篇中關聯事物之“性”)的自然秩序,那么“六氣之辯”則是對之的偏離、扭曲甚至顛覆。當然,這不是說“六氣之辯”不再是自然或外在于自然,而是可以理解為“自然秩序”中的“反結構”(20)關于“反結構”,參見[加]查爾斯·泰勒:《世俗時代》,第60—66頁。自然既可以包含規范性的內涵,即一種與存在者本性相關的秩序,同時也可以指一種與人為相對的自然狀態,近乎天然。自然狀態中既包含自然秩序,也可能包含自然秩序的變異,即作為秩序的對立面的渾沌或失序。本文的自然秩序均是在規范意義上使用,它的內涵無法脫離存在者的本性來思考。。“天地之正”意味著合乎天理、順遂萬物本性的自然秩序,《養生主》“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所表述的就是遵循“天地之正”所體現的秩序;而“六氣之辯”意味著氣化過程中與存在者本性不相應的狀態,可以視為偶然的變合,例如疾病。《莊子》一再出現與“六氣之辯”相關聯的經驗性狀況: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莊子·外物》)
天氣不和,地氣郁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莊子·在宥》)
所謂的“陰陽錯行”,以至于雷電焚燒大樹,雖就是今人所謂的自然現象,有其自然的條理與秩序,但在古典時代卻被視為自然界中發生的有悖“天地之正”的現象,因而被視為“六氣之辯”的表現。例如,疾病是體內六氣失調的結果,其形成與運作有其機制和條理,但不是健康有道的顯現,生理上的有道意味著氣機通暢,以及由此而帶來的身心健康。在人類社會,由于風氣不正而導致的是非錯亂,同樣是“六氣之辯”,而非“天地之正”。
事實上,“天地之正”,并非專屬《莊子》一書的語匯(21)蔡璧名《莊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新詮》一文(《大陸雜志》第102卷第4、5期)對此提供了諸多文獻學的例證。本文對六氣之辯的理解以及所使用的例證,都參考了蔡文。。一個思想家所使用的語匯,必須納入到其所在的語言共同體,尤其是同時代的文本的互文中,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逸周書·周月解》)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鬼谷子·本經陰符》)
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羅瑞顯然有點著急了,結結巴巴地解釋:“我也沒想到她會那么激動,我不是故意的。哎,警官大人,你不會懷疑我吧?!我可沒殺她!”
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管子·四時》)
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變至則病。(《黃帝內經·六節藏象論》)
據此,“天地之正”意味著正常性的自然秩序,而“六氣之辯”的“辯”即“變”,意味著“非常”即不正常,或者說正常秩序的變異、偏離。事實上,《論衡·自紀》將這種意義上的“變”與“異”“妖”“怪”等并列合觀:“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于眾而突出曰怪。”這就是說,它們同屬一個不正、非常的序列,“變氣不僅會使得人體氣血紛擾失調,甚至萬物亦將隨之而害病”(22)蔡璧名:《莊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新詮》,《大陸雜志》第102卷第4、5期,第201頁。。由此,“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內涵,當與《管子·侈靡》所謂的“天之變氣,應之以正”相當。《在宥》關于“六氣不調”的陳述正是“六氣之辯”的表現,故而它與天氣、地氣、四時等失序、失和聯系在一起,構成對各正性命的秩序的悖反。《在宥》所謂的“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即是轉化失調的六氣,使其歸于正常,從而可以接續繼承天地生養萬物的事業。《外物篇》提及“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與《漁父》所謂“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皆屬上述意義上的“六氣之辯”(23)蘇轍《再論分別邪正札子》云:“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這也從另一層面顯示:天地之正,必然顯現為陰陽之和。。許多解釋者引用《左傳》昭公元年的文本,對《逍遙游》的“六氣”進行解釋。耐人尋味的是,該文本正好強調了六氣的變異:“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24)[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8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342頁。基于這一文本,奚侗強調說:“氣過則為災,所謂‘六氣之辯’也。”(25)奚侗:《莊子補注》,方勇:《莊子纂要》第1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第73頁。顯然,奚侗也突出了“六氣之辯”意味著六氣之失和。
毫無疑問,郭慶藩對“六氣之辯(變)”中“變”的解釋,核心在于“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辯”二者的關系。其要點在于,“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辯”之間存在張力,后者是對前者的乖變、偏離或變異。而通常的理解,如郭象、張默生等強調的是后者乃是前者的展開與體現,即強調“天地之正”與“六氣之辯”的一致性。退一步說,即便“六氣之辯”的“辯”同時包含負面的“乖變”之“變”與中性的“變化”之“變”,“六氣之辯”仍然可以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天地之正的體現,二是天地之正的偏離。因為存在著偏離的趨向,所以才有“燮理陰陽”(26)《尚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這一表述意味著,雖然陰陽本是自然的變化,但人對之的燮理仍有必要。的必要。可以肯定,對于六氣的運化,無論是《莊子》還是同時期的孟子、荀子,都不會采取完全被動的順從與因任,否則,主體的修養與社會政治行動對于六氣運作的介入就失去正當性,意味著《莊子》哲學淪落為對于一切經驗性現實的無抵御、無介入、無變化的簡單順從。將郭慶藩與郭象為代表的兩種解釋綜合起來的可能方式,就是承認六氣之變化的兩種可能方式,即合乎萬物本性(天地之正)的狀態與偏離萬物本性的狀態,這也要求承認“六氣之辯”與“天地之正”之間可能存在著的緊張。
盡管歷代解《莊》者對“六氣之辯”有眾多不同理解,但郭慶藩對其具體內涵的總結提煉堪為經典:
六氣之說,聚訟棼如,莫衷一是。愚謂有二說焉:一,《洪范》雨旸燠寒風時為六氣也。雨,木也;旸,金也;燠,火也;寒,水也;風,土也;是為五氣。五氣得時,是為五行之和氣,合之則為六氣。氣有和有乖,乖則變也,變則宜有以御之,故曰御六氣之辯。一,六氣即六情也。《漢書翼奉傳》奉又引師說六情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此二說似亦可備參證。(2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2頁。
郭慶藩正確地指出六氣包含兩種不同的含義:在內,為好、惡、喜、怒、哀、樂之六“情”;在外,則為自然界中的雨、旸、燠、寒、風、時等運化的六“氣”(28)當然,在天人感應的擬人化的神話宇宙中,內之六情與外之六氣相感相通,如《史記·天官書》正義曰:“軒轅……主雷雨之神。陰陽交感,激為雷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云氣,立為虹霓,離為背譎,分為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但對他而言,六氣的上述兩種內涵只是可備參證的未成共識的觀點,他未能明確兩種含義其實可以并行不悖、相輔相成,六氣之在外者謂之雨、旸、燠、寒等,在內者謂之好、惡、喜、怒等,因此,六氣在人之身內與身外有所不同。其實,《在宥》已經涉及六氣的上述兩層內涵:
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后有盜、跖、曾史之行。
在內的六情不和,與在外的陰陽四時寒暑之不正一樣,傷人之形,不能居常;而且,在內之六氣與在外之六氣,相互影響,彼此感應。調整六情,使之歸于和平中正,正是“御六氣之辯”的題中應有之意。《管子·戒》也以人的“好惡喜怒哀樂”構成“六氣之辯”的內容,如下的言述可以與《莊子》對勘:
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辯,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無定生,圣也。
借助于王船山富有啟發性的詮釋,可以進一步地將主體身外的六氣概括為“勢”,即某種不可逆的現實化的趨勢;將身內之六氣界定為“情”,即人的主觀情感。由此,對“天地之正”的偏離就主要包含內外兩個因素:在外,為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客觀的氣化之“勢”,作為某種不可逆的必然趨勢;在內,為人之喜怒哀樂等所體現的主觀之“情”(29)王夫之《莊子通·逍遙游》:“夫大非不能笑,不能小者,勢使之然也。小非不能大;不能大者,情使之然也。”“勢之困尤甚于情。情有炯明,而勢善迷,豈不甚乎!”([明]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3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495、496頁。)。客觀之“勢”若偏離“天理”(自然而然的秩序、條理),主觀之“情”若有悖本性,則皆為六氣之乖逆,是為“六氣之辯”;氣化之勢若與天理和諧,主觀之情若與本性協調,則為和順,即為“天地之正”。換言之,在內之六情,在外之六氣所成之勢,都可能導致對“天地之正”即各正性命的秩序的偏離或背反,因而需要掌控、調御,以使之歸正(30)“御六氣之辯”的“御”一般被解釋為“乘”的互文,如聞一多的《莊子校釋》。然而,當“六氣之辯”指人的六情之變時,如在《管子》《韓詩外傳》中,這時“乘”顯然于義不合,聞一多轉釋為調節。而奚侗釋御為“止,與馭同。乘天地之正氣而御其變氣”。事實上,《管子·戒》云:“御正六氣之辯。”顯然,“御”的目的是使之“正”。(方勇:《莊子纂要》第1冊,第73頁。)。
這樣,“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核心仍然落在“天地之正”。問題被轉義為:《逍遙游》的“無待”自由何以無法脫離“天地之正”?
三、作為自由根據的“天地之正”
郭象在解釋“乘天地之正”時指出:“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31)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1頁。這一解釋構成歷代解《莊》者的共識。何以“天地之正”被理解為這樣一種秩序,即萬物各各遵循其本性而形成的秩序?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明白天地與萬物的關系。在《莊子》中,“天地”往往與“萬物”相連,但二者并非同一層次的概念。譬如《齊物論》“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德充符》“官天地,府萬物”;《天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天道》“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外天地,遺萬物”,等等。《天道》觸及天地與萬物的關系:“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在這里,《天道》顯然是在敘述帝王之德與天地之德二者之間的相配,萬物之化,萬物之育,顯然都是天地之功、天地之能的顯現;問題的核心是,“天不產”且“地不長”,然而萬物化、萬物育,這就彰顯了天地之功、天地之能的如下的特點,即天地之生育萬物實則讓萬物之自生自育,但萬物之自生自育之能卻源自天地。故而,天地對于萬物的生養之德,展現了一種無功之功、無為之為。由此就不難理解《至樂》以無為而無不為概括天地的德性:“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從中國思想的“外部視域”看,譬如從中國古典思想與古希臘、古印度、古希伯來傳統的對照中看,《莊子》關于天地與萬物的思想與《論語·陽貨》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處在同一思想譜系與傳統之中(32)如果限于中國哲學的區域,對《莊子》的探究而言,儒道差異就是不得不面對的課題。但考慮到古今中西之爭的現代語境以及跨文明的深層比較視野,儒道差異相對于中國思想與文明論意義上他者的差異,其間距也就可以忽略不計。。事實上,《知北游》如下的言述可以視為對上言的呼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至人無為、大圣不作的本體論根據正在于天地對萬物的無功之功、無為之為,即讓萬物自生自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大德。所以,在《莊子》中,天地是萬物的創生者,這種創生意義被比喻為父母與子女的關系。《達生》有謂:“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天地與萬物之間的如上關系,恰恰勾勒了一種以“自然”為核心的天地秩序。郭象在解釋“天地之正”時直指這一秩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37)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1頁。郭象將“天地之正”落實為“萬物之性”,這種從萬物之性講“天地之正”的思路特別值得注意。天地以萬物為體,在萬物之外別無所謂天地,因而“天地之正”中的“天地”不能離開萬物來說。由此,“天地之正”具體展開為萬物之性在其中得以生成的自然秩序;“自然”既意味著自己而然、非由外力,因而自然與存在者自身的主動構成自我不可分割;另一方面,自然又表達了某種深層的純粹被動性,即便是存在者自我構成、自我成就的能力最終也來源于“天命”,即一種沒有施動主體的被給予性。譬如,人的自我成就的能力,與草木據其本能而生長,其實具有共同的根據。在更高層次上,并非人與草木的能力都是自己的作品,而是源自某種被給予性;既然是被給予的能力,那么就有著與生俱來的限制。譬如,人的會說某種語言的說話能力,雖然通過人的學習過程展現出來,看起來似乎是人的作品,但只要相對于其他存在者,就可以看出它是人的“不為而自能”的“自然”,畢竟其他存在者即便通過學也無法獲得擁有運用語言說話甚至書寫的能力。學習過程對于人之擁有并運用語言的言語能力而言,并不是創造、建構這種能力的“為”,相反只是展現這種“被給予”的能力。因此,它既不是人的自我建構的能力,也不是可以由他者所剝奪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運用語言說話是“天地之正”在人性能力中的自然體現。也可以說,人類的文化創造在更高層次可以視為人的“自然”,但卻并非其他存在者的“自然”;文化既是人的作品,又是更高層次的被給予性,甚至人的文化創造能力本身也可以在被給予性維度上來理解(38)事實上,《莊子》中的“自然”,并不能簡單地被視為現代日常語言意義上“自然界”之“自然”,而是“人文”的一種形式。關于道家的人文主義的討論,參見王博:《道家人文精神的特質》,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22輯,第50—74頁;劉笑敢:《人文自然與人類和諧》,《詮釋與定向——中國哲學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75—414頁。。進一步,“天地之正”最終落實到萬物的本性并通過后者表現出來:一方面,作為本性,它乃萬物在大化之流中建立的“外化而內不化”的本質屬性,標志著某一存在者之為其自身的同一性的本質,這些都是不由外爍的;另一方面,作為本性,它又得之于“天”,即得之于“自然”,即它被授予卻并沒有一個外在于它自身的授予者,天地本身乃是天道本身都不能被視為實體化的授予者。王夫之指出:“天不能使人處乎自然。”(39)[明]王夫之:《船山全書》第2冊,第340頁。“自然”本身并非完成,并非“現成”,而是離不開存在者的自身參與自我證成。“天地之正”作為一種各正性命的自然秩序,它是開放性的,在現實性上具有變異的可能性,因而自然本性也需要通過存在者自身的存在與勞作來展現。各正性命的自然秩序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與其他存在者一樣,人也是這一秩序的構成部分,人對自然秩序的投入與融入,與人自己建構自己的活動,都是參與這種秩序的構成性環節(40)正是基于人物之性命與天地之正的上述關聯,我們才能看到如下的表述:“故嘗原君子之出于斯世,惟其與天地立道,故可與生民立極。生民之極,同受命于天地,而君子獨以一身周旋其中。蓋得于天地者,粹然之正猶故也。存吾靜一之性,皆天地之正性;知吾順受之命,皆天地之正命;又養吾剛大之氣,無非天地之正氣。”(《永樂大典》卷3800)。而自由就是參與這種秩序的構成,以那種深層的來自天道的被給予性為基礎,建構自己、實現自身本性的能力。這種能力既然是沒有給予者的給予,因而既無法被某種存在者所賦予,也無法被其剝奪,自由展現為這一存在者得之于天而成之于己的那種特有的東西。所謂得之于天,觸及到這種深層的被給予性,人的自由的根據由此而被給出,不僅對人與萬物所置身其中的自然秩序,而且對存在者本性及其能力的理解,都無法脫離上述被給予性,這種沒有給予性的給予性就是天道,它是自由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