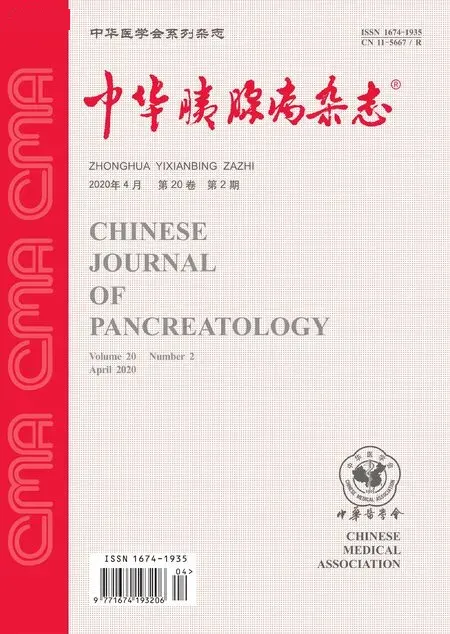急性胰腺炎伴發中心靜脈導管相關血流感染的危險因素與病原學分析
陶緣發 榮愈平 陶京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胰腺外科,武漢 430060
AP是一種常見的臨床急腹癥,輕癥者多以胰腺水腫為主,易于治療,且恢復快,預后良好[1];少數患者可發展為MSAP甚至SAP,出現胰腺壞死、出血、腹腔感染等,病死率高[2-3]。因病情危重,腸內營養難以足量給予,往往需要留置中心靜脈導管用于輸液、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和腸外營養,這可能引起中心靜脈導管相關感染,尤其以導管相關血流感染(catheter-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CRBSI)最為嚴重,不僅增加患者痛苦,延長住院時間,且會增加住院費用和病死率[4]。現有研究表明導管留置天數、穿刺部位、經導管輸血、經導管輸注脂肪乳和糖尿病等為CRBSI的危險因素[5-7],然而上述研究結論多來自于整個醫療中心或重癥監護室患者資料,罕見針對特定疾病的CRBSI流行病學研究。本研究回顧性分析MSAP及SAP患者伴發CRBSI的危險因素,并分析其病原學資料,為AP伴發CRBSI的預防和診治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收集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間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胰腺外科收治的行中心靜脈置管的MASP和SAP患者的臨床資料。排除標準:(1)入院前已出現可疑CRBSI者;(2)已出現菌血癥者;(3)留置中心靜脈導管不超過48 h者;(4)留置中心靜脈導管2 d內死亡者。將發生CRBSI者歸為感染組,未出現感染者按1∶1比例與感染組匹配后作為對照組。匹配條件:(1)年齡相差≤3歲;(2)性別比例一致;(3)是否合并糖尿病;(4)是否經中心靜脈導管輸血;(5)是否經中心靜脈導管輸注腸外營養;(6)穿刺部位;(7)導管留置時間相差≤3 d。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在置入中心靜脈導管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二、CRBSI診斷標準
根據2009年美國感染病學會指南[8]留取標本行病原學檢測。方法如下:(1)拔除中心靜脈導管時將尖端5 cm送檢。(2)留取2套血培養標本,其中1套從中心靜脈導管抽血,另1套從外周血抽取;如果外周血留取困難,可經雙腔中心靜脈導管的兩個管腔各留取1套血培養。當導管尖端菌落數半定量培養>15 CFU或定量培養>102CFU時可判定導管定植。當培養結果滿足下列任何一條時可診斷為CRBSI:(1)至少1次外周血培養陽性,導管尖端半定量培養菌落數>15 CFU或定量培養>102CFU,且為同種細菌;(2)導管血和外周血均為同一細菌,且導管血定量培養菌落數是外周血的至少3倍;(3)導管血和外周血均為同一細菌,前者報告陽性時間比后者至少早2 h;(4)從雙腔中心靜脈導管兩個管腔各自留取血標本培養為同一細菌,且一個管腔血定量培養菌落數是另一管腔血的至少3倍。
三、統計學處理

結 果
一、一般資料和臨床特征
共收集352例MSAP和SAP且留置中心靜脈導管的患者,其中男性219例,女性133例,總計留置導管天數為4 517 d。39例發生CRBSI,感染發生率為11.08%(39/352),8.83例/1 000留置導管日。39例CEBSI患者中男性23例,女性16例,中位年齡45歲,發生CRBSI的中位天數為17 d。35例在病原學確診前拔除導管,4例在確診后立即拔除導管。CRBSI導致膿毒癥7例,無感染造成死亡病例。CRBSI組和對照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和臨床特征見表1。

表1 CRBSI組及對照組患者的臨床特征
注:CRBSI為導管相關血流感染;AP為急性胰腺炎;MSAP為中度重癥急性胰腺炎;SAP為重癥急性胰腺炎;APACHEⅡ為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指標評估,表中評分為留置導管期間最差的一次評分;-為無數據
二、AP患者伴發CRBSI的危險因素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合并腹腔感染(留置導管前1周及留置導管期間同時合并腹腔感染)、APACHEⅡ評分≥20分(留置導管期間最差的一次評分)為發生CRBSI的獨立危險因素,而早期腸內營養(入院后48 h內)是其保護因素,留置導管前3 d內及留置導管期間使用抗菌藥物與是否發生CRBSI無關(表2)。

表2 AP患者發生CRBSI的危險因素
注:AP為急性胰腺炎;CRBSI為導管相關血流感染;APACHEⅡ為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指標評估
三、AP伴發CRBSI患者的病原菌分布
39例CRBSI患者共分離出病原菌43株。革蘭陰性菌25株,占58.1%(25/43),其中肺炎克雷伯菌19株,大腸埃希菌3株,產酸克雷伯桿菌、陰溝腸桿菌及鮑曼不動桿菌各1株;革蘭陽性菌7株,占16.3%(7/43),其中屎腸球菌4株,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 hylococcus aureus, MRSA)3株;假絲酵母菌11株,占25.6%(11/43),其中熱帶假絲酵母菌7株,白假絲酵母菌3株,光滑假絲酵母菌1株。
細菌耐藥方面,多重耐藥菌檢出比例高達67.4%(29/43)。3株大腸埃希菌均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beta lactamase, ESBL)。1株產酸克雷伯桿菌亦產ESBL。15株產ESBL的肺炎克雷伯桿菌中2株對碳青霉烯類耐藥,唯一的1株鮑曼不動桿菌為廣泛耐藥菌株。4株屎腸球菌和3株MRSA僅對糖肽類、利奈唑胺等少數抗菌藥物敏感。熱帶假絲酵母菌對氟康唑耐藥率較高,達57.1%(4/7),1株光滑假絲酵母菌對氟康唑劑量依賴性敏感,其余菌株對氟康唑保持敏感性。
討 論
中心靜脈導管在臨床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在重癥監護病房搶救工作中必不可少。AP由于存在血流動力學紊亂,腸功能障礙導致腸內營養不足,以及長期輸液治療等,往往需要留置中心靜脈導管。CRBSI的發生率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或地區差異較大,發達國家或地區的CRBSI發生率普遍低于不發達國家或地區[9]。在發達國家中,法國的CRBSI發病率最低,約為0.9例/1 000留置導管日。而一項涉及36個國家的研究結果顯示,CRBSI發生率約為6例/1 000留置導管日[10]。本組AP的CRBSI發生率為8.83例/1 000留置導管日,處于較高水平;發生CRBSI的中位天數為17 d。中心靜脈導管留置時間過長可能為AP患者CRBSI發生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文獻報道,留置中心靜脈導管>15 d者較<15 d者發生CRBSI的風險更高[11]。相當多的MSAP和SAP患者留置中心靜脈導管超過2周,CRBSI發生率隨之升高。國內有研究報道發生CRBSI的重癥監護室患者病死率達40.9%[12],高于突尼斯一家醫院報道的21.8%[5]。本研究CRBSI患者無1例死亡,可能與發生CRBSI后均及時拔除了中心靜脈導管并積極抗感染治療有關。
文獻報道穿刺部位、腸外營養、輸血和合并糖尿病等為發生CRBSI的危險因素[5,7],可能的危險因素還包括年齡[13]、性別[14]等。本研究將合并腹腔感染、APACHEⅡ評分≥20分、是否早期腸內營養和抗菌藥物作為AP發生CRBSI可能的危險因素納入回歸分析,是基于CRBSI的發病機制做出的設想。腹腔感染時極有可能發生一過性或持續性菌血癥。雖然大多數細菌被免疫系統和抗菌藥物清除,但少量細菌隨血流播散定植在中心靜脈導管尖端,增殖聚集并形成生物被膜,這可能是AP患者發生CRBSI感染發病機制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本研究結果顯示,置入中心靜脈導管期間合并腹腔感染是發生CRBSI的危險因素,印證了課題的設想。文獻報道APACHEⅡ評分是重癥監護室患者發生CRBSI的危險因素[12,15],可能的機制是基于病情危重時機體抵抗力低下,細菌易于通過破損的皮膚黏膜屏障侵入造成。Cheng等[16]研究提示,APACHEⅡ評分≥20分與留置導管患者發生CRBSI相關。而相當多的MSAP和SAP患者APACHEⅡ評分很高,因此本研究將該評分納入模型進行分析,再次驗證了APACHEⅡ評分≥20也是AP患者發生CRBSI的危險因素。有研究表明,早期腸內營養甚至腸內滋養能有效地維持腸黏膜屏障的完整性,防止腸內菌群易位,從而降低全身性感染的發生風險[17]。本研究結果表明,早期腸內營養是降低AP患者CRBSI發生的保護性因素,同樣是基于在病程最早期應注意維護腸黏膜屏障的原理。2009年發布的美國感染病學會指南并未涉及是否需用抗菌藥物預防CRBSI[8]。本研究中部分病例留置中心靜脈導管期間使用抗菌藥物,并非用于預防CRBSI,而是治療其他部位的感染,尚不能確定抗菌藥物是否增加或減少CRBSI的發生風險,有關抗菌藥物是否能預防CRBSI,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多篇文獻報道,革蘭陽性菌是CRBSI最主要的病原體[8,18]。本研究革蘭陰性菌,尤其是肺炎克雷伯菌是AP患者發生CRBSI的最常見病原菌,其次是假絲酵母菌屬,最后才是革蘭陽性菌(主要為腸球菌,未檢出凝固酶陰性的葡萄球菌),與文獻報道的不完全一致。從大多數病原菌為腸道定植菌推測,AP并發的腹腔感染或腸黏膜屏障破壞導致的腸道菌群易位可能是發生CRBSI最重要的機制。而耐藥菌比例居高不下的現實再次說明合理使用抗感染藥物和加強醫院感染管理的重要性。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選擇性偏倚。研究數據來自單中心,而不同醫院、地區的病原學分布,細菌耐藥情況以及醫院感染管控均有差異,故本研究結論可能不具有普遍代表性。雖然本研究將病例資料采用1∶1配對后再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以減少協變量的數量,但感染組的樣本量偏少,仍有可能造成回歸模型不夠穩健。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