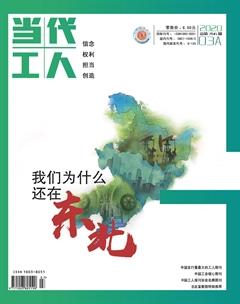在父輩的旗幟下
夭夭

曾經的艷陽天
我們為什么還在東北?
1976年9月,擁擠的下班路上,人群突然向兩側退去,自發讓出一條通道,敲鑼打鼓的儀仗隊緩緩走過,后面跟著數十輛大解放,車斗里站滿身穿工裝、胸別紅花的老工人,他們一手拎著裝有臉盆、搪瓷缸子、糖果的網兜,一手向行人擺手,大人們回以熱烈的掌聲,孩童們則追著車子瘋跑嬉鬧、討糖吃……
“儀式像御街夸官,但不是中狀元,而是光榮退休了。”鞍鋼退休工人田力解釋,御街夸官也叫游街夸官,是古代制度,指新科狀元殿試欽點之后,由排列鼓樂儀仗鳴鑼開道,在皇城主干道上走過,接受朝賀的儀式,目的是激勵眾人以此為標桿,積極上進。
鞍鋼仿照夸官辦退休儀式并非孤本,而是在各大企業廠礦間,流行了近20年的常規節目。可即便如此,仍歷久彌新,甚至在工廠社會化功能的疊加作用下,潛移默化出“工人即榮耀”的社會認同。
“當時我13歲,吃著工廠發給爺爺的退休喜糖,喝著父親從車間打來的鹽汽水,坐在媽媽的自行車上原地亂蹬,生活簡直太美好了,恨不得見人就報告:‘咱一家都是工人,我長大后也是。”現實還真不出田力所料,高中畢業后,充分備考的他從眾人中脫穎而出,成了一名鞍鋼工人。
與生于新中國老工業重鎮的田力不同,百公里外,廣袤的紅海灘上,李錦華又是另一番感受。
還是1976年,歡喜嶺采油廠在盤錦正式建廠,荒涼的鹽堿沼澤和蘆葦蕩迎來了全國各地奔赴而來的石油工人,他們在帳篷里安了家,一邊搭基建、一邊搞生產,奏起了遼河油田的創業序曲。
年幼的李錦華跟著父親李春財,從老家搬到盤錦,身份也隨之改變——由農二代變身工二代。父親夜以繼日忘我勞作的身影,田野中紅彤彤的特有榮耀(采油工人的工裝是紅色的),印在她的心里,更生成一種驕傲和自豪,令她心甘情愿走入父親規劃好的結局:從油田幼兒園到油田小學,再到油田技校,最后被分配回油田工作,為名副其實的工二代畫上圓滿的句號。
“一身工裝,扎兩條麻花小辮走上街頭,用現在的流行語形容,我就是這條街上最靚的仔。”李錦華打趣。
的確,那是一個火熱的年代,工人們生龍活虎、爭分奪秒地勞作,不僅厚積了工業強國的黑色土壤,更強化了當工人的體面與榮光,“連對象都好找咧。”
當時流行這樣一個順口溜:一年車子二年表(自行車和手表),三年就把對象找。“住廠子分的房,食堂管飽還能外帶,看病廠里有醫院,孩子上學小初高全包。生活上沒顧慮,職業穩定還有面兒,能不搶手嗎。”
無論主動出擊,還是按部就班,在很長一段歷史長河中,工人無異是大多數人理想職業的首選。如此看來,1976年也真是一個有趣的年份,它跨越地域將人們連接起來,用無數個體的親身經歷,替一個時代宣告:我們為什么還在東北。
時有落花至
告別了1976年,再來看看后來是如何作答。
“怎么,國營廠還能倒閉?怎么,工人鐵飯碗還能打破?”1986年,擁有70多名工人的沈陽防爆器械廠,成為中國第一家正式宣布破產的公有制企業;1992年,在媒體熱烈鼓噪和“徐州經驗”啟發下,中國大型企業——本溪鋼鐵,第一次打破鐵飯碗,10.6萬名職工實行全員合同制……陣陣驚雷,震動了整個鐵西區、沈陽市、遼寧省,乃至國內外。
那時的鐵西,流行一首叫《下崗工人》的歌:習慣了接訂單的手,今天的指尖流出彷徨;裝工資的口袋,今天寫滿空蕩……
“我穿工裝回廠辦事,在廠門口,一個小孩吵著要去公園玩,媽媽不同意,指著路過的我說:‘趕快回家寫作業,現在不好好學習,就得像他那樣進廠當工人。”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獲得者、鉚工楊建華心里難受極了,但也只能暗自無奈地嘆氣。
就在這樣一個風口浪尖上,卻仍有一群人考技校、鉆技術、進工廠,田力就是其中一員。“家住工人街、工業路,祖輩、父母、叔伯,親朋鄰居全是工人,作為工三代的我,除了工廠,真不知道還能去哪兒,干點兒啥。”田力坦言。
為什么工人子弟一定要是工人?英國人類學家保羅·威利斯早已給出答案:既不是他們笨,也不是他們不努力、不改變,而是他們主動選擇走上父輩的老路。
往大了說,“一個大國強國,怎能少了工業?總要有一群人去支撐它的發展,不至于出現人的斷層和流失。往小了說,上一代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這一切,對于我們下一代也最熟悉,也最穩妥。”田力坦言,蕓蕓眾生不是西部牛仔,不靠冒險精神過日子。
然而,仍有許多人把東北的惆悵、難解的改革命題、轉型的陣痛、近乎偏執的堅守,統統歸咎到東北人自身的懶惰上。
在《丑陋的中國人》書中,柏楊對東北最刺眼的攻擊即東北人懶惰,稱可能是當年幫助日本人做事“磨洋工”習慣了;在《鳳凰周刊》刊登的《振興東北,先震東北人》一文里,東北籍作者激憤地指出:懶成了現代東北人的通病,許多青年寧愿游走江湖、給人看場,以期一朝富貴,也不愿意本分地干活兒,靠勤勞吃飯。盲從的自媒體時代,諸如“逃離東北”“10年流失400萬人”“冷清凋敝,難見青年,滿目銀發族”“過年返鄉票東北最難買”,危言聳聽且缺乏考究的蒼白觀感甚囂塵上……“他們為何‘自甘如此”的疑問也開始充斥網絡。
作家謝景芳曾說過:“歷史是一種提供豐富選擇的源頭,歷史是一種選擇性的記憶。”通俗地講,就是大家都說要銘記歷史,但真銘記起來,卻往往是有選擇性的,正如我們記住了東北在九一八事變中的淪陷,9月18日在社交媒體打卡“勿忘國恥”,但我們卻模糊了,從一開始,東北就是工業文明產物的現實。
20世紀20年代,遼寧就有30多萬產業工人,走在全國前列,而這一形象,又在1949年建國后被強化,在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東北落地了156個國家重點工業項目中的54個,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單拎出來一個沈陽,就為全國提供過20萬臺擊穿設備、60萬臺冶金設備、2億千伏安的變壓器、40萬中級和高級人才,直至20世紀90年代,東北都是全國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
所以,請不要斷章取義,否則,鋼鐵、飛機、輪船的種種,無數個昭示世界的第一,以及改變世界產業格局的物質力量,就不會拔地而起。否則,在工廠社會化架構的城市文化系統中,在車床輪轉、世代交替間,以“懶惰”二字來帶動傳播共鳴,詮釋固守一地、身肩重任,一代代傳承和強化了的職業認同,勢必被歸為嘩眾取寵——對人間厚重的不體諒和對生活察看的輕浮。
不僅如此,1999年的春晚,還給出了另一種回擊。那年正值國企改革,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飾演下崗工人的黃宏,在小品《打氣兒》中喊出這樣一段自白:“誰都能一帆風順?誰這輩子還不遇上點兒事?就拿我來說吧,過去大小也算個干部。不是跟你吹,18歲畢業我就到了自行車廠,先入團后入黨,上過三次光榮榜,廠長特別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組長。領導一直跟我談話,說單位減員要并廠,當時我就表了態,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這些被稱為經濟轉軌過程中必然反應,本應是弱勢一方的群體,以平靜的姿態默默承受歷史轉型的斷臂之痛,承載了某種社會發展的宿命,為技術升級、國企改革和騰飛爭取了時間。試問當下還有何種理由,因整個國家都在跑步前進,而忽略了那些被撞到的人呢?
清輝照衣裳
隨著國家有關東北振興的政策紅利不斷釋放,投向東北的資本漸如過 江之鯽魚。
2018年,毛振華控訴當地政府嚴重侵占民營企業權益的聲音還未消失,“投資不過山海關”的風向就已經有所轉變,王健林800億元投到沈陽,馬化騰和馬云也頻繁動作,騰訊與遼寧省人民政府牽手打造“數字遼寧”,阿里巴巴和黑龍江省共建“數字龍江”,深圳大象文化科技產業有限公司等168個項目簽約,總投資1869億元。
與此同時,在全國百萬城市白熱化的人才競爭戰中,東北的“回振”讓人眼前一亮,如智聯招聘對全國37個主要城市的招聘數據監測發現,2018年春、夏兩季,沈陽地區人才供需競爭指數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國第三位。電商平臺大數據統計顯示,沈陽的高校畢業生本地居留率高達49%,僅次于北京的51%,居全國第二位。
回眸過往,在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布局謀篇中,為先鋒、為時代沖鋒陷陣的工人們,縱使迷茫彷徨,但從未膽怯,更在改革開放宏大的舞臺之上,完成華麗轉身——撕掉了“技術技能素質不高”的標簽,伴隨著80后、90后專業技術人才的加入,“工人榮耀”也開始演化出新的注腳。
“祖輩們付諸一生的事業,怎能輕言放棄。或許是受前輩們無形的影響,又或許是緣分已然注定,我2009年大學畢業后,通過招聘考進工廠,成為生產線上的一名普通軋鋼工人。”李亮坦言,爐膛里沸騰的鐵水,數千度的高溫,什么都可以熔化,卻熔化不了工人煉鋼的決心,煉鋼爐發出咆哮,似乎在唱著讓人遐想的堅持之歌。
想必看到這里你終會明白,我們親切喚作工一代、工二代、工三代……工N代的他們,究竟為什么還在東北,正如歌中吟唱: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
也不知要有多難才能睜開雙眼
我從遠方趕來 恰巧你們也在
我在這里啊
就在這里啊
像夏花一樣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