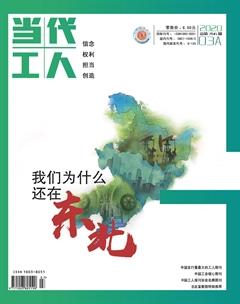深陷“興奮劑困局”的俄羅斯
和曉強
體育比賽與興奮劑結緣
體育是人類文明的產物。長期以來,受人們積極參與和熱情謳歌,也形成了應有的體育規范和體育道德。人們以“更高、更快、更強”為標準,以“挑戰生命、超越極限”來自我鞭策,形成了一次又一次被打破的世界紀錄,造就了無數優秀的體育健兒和團隊。現代醫學和科技的發展使人們在為冠軍歡呼雀躍,聆聽獲勝者背后的國家國歌奏響,看到其國旗升起時,也讓硬幣的另一面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運動員自身乃至被國家鼓勵作弊服用興奮劑成為體育界的一大丑聞。
興奮劑,其實是一類特效藥物或者生理制劑的統稱,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能夠增強或者輔助運動員增強體能或控制能力,提高比賽成績。在當今體育界,興奮劑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追溯其歷史如同體育發展史一般也是源遠流長。據說,最早登上現代體育舞臺的興奮劑是鴉片,英國傳統的耐力賽跑則是現代體育使用興奮劑的源頭。1807年,參賽者亞伯拉罕·伍德聲稱因為自己使用了鴉片酊才保持24小時一直清醒,擊敗了其他選手。
在那個時代,使用藥物參賽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而是一種新的“科學”方法,伍德的經驗迅速得到推廣,并產生令人難以置信的結果。1877年,英國耐力賽的奪冠成績達到了500英里。一年之后,最好成績被提高到520英里,冠軍為此連續奔跑達138小時。
興奮劑的奇效迅速在體育界傳播。在美國,著名的六天自行車耐力賽的參賽選手大規模使用可卡因是個公開的秘密。1896年,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雅典拉開帷幕,同樣吸引了興奮劑的參與。其后,諸多的世界性體育比賽都有運動員服用興奮劑。彼時,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興奮劑的危害,使用興奮劑被視為合法。
到了20世紀20年代,人們逐漸意識到有必要限制在體育運動中使用此類物質。然而,當時人們缺乏有效的手段檢測運動員是否服用了興奮劑。直到1960年,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奧運會上,丹麥自行車選手詹森因服用苯丙胺猝死,1967年,英國自行車手湯姆·辛普森在環法自行車賽上因服用興奮劑而死,才引起體育界的高度重視。此后,國際奧委會終于決定把興奮劑檢測正式引進1968年舉行的第十九屆奧運會。20世紀末以來,對興奮劑的管控進一步加強。在1998年的環法大賽中,法國警方對多支車隊進行突襲,僅在荷蘭TVM車隊駐地就查出104瓶禁藥。這一丑聞極大地震撼了整個國際社會,引發了人們對服用興奮劑事件的高度重視。次年2月,國際奧委會在瑞士洛桑召開反興奮劑世界大會,并發表了《洛桑反興奮劑宣言》;同年11月,獨立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在洛桑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務是在國際奧委會的領導下,負責審定和調整違禁藥物名單,對各國興奮劑檢測實驗室進行認證等,總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爾。
2005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三十三屆會議上,以122票通過了《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國際公約》(簡稱“反興奮劑國際公約”),這是全球第一個旨在反對興奮劑的有普遍國際約束力的法律文書。2007年11月,在西班牙舉行的為期三天的第三屆世界反興奮劑大會上,修訂后的《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獲得通過,這標志著對興奮劑的嚴厲打擊進入了新的階段。
興奮劑不僅對運動員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危害,而且極大地玷污了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然而,你使用興奮劑超過我,我就使用更多的興奮劑超過你。于是,體育比賽中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事件依舊屢禁不絕。據統計,國際反興奮劑組織成立20年來,已有107名違規使用藥物的運動員受到了處罰。
俄羅斯成靶子
近年來,俄羅斯就一直深陷“興奮劑困局”不能自拔。這還得從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會說起,此次冬奧會東道主俄羅斯以攬13枚金牌、33枚總獎牌大獲全勝,然而當年底,德國的一家電視臺播放了題為《禁藥密檔:俄羅斯如何制造出它的冠軍們》的紀錄片,揭露俄羅斯田徑界普遍存在的使用興奮劑的行為。
節目播出后,輿論嘩然。國際奧委會立即要求對紀錄片曝光的黑幕進行調查,國際反興奮劑機構遂展開調查。近一年后,該機構公布了調查報告,指出俄羅斯田徑界存在“有組織”“系統性的”使用興奮劑的問題,同時呼吁全面禁止俄羅斯田徑運動員參賽。
屋漏偏逢連陰雨。2016 年初,曾長期擔任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實驗室負責人的羅琴科夫自稱受到政治迫害而赴美,他向《紐約時報》爆料稱,俄羅斯在 2014 年索契冬奧會期間由俄羅斯奧委會牽頭組織運動員服用興奮劑,有問題的陽性尿液樣本在俄羅斯情報機構的幫助下通過實驗室之間一個小如老鼠洞 的秘道被替換。這一消息令人咋舌,于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委托加拿大籍體育律師理查德·麥克拉倫進行了為期 57 天的獨立調查并于 2016 年 7 月18 日對外公布了長達 100 多頁的“獨立報告”。該報告證實俄羅斯運動員在俄羅斯政府的幫助下集體有組織地服用興奮劑,俄羅斯以國家行為,支持至少30 種不同項目的運動員服用興奮劑。同年 12 月,麥克拉倫又發布了第二部分報告,內容涉及 1166 例尿樣,時間跨度為 2011 年至 2015 年。該報告提供了更多證據、電子郵件等通訊資料以及相關調查內容,這兩部分報告被統稱為《麥克拉倫報告》。
在首份報告公布后,由麥克拉倫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曾建議禁止俄羅斯代表團參加里約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在 2016 年 7 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是否允許俄羅斯運動員參加里約奧運會,由各個單項體育聯合會自主決定。最終,俄羅斯體育代表團中不到 70% 的運動員獲得了里約奧運會參賽權,但所有俄羅斯田徑運動員的參賽資格被剝奪。
2017 年,《麥克拉倫報告》發布一年后,由國際奧委會委員、前瑞士聯邦主席塞繆爾·施密德負責的一個專門委員會又發布了《施密德報告》。該報告又一次將俄羅斯推到了風口浪尖。報告證實,俄羅斯存在有組織地操縱興奮劑檢測的問題,特別是操縱了 2014 年索契冬奧會的興奮劑實驗室的檢測工作。于是,2017 月 12 月 5 日在瑞士洛桑召開的國際奧委會會議上,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代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宣布了對俄羅斯的禁賽處罰決定:國際奧委會禁止俄羅斯代表團參加 2018 年韓國平昌冬奧會。最終,168 名俄羅斯運動員只能以中立的“俄羅斯奧運選手”身份參賽。
2018 年 2 月 28 日,國際奧委會履行此前承諾,恢復了俄羅斯奧委會的成員資格。同年 9 月 20 日,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恢復了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于 2015 年 11 月被剝奪的權利,與此同時,提出了一份“合規路線圖”,要求莫斯科實驗室在指定的期限前提供一份真實的實驗室數據。2019年 1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根據 “合規路線圖” 中的要求,從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提取了超過 2 萬個樣本數據。 9 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表示,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提供的數據存在 “不一致” 的問題,要求俄羅斯體育部和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就此做出解釋,并對俄羅斯啟動合規調查程序。同月,國際田聯理事會宣布延長對俄羅斯田徑聯合會的禁賽期,俄羅斯田徑運動員也就此無緣2019年的多哈田徑世錦賽。10月,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合規委員會建議對俄羅斯實施禁賽 4 年的處罰,以懲罰其提供了偽造和不完整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數據。最終,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作出了上述對俄羅斯禁賽 4 年的決定。禁賽4年對于素來以“戰斗民族”和世界第二體育大國自居的俄羅斯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而這一決定的出臺可謂多年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俄羅斯不滿情緒的總爆發。
陰謀還是陽謀
回望2014年至2019年這5年間,俄羅斯體育界深陷“興奮劑困局”的故事情節可謂跌宕起伏,俄羅斯整個國家已然受不了國際反興奮劑機構的輪番折騰。其實,在這場把俄羅斯當靶子的反興奮劑風暴中,作為被制裁一方的俄羅斯從未停止過“反擊”。據英國BBC廣播電臺報道,俄羅斯官方在改組反興奮劑機構的同時,也成立了專門的調查部門。調查結果顯示,索契冬奧會興奮劑事件的告密者——前俄羅斯反興奮劑實驗室負責人羅琴科夫曾通過私人途徑向運動員提供興奮劑,他的舉報實際是賊喊捉賊。俄羅斯官方同時強調,“羅琴科夫摧毀了運動員的樣本,然后指責俄羅斯實施國家興奮劑計劃。”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在 2016 年接受《莫斯科日報》采訪時表示,羅琴科夫的行為是 “一個聲名狼藉的人對體育的干預”,并稱重蹈 “政治干預體育” 的覆轍非常危險。
此次俄羅斯被宣布禁賽4年,則令俄羅斯整個國家都憤憤不平。俄羅斯奧組委稱,制裁不合邏輯也不正當。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此前也曾表示,俄方認為將興奮劑問題政治化,搞不公平競爭、玩無規則游戲是不能接受的。時任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在聽到這一消息后隨即表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俄羅斯體育事業提出的要求好比是一部沒完沒了的反俄連續劇。普京對此決定進行評論時表示,任何懲罰都應該針對個人,而不能具有針對集體的性質。普京同時認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決定的基礎與國際體育的純潔度無關,而是出于與體育和奧林匹克運動無關的政治考量”。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于2019年12月27日向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正式發出官方通知,對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決議表示異議。
如果因循俄方的觀點來反觀世界反興奮劑組織,似乎的確有一些蹊蹺之處。 2016 年 7 月初,美國參議員圖恩就曾爆料稱,過去10多年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一直接受美國政府的資金支持。此外,公開資料顯示,僅 2018 年,向世界反興奮劑組織捐款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其捐款額占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全年募款額的 15%。這就意味著美國與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關系非同一般。還有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是,針對俄羅斯的反興奮劑調查始于 2014 年,這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因為在此事件之前爆發了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事件,此事件之后則是敘利亞戰爭、俄美互驅外交官等事件,而這些事件無一不是或明或暗的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角逐。因此,這一次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針對俄羅斯的4年禁賽令,究竟是為了維護體育公平競爭精神,還是美俄等大國間政治博弈的延伸,還真讓人生疑。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