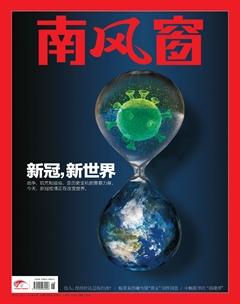闖過“病毒門”,來到“混沌世界”
謝奕秋

疫情沖擊下,我們熟悉的世界變了面貌,但沒有與過去一刀兩斷。中國駐美大使仍表示將執行貿易協議的內容,越南也恢復了對外出口大米;英國首相發表了闖過鬼門關后的首次演講,歐盟為馳援不及時向意大利道歉,美國也向意大利伸出了援手;也門響應聯合國的呼吁停火兩周,美國以外主要產油國則達成了減產協議以穩定油價……
這是一個持續時間不確定的“混沌世界”,有別于“常態世界”和“停擺的世界”。暫時闖過了“病毒門”的中國,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部分在恢復常態、但也有很多事情“回不去了”、且各種變化交迭發生的混沌世界。
這或是通往未來世界的入口,前提是后續的反思和問責足夠充分。在仍不斷攀升的死亡數字面前,各當事國不輕言勝利,頂著群起的非議不懈賑災抗疫,是最好的救贖方式。
疫情暴露西方“印度化”?
幾個月來,新冠病毒“坐著飛機、汽車和郵輪”在全球播散,從第一波的日本、新加坡、韓國到第二波的伊朗和意大利,從第三波的歐美大暴發到現在的全球大流行……不知道印度、非洲和南美,會不會成為下一階段大暴發的中心。
病毒不問國籍、信仰和文化程度,但與全球化聯系最緊密的西方國家,現階段的確診人數占了全球約八成。截至4月中旬,“感染率最嚴重”的10個國家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的高齡人群比例高,而養老院在這次疫災中受摧殘嚴重,有的養老院老人死亡率達40%。
新冠病毒無孔不入,就連美軍接收非新冠肺炎病人的醫療船上,都有多名船員確診;而“羅斯福”號等4艘美航母也紛紛中招,光是“羅斯福”號艦員中,就有包括被免職的艦長克羅澤在內的近600人確診,堪稱軍心動搖。
由于新冠疾病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的身體“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資源差別,此刻已不再分明。“衰老的西方”在這一刻,被譏嘲為正在“印度化”,即體現了“無能的民主治理”。但這并非全部的真相。
自3月26日G20視頻峰會后,全球新增確診數相當于“每天增加一到兩個武漢”。如今全球疫情榜上,累計確診數的前六名都是西方國家了。西方復活節前夕,美國邁過了累計確診數50萬大關和日新增死亡數2000大關,刷新了人們的認知。承平日久的西方社會,何以至此?
當初,基于社會發達和醫療資源豐富帶來的盲目自信,西方人在疫情潛滋暗長的時候,仍然熱衷于大規模聚集—包括美國的競選造勢活動、超大型國際會議、新奧爾良狂歡節等,都營造了一種“世外桃源”的假象;后來,出于對所謂低死亡率和年輕人容易康復的迷思,西方的年輕人仍不禁足,成為“行走的傳播源”;再后來,局部地區的醫院被擠爆,政府號召輕癥患者居家隔離,約等于放縱疫情深化。
特朗普的故鄉紐約,成了全球疫情的震中。到4月中旬,全球累計確診200多萬人,而紐約州的確診數字就突破了20萬,超過了美國以外的任一國家。特朗普的好友、紐約房地產大亨斯坦利·切拉,因新冠肺炎死于78歲,活生生打臉了特朗普最初的樂觀言論。基因組顯示,新冠病毒2月中旬就開始在紐約地區傳播,大多數病例來自英、法、荷蘭、奧地利等歐洲國家,而不是被重點防范的中、韓等亞洲國家。
直到前不久,西方國家才開始以防范無癥狀感染者對外播毒為由,要求民眾在公眾場合佩戴口罩。而在目前疫情防控較好的亞洲國家,以及許多非洲國家,戴口罩都是民眾剛需。西方華人整體的低感染率,再次說明了個人防范意識和衛生習慣的重要性,而這與不同文化的影響有關。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資源差別,此刻已不再分明。“衰老的西方”在這一刻,被譏嘲為正在“印度化”,即體現了“無能的民主治理”。但這并非全部的真相。
體制的因素也要負上一部分責任。像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衛生大權歸州所有,當聯邦政府的賑災緩不濟急,就別指望州政府會同意采取封城措施、限制本州人民到州外求醫或避禍。當歐盟最初對意大利的吁求置若罔聞,就不能苛責意大利的封國措施多么像亡羊補牢。
也有很多例子顯示,體制的問題不是決定性因素。像新加坡、韓國這些民主國家,都曾是抗疫的績優生;聯邦制的加拿大,人均感染率不到美國四成。這部分得益于它們都有過疫災教訓,無論是對抗非典還是中東呼吸綜合征的慘痛經歷,都有助于其快速組織起來。
不過,抗疫經驗更豐富的世界衛生組織,這回卻遭到美國痛批。白宮認為它“以中國為中心”、屢次錯判疫情形勢,因而暫停繳納4億美元會費,甚至威脅創建一個替代性機構(已有英國下院外交委員會拋出“G20公共衛生組織”構想)。
針對美國的“甩鍋”行為,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回擊道:“如果你想有更多的裹尸袋,好,那你就這么干吧。”可世衛組織流年不利,其總部所在的瑞士,人均確診數、死亡率都超過美國。譚德塞還呼吁:“我們必須在國家和全球層面將‘疫情政治化這種做法‘隔離起來。”這倒不失為中肯的建議。
次生災害不亞于病毒?
最近,美日支持生產線撤出中國的動向,成為國內輿論熱點。這其中存在一些誤讀。比如,實際上日本政府并沒有出錢給生產線遷移“兜底”,只是在總額高達1萬億美元的一攬子刺激經濟計劃里,提供了約22億美元的定向貸款,占比不過0.2%左右。
日方的初衷,是應對中國工廠2月關閉導致日本制造商(如豐田)缺乏零部件的情況;后來中國復工,日方政策目標就變成,將部分對華依存度高、附加值高的生產線轉回日本,口罩等防護物資的生產分散到東南亞,而針對中國市場的生產線不動。日本在華企業約3.5萬家,是走是留還得看綜合的投資環境,不是一點點官方貸款就能拉走的。
至于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百分百報銷廠家遷移費用”的聲音,也就是一種政策建議,真正落實還得經過立法程序。只要中國的營商環境持續改善、外交不走極端,特朗普在本屆任期內難以實現美企大遷移,頂多打打對華為斷供、撤銷給中國電信的業務授權這些牌。
日本的動作是出于經濟考慮,美國的威脅尚未落到政策上,但從中長期來看,還是需要針對性化解其力道。因為外資關聯到中國數千萬就業崗位,美國總統在特殊情況下也有權下令企業回國,而且特朗普不止一次拿《緊急經濟權力法案》說事,只是企業未必聽從,法院也可以干預。
另一個近期的熱點,是糧食(大米、小麥、大豆、玉米等)市場的波動。經濟“停擺”讓石油產品價格暴跌,但國際米價卻是扶搖直上。
糧價受當季及下季產量、供應商庫存、物流、市場囤積等因素影響。由于泰國嚴重干旱,加上亞洲和非洲進口商需求強勁,去年年底大米價格已開始攀升。當前,非洲遭遇新一輪蝗災,蝗蟲數量可能是今年第一輪蝗災的20倍;若這輪蝗災再蔓延到中東和南亞,今年全球的糧食產量可能銳減三成。
供應商也受到疫情影響。世界頭號大米出口國印度,因勞動力短缺和物流不暢,暫停簽署新的大米出口合同。而為了平抑本國米價,孟加拉國暫停出口普通大米。俄羅斯和一些中亞國家,則暫停對華出口大豆。“歐洲糧倉”烏克蘭倒是不打算限制糧食出口,但其今年產量可能下降10%。
為保障本國口糧,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國越南,3月25日開始禁止大米出口,但4月7日解禁,大概因為越南迄無確診者死亡,米價上漲也帶來暴利。第二大大米出口國泰國,照常供應國際市場,但由于柬埔寨勞工返鄉,人手告缺,今后產量存疑。柬埔寨已封國,并禁止大米和魚類出口。
美國作為農業大國,也會因疫情影響糧食播種,并且可能把農產品出口作為今后的牌,而不是逼著別國購買。聯合國內負責多邊糧食援助的“世界糧食計劃署”,與更多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屈冬玉)多有齟齬,這給國際糧食協調工作帶來更大挑戰。
不像股市暴跌、停工停產有著瞬時的直接影響,無論是生產線遷移還是糧價波動的后果,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看出來。這種晦暗不明的狀況,是“混沌世界”的表征之一。
相比之下,病毒這個“原生災害”的威力迅猛,短短兩個月即奪命十多萬條。即便西方疫情正在步入拐點,也還有土耳其、印度、巴西這類國家等著“接力”。就算是打贏了第一階段抗疫戰的中國,面對壓向國境南北東三線的境外輸入疫情,也容不得半點疏忽。
不像股市暴跌、停工停產有著瞬時的直接影響,無論是生產線遷移還是糧價波動的后果,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看出來。這種晦暗不明的狀況,是“混沌世界”的表征之一。
政府疏于管理的聚居地帶,是抗疫的最大隱患。土耳其境內有360余萬敘利亞難民,幸虧他們遠離重災區伊斯坦布爾,但土耳其全國確診數已超6萬,引爆衛生狀況糟糕的難民營,似乎只是時間問題。而印度孟買的達拉維貧民窟,2平方公里住著約100萬人,人口密度30倍于紐約,且早已有確診者死亡。印度為防疫全國封鎖三周,除了導致非正規部門數億從業者失去收入外,還引發規模浩大的打工者返鄉潮,暗藏的傳染風險令人提心吊膽。
越研究病毒越迷糊了?
對中國而言,外貿因國外需求和物流等因素萎縮,可能只是一時的,但疫情成全“逆全球化”,是中期的趨勢;某些國家更在鼓噪“去中國化”,雖然應者寥寥,但也提醒中國在低位增加原油儲備的同時,也要更多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
近來,中國已供應國外呼吸機1.8萬臺,與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交流防疫經驗,向韓國出口了兩座“火神山醫院”,中歐班列一季度增加了15%的班次。中國醫療隊還奔赴菲律賓、巴基斯坦、伊朗、俄羅斯、塞爾維亞、意大利、英國、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16個國家。
但是,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的期待還很高,比如加納財長就公開提出,希望中國減免非洲國家的債務,巴基斯坦總理也提出類似的減債呼吁。還有一些國家的人士不懷好意地要求中國賠償。面對洶涌的國際關系風暴,中國在主動承擔大國責任之外,還得做更壞打算,比如避免非洲當地出現排華運動。
在“看不見的對手”面前,吃一塹長一智,少出笨招,就有希望。美國在這方面并非一個好榜樣。其抗疫錯失先機,地方各自為戰,媒體苛責聯邦政府,總統則任性而為。《華爾街日報》一篇題為“特朗普浪費掉的簡報會”的評論文章,“美國之音”為中國說了幾句公道話,都被特朗普狠懟。
于是乎,大眾對于美國的期待,集中在醫療科技方面。所謂“斯坦福首創:驗血15秒測出是否有新冠抗體”,最適合無癥狀感染者的大規模快速篩查,對于局部復工意義重大。美中不足的是,抗體檢測并不能獨立用作是否感染的診斷,尤其是對于剛被感染尚未產生抗體的患者而言。
在美國開展抗體測試之前,中國、新加坡已利用相關檢測追溯疫情。英國、澳大利亞、法國也在跟進,試圖用于制定后續“退出”戰略。但美國著名病毒專家羅伯特·加洛博士稱,因為某些引發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的干擾,目前大多數的抗體檢測、甚至所有檢測都存在假陽性現象。而核酸測試的假陰性比例也畸高。

“檢測神話”并不完全可靠,疫苗呢?日前,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宣布了一款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據稱只要把疫苗貼在皮膚上,就可以產生足夠的抗體。但該疫苗一期人體臨床試驗還要幾個月后才開始,而研究者也不知道臨床開發過程需要多久。事實上,美國已進入一期人體臨床試驗的兩種疫苗(mRNA-1273和INO-4800),即便一切順利,也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大規模上市。還有專家警告說,抗體并非沒有副作用,在某些情況下(如感染登革熱病毒),抗體可能會惡化病情。
藥物方面也不容樂觀。4月公布的瑞德西韋首批臨床試驗結果,不盡如人意。特朗普多次推薦法國團隊遴選的抗瘧藥羥基氯喹,副總統彭斯宣布將在3000人身上做試驗,但該藥副作用大(如導致心臟驟停),經常為總統站臺的傳染病專家福奇博士并不看好,法國方面也警示了高風險。
美國著名病毒專家羅伯特·加洛博士稱,因為某些引發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的干擾,目前大多數的抗體檢測、甚至所有檢測都存在假陽性現象。而核酸測試的假陰性比例也畸高。
對于病毒源頭的研究也進展不大。就與新冠病毒的整體相似度來說,馬來穿山甲所攜冠狀病毒,不如云南蝙蝠所攜RaTG13病毒。而后者也與新冠病毒隔著20多年的進化距離,且兩者間的時間進化信號呈負相關,顯示RaTG13不太可能是新冠源頭。
至于陰謀論常提到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其所在的馬里蘭州確診數排在全美第14名,完全不是疫情起源地應有的樣子。而意大利權威腎科專家雷穆齊,也否認曾說過“在中國疫情暴發之前,病毒或已在意大利傳播”,認為是媒體斷章取義。最近劍橋大學彼得·福斯特團隊的一項所謂“新冠病毒分3個類群,其中原始類群主要不在中國傳播”的研究,也被同行批駁得體無完膚。
所以,隨著認識越來越深入,人們反而看不清病毒的來路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甚至不排除新冠病毒多年前就已潛伏在人群中,直到變異后毒性增強才大暴發。這種學術上的“推倒重來”,也是“混沌世界”的隱喻之一吧。
“全球共(疫)情”,未來中國人到任一國去,能夠聊的公共話題,將多出疫情對所在國影響這一項。雖然“巴黎空氣40年最佳”帶著一絲苦澀的味道,但期望眼下“混沌”的世界能變得風清氣朗、海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