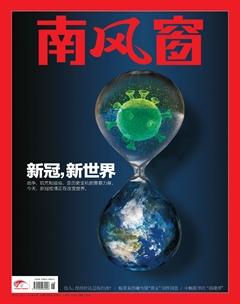“科學”不是認識世界的唯一方法
尤丹娜

面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傳統醫學也在“戰疫”中發揮了自己的獨特作用。近年來,中醫始終覆蓋著神秘的面紗,也飽受著大大小小的爭議。但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352場瘟疫,中醫從未缺席。
面對疫情,中國古代社會如何應對?中國傳統醫學為抑制疫情蔓延曾做過哪些努力?中醫應如何在現代醫學體系中尋求自己的位置?《南風窗》記者采訪了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職業醫師陳昱良,就以上問題做了相關探討。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疫病隔離制度的國家
南風窗:今天我們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個重要防控措施是“隔離”。在古代,面對大規模瘟疫暴發的時候,是否也有類似隔離及定點醫院的措施?
陳昱良:在古代是有隔離措施的。甚至,中國的“隔離”制度是全世界最早出現的。
近年出土的“云夢睡虎地秦簡”,這份秦朝的律政文書中,就有很明確的關于麻風病防治的記載。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就是:只要檢查確診,直接送去隔離。隔離的地方稱為“癘遷所”,至今有2200多年歷史的疫病隔離措施,就是從“癘遷所”開始的。
到了唐代,有一段時間麻風病流行,政府就直接開辟了“癘人坊”,由官方出資收購一些寺院中的空置房屋,作為專門的麻風病醫院,男女分住,政府給予供養,可以說非常科學了。
在中國的歷史上,對傳染病進行隔離預防幾乎是一個“深入骨髓”的概念。即使在《紅樓夢》這樣的文學作品中,都會有“隔離”出現:晴雯著涼了,按照賈府的規矩,患感冒就要搬出去住,避免傳染他人。
但我必須要強調一點,古代中國始終是一個復雜的“大帝國政府”。“隔離”制度在當時首都的執行情況可能比較理想,但到了邊疆,可能就會打折扣。
隔離的地方,也負責治療,有點像今天的定點醫院,是一種政策保障。但是保障能執行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級別的“癘遷所”里,是不一樣的。
南風窗:面對疫情時,中國古代社會有環境消殺的措施及保護身處防疫前線醫生的相關措施嗎?
陳昱良:有的。最早在三國時期的很多道教文獻中,就已經有記載,對患病之人居住的地方、治療時使用的器械、患者的衣物臥具,需要經過專門的消毒或者處理措施。
就環境消殺來說,清代的時候,宮廷檔案里面也有很多類似的記載。常見的比如:煙熏消毒、蒸汽消毒,都是對集體空間的空氣進行消毒的辦法。
百姓個人會隨身佩戴香囊,夜晚時放置在床頭,里面有一些特定的中藥,通過這種方式用草藥的氣味進行自我保護。
身處防疫前線的醫生,當時雖然沒有如今的這些防護用品,但有規定醫患之間的“診療原則”,比如“宜遠不宜近”;觀看患者的口鼻時,古代醫家叫“存氣少言”,醫生屏住氣、不說話進行診治;還有“夜勿宿于病者之家”,從規定的層面提出了很多防止傳染的措施。
南風窗:綜合來看,中國古代政府是否有一套較為成熟的應對疫情系統?疫情暴發時,從朝廷到基層,這一系統是怎樣運作的?
陳昱良:有的。我用北宋時期首都發生過的“開封大疫”來舉例。
開封城比較特殊,比起坊市分離、管理嚴格的唐長安,它是一種“雜居”的形式,又取消了宵禁,在人口密度、人員流動性、居住環境上非常接近我們現在的城市,可以作為一個“同類項”來比照。
發生在開封的這次疫病屬于腸道疾病,大疫之前剛剛經歷了旱災,且夏天非常炎熱,開封作為宋代的首都,人口眾多、居民密集,情況是很嚴重的。
面對這次疫情,宋太宗的政府做了幾個很重要的措施。首先,政府撰修了“太平圣惠方”—一個醫學知識的匯集,直接就把“太平圣惠方”頒賜京城及全國各地,為疫病的治療提供了一個指導方針,類似于現在國務院印發的《防治新冠肺炎防控指導意見》。
其次,就是進行上述的隔離治療、發放免費藥物、環境消殺、水源清潔等相關措施。同時,皇帝會派遣身邊的宦官去監督負責疫情處理的高級官員,隨時直接向皇帝匯報疫情救治情況。
最后,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會要求所有的皇帝在遇到疫情的時候,要好好反省自己,包括閉門思過、下“罪己詔”一類的行為。在這種道德約束之下,民間的鄉紳,會在疫病發生的時候去自發建醫院、自費購買藥品發放、自覺傳播防疫知識,和遇到自然災害的時候施舍食物一樣,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
隔離的地方稱為“癘遷所”,至今有2200多年歷史的疫病隔離措施,就是從“癘遷所”開始的。
“開封大疫”的防控效果非常好,在農歷6月份就全面控制了疫情的事態。從這場《宋史》記載的第一場大型瘟疫的防控勝利中,我們可以看到皇帝的重視、政府機構的有效配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動員和監督、財政的支持,加上醫學知識的支持、道德的約束等綜合起來,打贏了這場戰“疫”,也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開封大疫”之后的古代政府,在應對疫情的時候,就有了一個相對比較流程化的處理措施。并且,北宋處理疫病的經驗,對當時的遼西夏、高麗、日本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即使在今日,也有非常值得我們繼續去沿襲的一些寶貴經驗。
中醫也有“疫苗”
南風窗:中國古代是否有運用傳統醫學治療有效控制住疫情的案例?
陳昱良:前面提到的“開封大疫”就是運用中醫藥方成功抑制疫情。這個“藥方”包括食療方和純粹的“藥”方兩部分。“藥”方的部分,因為特定的藥物存在一定的購買難度,普通民眾也沒有購買它的經濟承受力,所以一般來說,政府會負責批量發放。北宋時期,地方官甚至會把特定的藥材直接放到水井中,通過公共飲水系統來實現對疫情的預防。
還有一次比較成功的防治是處理“大頭天行”。
金朝的時候,“大頭天行”這個傳染病流行,且傳染性很強。患病之后,患者的頭開始腫,腫到眼睛睜不開,嗓子腫到吃不下飯,最后呼吸困難,缺氧喘息而死。這個病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是一個呼吸系統疾病,當務之急是處理喉頭水腫。
金代醫學家李東垣試用了原有的“大承氣湯+板藍根”藥方進行治療后,發現效果不太理想,就進行了結合臨床的改良,以黃芩、黃連為主制成了新的藥方,即“普濟消毒飲”。它的療效顯著,也成為了后世治療“溫熱病”的一個基礎方。
即使在今天,中醫臨床治療腮腺炎、腦膜炎、風熱、邪毒等單獨急性扁桃體炎、淋巴結炎、咽喉水腫一類的疾病,依舊在使用這個藥方,效果也特別好。
南風窗:疫病暴發中,中醫也會進行疫苗或類似疫苗的預防藥物研制嗎?
陳昱良:中醫史上確實有“疫苗”,就是面對天花的時候。
天花是我國古代軍隊作戰的時候,從交趾(今越南)的俘虜傳染給東漢的軍隊,再逐漸到中原地區流行起來的一個烈性傳染病,死亡率極高。
對于天花進行免疫接種,在唐末就已經出現了,但方式比較野蠻:讓沒得過天花的人感染一次。但是這樣死亡率和免疫率是不分上下的,所以中醫就開始研究如何讓人們“有選擇地去得一次死亡率比較低的天花”。
第一步,中醫嘗試了“痘衣法”,找到得了天花又痊愈的人,拿來他們的衣服給健康的人穿,發現死亡率依然很高;第二步,中醫試圖把癥狀較輕的天花患者膿皰中的膿漿接種到健康人的鼻孔里;第三步,開始嘗試把處于康復期的患者,其天花膿皰破了之后結的痂磨成粉,吹到健康人的鼻孔里。到這一步的時候,其實在疫苗的減毒方面已經非常科學了。
但接下來,中醫又發現新的問題,就是吹進鼻孔里的這些粉末,可能打個噴嚏就出去了,不好控制用量。所以發展到最后,演變為“水苗法”,即把已經處于康復期的天花患者,收集其膿皰和痂皮,研磨后蘸水用棉花塞進鼻孔里。這時,天花的疫苗已經比較成熟了。
后來,中醫開始選煉“熟苗”,中醫的傳統說法叫“選苗”“煉苗”,把疫苗一代又一代地使用:給第二代接種的人選用第一代接種的人身上發出的膿皰、痂皮,在保證免疫能力的基礎上,將毒性降到最低。
天花疫苗的研制和普及對我國中原地區抗擊這一烈性傳染病發揮了巨大的成效。到了康熙年間,他將天花疫苗的接種制度在宮廷、蒙古王宮、滿洲貴族之間全部推廣開來。和康熙同一時代的俄國彼得大帝,正式派遣使團來中國學習天花接種的技術,之后,又傳至土耳其、英國等國家。可以說我們中國的人痘接種術在歐洲是廣為人知的。像法國的思想家伏爾泰,對包括人痘接種術在內的中醫成就也非常推崇。
“科學”不是唯一的方法
南風窗:中國古代的邊境是否會專門設置控制國際間瘟疫傳播的檢疫站,來檢驗入境的外國人、歸國的使節與邊塞將官?
陳昱良:坦率地來說,在邊境檢疫、控制輸入傳染病方面,中國古代是不如歐洲的。
歐洲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興起邊境的檢疫制度,主要是海港檢疫。當時,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在貿易過程中發現,往來通商的船只會帶來未知的疾病。地理大發現之后,來自印度、非洲的“異域”疾病更是對歐美產生致命影響,海港檢疫制度因此誕生。檢疫方式也比較簡單:船上是否有生病的、發燒的人?只要有病人,船只到達港口后,船上人員一律不允許上岸,在船上呆滿規定時間,痊愈了再下船。
“開封大疫”之后的古代政府,在應對疫情的時候,就有了一個相對比較流程化的處理措施。
海上往來進行檢疫制度相對方便,到了陸地上,就變得很有難度。中國古代并沒有現在的這種國境線,沒有規范的出入境和關稅制度,哪怕是張騫出使西域、唐僧西天取經這樣“著名”的國際往來行為,出入過程也沒有官方的統一管理,更遑論檢疫制度了。而我國的海上貿易往來,除了明初的鄭和下西洋去過“遠洋”之外,大部分也都是在東南亞地區、東北亞地區海域,也沒能見識到歐洲的海港檢疫制度。
所以,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中國古代在檢疫制度,尤其是海外檢疫方面缺乏意識。
但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中國古代又十分熱衷于搜集海外的藥材。唐代的時候就有“海外本草”的說法,指那些通過商貿和往來從其他地方傳入的藥物—比如我們現在很熟悉的藏紅花,其實它不是西藏特產,而是經由西藏地區傳入的一種歐洲的花蕊。還有一些藥材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醫對這些藥物十分重視,用它們豐富了中藥的本草體系,對于當時疾病的防治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中國古代的文化在這一方面是相對比較包容和開放的,更重視是否可以“為我所用”。
南風窗:歐洲暴發“黑死病”時,似乎除了祈禱、“放血”,沒有特別多的科學干預,但中國古代面對“傷寒”,已經有了一套靈活多變的辨證施治療法。你覺得同樣是面對瘟疫,中醫與歐洲的醫學,有怎樣的不同?
陳昱良:總的來說,歐洲的現代醫學發展很短暫,且醫學的發展可能并不在醫學自身,而是在醫學的上游學科:比如有了顯微鏡,就有了對身體、藥物的微觀認知。但中醫,是完全的臨床經驗。在疫情之中,通過臨床經驗的總結、修正,對整個疫情的防控作出自己的貢獻。
就你提到的“放血療法”而言,提出它的是古羅馬醫學之王蓋倫,只比我國的中醫張仲景大19歲,他們是同時代的人。蓋倫的醫學體系依靠動物實驗,也因此得出了許多非常錯誤的結論。比如:人的下巴是兩塊骨頭拼接的—因為兔頭是這樣的。同時,他認為血液在肝臟產生,心臟把血液輸送到身體的各個部分之后,血液在身體的末端被吸收—這是“放血療法”的理論基礎:血液會源源不斷地從肝臟產生,人不會因失血過多而死,放血反而可以釋放體內多余體液,糾正身體的失衡。很顯然,基于動物實驗的人體理解是完全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