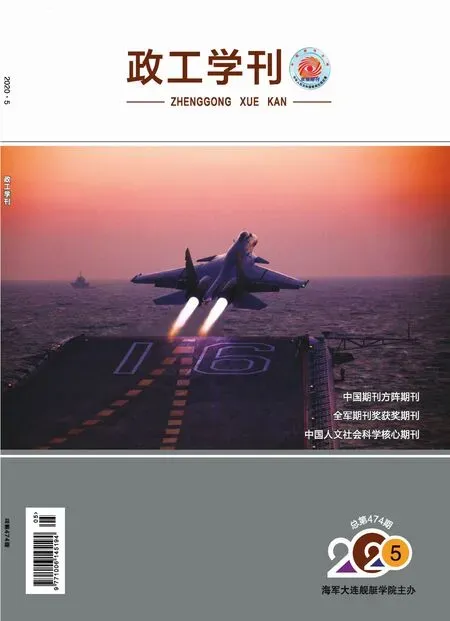煥發臨戰動員的強威力和新活力

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盛者,鼓也。習主席反復強調:“我軍歷來是打精氣神的。”我軍歷版戰時政治工作綱要也均把作戰動員列為戰時政治工作第一項內容。戰爭年代,往往幾分鐘的戰前動員就讓戰士們熱血沸騰、氣勢如虹,強如美軍也敗在我軍盛“氣”之下。進入新時代、應對新挑戰,我軍各級指揮員特別是政治干部,絕不能丟掉臨戰動員這一看家本領和傳統優勢,切實為勝戰打贏提供旺盛戰斗精神和強大心理支撐。
然而,從近年來部隊演訓實踐情況看,雖說臨戰動員始終在固化堅持,但固有優勢已趨于弱化,政治干部“不擅”甚至“不會”做臨戰動員的問題日益凸顯,致使臨戰動員有淪為“雞肋”之憂、成為“軟肋”之險。戰斗味不濃。有的臨戰動員說是臨戰,實則離戰,沒有戰場代入感,不少指揮員平時嘴上喊實戰化,演訓臨戰動員卻通篇都是遵守規則少扣分、嚴守紀律少挨批,只字不提生死存亡、不講防間反特、不談殺敵立功,沒有緊張感、硝煙味,嗅不到一絲戰場氣息。針對性不夠。有的動員講話千篇一律、生搬硬套,不貼單位實際、不符任務特點,一些指揮員講起世界局勢頭頭是道,談及戰場走勢支支吾吾,分析思想形勢若明若暗,結果動員聽似“高大上”、實則“空虛偏”,官兵不知所云、無所適從。激情度不足。有的動員有“員”沒“動”,調動不了人、觸動不了心,比如少數指揮員滿足于自我欣賞,熱衷于搞靚詞、玩對仗、瞎咋呼,臺上激情飛揚,臺下反感倒胃。還有個別指揮員形象不佳、口齒不清、聲調不高,戰士縱有滿腔熱情也消耗殆盡。理性化不高。有的動員“劍走偏鋒”,只要感性,不要理性,比如有的制定戰斗口號明顯不切實際,部隊根本做不到,造成官兵不想聽、不相信、不愿做,同時也可能使部隊滋生盲目自大、麻痹輕敵思想,一旦行動受挫極易產生心理塌方。時代感不強。有的臨戰動員一味墨守老模式,要么就是臺上喊口號、臺下表決心、臺前挑應戰掄“三板斧”,要么就是成立敢死隊、沖鋒拼刺刀唱“老調門”,而不注重運用新媒介使用新手段,摸不準新時代脈搏,打不準官兵新思想鼓點。應變力不好。有的搞動員滿足于“一稿管多案”,死板教條、一成不變,一旦設置導調科目或出現突發情況,基本上處于“串線”甚至“短路”狀態,不會靈活變通、不會隨機應變,甚至慌亂無措、語無倫次,動員煩瑣低效不說,還可能延誤戰機、造成被動。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考評難量化等外因,更在于指揮員自身思想認識與技能錘煉等內因上。解決思想認識問題,關鍵在自己、在自知、在自悟。下面重點就錘煉動員技能、掌握動員技巧,結合實踐思考談幾點認識。
一、情感上走“心”。動員先動心,觸動不了官兵的心,動員將如“空中樓閣”,看得見卻進不去。欲動心者,必先知心。戰場態勢緊急、情勢多變,官兵思想、心理也必然波動跳躍。這就要求我們開展動員必須深入調研、充分預想,緊緊抓住官兵的活思想,主動迎合官兵所思所想,用兵言兵語聯通兵情兵心。說到官兵心坎上,走進戰士心眼里,產生共情的將士必然更易接受動員內容并付之行動響應。
二、內容上落“實”。動員要想取得實效,就得在“實”字上做文章、見真章。戰爭最現實的問題是生死,動員必須直面生死關解答生死觀。臨戰動員必須說實話、報實況、講實理,讓官兵明白作戰意義、個體作用、生死價值,引導官兵正視鮮血、英勇戰斗。鄧小平在碾莊戰役前動員直截了當:“人人都要有燒鋪草的決心!……只要消滅了南線的敵軍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國各路解放軍還可以取得全國的勝利,這個代價是值得的!”頭腦越清醒,行動越堅定。準確把握戰場態勢走向與部隊作戰意義的官兵,必然戰意更濃、斗志更盛。
三、語言上有“力”。動員表面是調動人員,實質在調動力量,而語言就是催化劑,就是力量源。大道至簡,樸實語言最有力量。歷數我軍輝煌戰史中戰斗動員,都沒有華麗辭藻,卻都極富力量。塔山阻擊戰中,某連長戰壕內動員道:“塔山沒有塔,塔山也沒有山……我們四縱就是塔,我們四縱就是山,有我們四縱在,敵人他打不過塔山。”戰士們聽后無不壯志激昂、豪情滿懷。
四、口號上提“氣”。戰斗口號是戰斗精神的濃縮。彭德懷講:“一個口號抵得上十顆子彈。”一句響亮的戰斗口號往往極具號召力和殺傷力,傳遞出強烈殺敵決心和必勝信心,催生出強大戰斗力。濟南戰役中粟裕親擬的戰斗口號“打進濟南府,活捉王耀武”,猶如催征號激勵官兵沖鋒,又如催命符震懾敵人心魄,最終戰斗口號都變成了現實戰果。這啟示我們,戰斗口號必須言簡意賅、短小精悍、雄健犀利,切實做到聽起來提氣、喊起來聚氣、打起來霸氣。
五、形式上求“活”。戰斗動員在于激發熱情,但刻板形式只會消磨激情,甚至適得其反。開展戰斗動員是我軍光榮傳統,但繼承傳統并不等于因循守舊,而實際上戰爭年代我軍也十分注重創新動員形式。賀龍所部師長賀炳炎一條胳膊長征中被打斷,手術后,賀炳炎僅在擔架上躺了六天,便又投入戰斗。后來每當作戰斗動員,賀龍就從懷里掏出手帕:“這手帕包過紅軍師長賀炳炎的骨頭渣!”總能極大調動戰士飽滿戰斗熱情。我們必須著眼動員效果,緊貼戰場實際,靈活組織形式,真正讓動員“動”起來、把激情“激”出來。
六、時機上借“勢”。動員往往因“勢”而作,唯有審時度勢,才能取得預期效果,否則只會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戰狼》中,旅長在一名戰士犧牲后順勢動員:“同志們,看著你眼前犧牲的戰友,告訴我,這是什么?這是戰書!是向中國軍人的挑釁!再過六個小時,敵人可能會穿越國境線逃出中國,現在我命令你們,把失去的尊嚴奪回來!”雖是電影片段,但其產生的煽動力卻是巨大而現實的,值得借鑒。我們必須準確捕捉官兵現實思想頻譜信號,針鋒相對、借勢發力,使動員效果最大化。
七、行動上立“樣”。欲動員他人,自己先行動。俗話說,“干部走在前,勝過搞動員”。戰爭年代,無數革命先輩舍生忘死、沖鋒在前,把“向我看齊、跟我上”變成了最有力的戰斗動員。1938年冬,日軍進犯汾河,王震奉命奪回陣地。戰前,他讓戰士抬出一口棺材,揮拳動員道:“我領頭向前沖,要死我先死,死后裝進這口棺材里。”所部軍心大振、人人決死赴戰,最終擊潰強敵。我們各級指揮員開展臨戰動員,必須十分注意自己一言一行,堅持以自己的形象樹立部隊的形象,以自己的激情感染官兵的激情,真正實現“上下同欲者勝”。
臨戰動員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關鍵靠各級指揮員結合戰備演練和日常工作,緊貼實際加強鍛煉、緊盯任務深入探究、緊跟形勢不斷改進,切實提高臨戰動員技能技術,真正讓看家本領再現強大威力,讓傳統優勢彰顯時代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