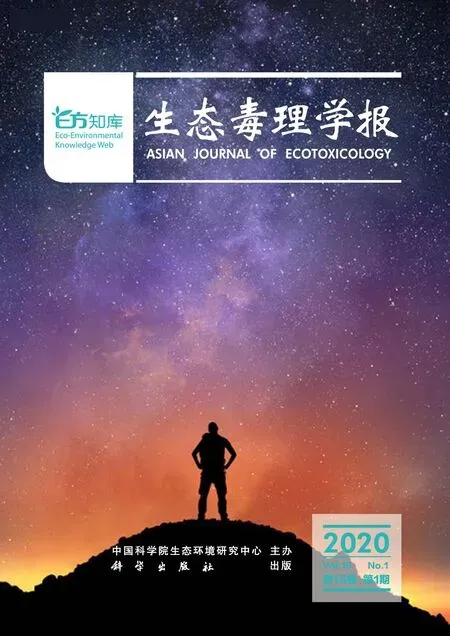化學品環境風險管理需求與戰略思考
趙靜,王燕飛,蔣京呈,葛海虹,菅小東,林軍
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北京 100029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將化學品環境管理列入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即《21世紀議程》,其中,第19章提出,應逐步淘汰或禁用那些對環境或人體健康構成不可接受或無法管理風險的化學品以及那些具有毒性、持久性和生物蓄積性且無法適當控制其使用的化學品[1]。2002年2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理事會第7屆特別會議決定,要擬訂一項國際化學品管理的戰略方針,并于同年8月底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WSSD)上獲得同意。2006年,在迪拜舉行的國際化學品管理國際大會第一屆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國際化學品管理的迪拜宣言》、《總體政策戰略》和《全球行動計劃》,這3項文件共同構成了《國際化學品管理戰略方針》(SAICM),提出到2020年,實現化學品和所有廢物在整個存在周期的無害環境管理[2]。2015年,聯合國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將減少由城市活動和危害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化學品所產生的不利影響,包括以環境無害方式管理和安全使用化學品[3]。2017年至今,聯合國環境署啟動多次閉會期間會議,就2020年后化學品與廢物健全管理行動方案的愿景、政策原則、目標和實施等問題進行磋商,呼吁從全球、區域和國家各層面開展積極有效的行動[4]。
我國參加了于1992年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同年8月,中共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了外交部和原國家環境保護局關于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報告,提出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2016年,為推進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國制定發布《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針對化學品環境管理發展目標提出多項落實舉措,包括:為減少危險化學品的環境和健康風險,要改革環境治理基礎制度,建立覆蓋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放許可制,力爭到2020年,建立全國統一的實時在線環境監控系統,健全環境信息公布制度,開展環保督察巡視,嚴格環保執法;為加強化學品和廢物的環境管理,要對化學品和所有廢物進行全生命周期的無害環境管理,降低化學品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大幅度提高綠色化工技術水平[5]。2017年,“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重點要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要堅定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6]。
化學品健全管理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重要領域。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歷經30多年的發展,在基礎信息收集、能力建設等方面已取得一定進展和成效,風險管理的基礎能力和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但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工作仍進展緩慢,頂層設計不足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因此,本文綜合闡述了當前國內化學品環境管理的形勢與現狀,研究提出了化學品環境風險管理的戰略需求、目標和主要行動計劃,以期推動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進入系統化、科學化發展階段,加快與國際接軌。
1 化學品污染問題(Problems on chemical pollution)
1.1 化學品潛在暴露風險增加
化學工業的快速發展增加了化學品環境和健康的潛在暴露風險。據《全球化學品展望2》的最新數據顯示,2000—2017年期間,全球化學工業產能(不包括藥品)從大約12億t增加到23億t,2017年全球包括藥品在內的化學品銷售額合計達到5.68萬億美元,預計2017—2030年期間銷售額幾乎將再翻一番(圖1),預計2030年中國將占全球銷售額的近50%。2018年,全球商業流通中的工業化學品估計約4~6萬種,其中6 000種化學品占流通總量的99%以上。根據歐洲環境署2018年匯編的數據,2016年歐洲化學品消費總量中約62%對健康構成危害[7]。
我國化學品種類多、產量大,潛在暴露風險較高。自2010年起我國化工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一,產值約占工業總產值的12%,“十二五”期間年均增長達9%,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化學品生產國,甲醇、化肥、農藥、氯堿、輪胎和無機原料等重要大宗產品產量位居世界首位[9]。據原環境保護部2015年開展的全國重點行業化學品生產使用情況調查顯示,2015年我國九大行業3萬多家企業生產使用化學品3萬余種,總產量8億多噸,總使用量6億多噸,其中,產量超過千噸的高產量化學品4 000多種,約占總產量的99%以上;國際癌癥機構發布的2B類以上致癌物質167種,產量1.2億多噸,使用量1.1億多噸。我國《中國現有化學物質名錄》統計的現有化學物質約45 000種[10],而且新化學物質種類每年以幾十種的速度在增長,化學品潛在暴露風險在逐年增加。

圖1 2017—2030年世界化學品銷售額(不含藥品)增長預測[8]Fig. 1 Projected growth in world chemical sales (excluding pharmaceuticals), 2017—2030[8]
1.2 化學品環境與健康風險增加
化學品的各種生產和使用過程會持續向空氣、水和土壤釋放大量化學物質并產生大量廢物,帶來諸多典型的環境污染問題,如微塑料在全球各地的水、沉積物和生物體中不斷被檢出,尤其是在人類生產活動密集的港口及河流入海口、海岸帶等地區[11],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積性、高親脂性以及長距離遷移能力等特征的六溴環十二烷(HBCDs)在環境各介質及生物體中均有檢出[12]。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某些工業化城市,源于化石燃料的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的主要來源是揮發性化學品(VCPs)的使用,例如農藥、涂料、印刷油墨、膠粘劑、清潔劑和個人護理產品等[13]。
據《全球化學品展望2》報道,在全球所有區域的空氣、水和土壤以及生物群中均可檢測到化學污染物。在水體和人類經常食用的海洋動物中檢測到了微塑料、藥物殘留物和汞等物質,在10 000 m深的海洋沉積物中的動物體內檢測到高濃度多氯聯苯,在喜馬拉雅冰川中發現了受《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管制的某些有機氯農藥。人類體內也經常檢測到令人關切的化學品,例如母乳中的二噁英和呋喃,尿液中的鄰苯二甲酸酯,以及人類血液中的重金屬等。最近的幾項研究顯示,在新生兒臍帶血中檢測到已禁止使用的阻燃劑,表明母嬰傳遞是殘留物質轉移到后代的途徑之一,而這正是持久性和生物蓄積性物質的一個典型特征。
近年來,我國河流、湖泊、近海水域、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廣泛檢測出各種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具有潛在毒害作用的化學品,包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14]、內分泌干擾物質(EDCs)[15]、含抗生素等的藥品及個人護理用化學品(PPCPs),以及重金屬鉛、汞和鎘等[16-17]。
1.3 化學品污染危害已經顯現
化學污染威脅生物群和生態系統功能。據研究,溴化阻燃劑對魚類可造成慢性影響甚至死亡,接觸多氯聯苯和多氟烷基物質會導致海豹和海龜的免疫系統受到抑制,雄性魚因接觸合成雌激素而雌性化[7]。2018年印度的一項研究表明,藥品雙氯芬酸在被禁止10多年后繼續對禿鷲種群的健康產生不利影響。此外,還發現一些殺蟲劑對非目標昆蟲和授粉動物有負面影響;農業中磷和氮的過量使用繼續造成世界各地的海洋形成“死區”;一些化學物質會對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健康帶來壓力。研究還表明,釋放到環境中的一些抗菌藥物、重金屬和消毒劑會使病原體產生抗藥性[18]。
化學污染是造成全球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19],根據2015年的幾項研究估計,由化學品引起的神經行為缺陷每年在歐盟造成的損失超過1 700億美元,因兒童鉛中毒在中低收入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9 770億國際元[7]。另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2016年由化學品污染帶來的疾病大約導致了160萬人的死亡[20]。
在我國,一些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污染危害也已顯現。清華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是全氟辛烷磺酸(PFOS)類物質的唯一生產國和供應國,部分沿江沿海區域PFOS污染嚴重[21]。北京大學的另一項研究表明,三苯基錫化合物(簡稱TPT)廣泛應用于船體防污漆,可能是造成野外中華鱘數量下降和畸形的重要原因之一[22]。另據非政府組織(NGO)報道,一些有毒有害物質在長江上、中、下游的野生魚體內廣泛存在,在取自長江上、中、下游不同城市的鯉魚和鯰魚體內,均測出了具有內分泌干擾特性的壬基酚和辛基酚,這2種物質可導致雌性性早熟等性發育和生殖系統問題。
2 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需求與目標(Needs and goals of chem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2.1 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現狀
我國的化學品管理起步較晚,1988年原國家環境保護局成立有毒化學品辦公室,1994年啟動有毒化學品進出口環境管理工作,2003年原國家環保總局發布17號令(《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辦法》)并開始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登記。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則早已制定并逐步完善化學品管理法律法規。歐盟自1967年開始對危險物質進行分類、包裝和標識管理;1993年和1994年,分別對新物質和現有物質提出風險評估要求;2007年,頒布實施《化學品的注冊、評估、授權和限制》(簡稱REACH),同步管理新物質和現有物質,對所有上市的化學物質實施注冊、評估、授權和限制。美國于1976年頒布有毒物質控制法(簡稱TSCA),目的是有效管理那些在生產、加工、商業銷售、使用和處置過程中對人體健康或環境產生不合理風險(unreasonable risk)的化學物質;2016年發布《弗蘭克勞滕伯格21世紀化學物質安全法案》最新修訂版,建立新的基于風險的安全標準,建立新的風險評估程序和要求,設定嚴格的執行期限,在不考慮成本的前提下開展評估。日本于1973年頒布《化學物質審查及制造管理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管控化學物質風險的法規,要求對現有化學品的環境和健康風險進行評估和審查,根據評估結果實行分級管理。
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建立了一套相對完整、成熟的化學物質風險識別、評估和防控的法律和技術體系,包括:新化學物質審查制度;現有化學物質風險評估制度;根據評估結果采取禁止或限制生產、使用、進出口措施;在化學品生命周期的各主要環節建立有毒有害化學品的環境污染控制體系;強化企業主體責任,提供數據、風險防范;強化公眾知情權和利益相關者參與;評估禁限措施的技術可行性和社會經濟影響等。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基礎薄弱,目前尚有多種化學品不明其危害,知其危害的化學品也還不能科學認知和防范其風險,大量生產、使用導致污染形勢嚴峻。因化學品污染更多源于有毒有害物質的慢性毒性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的長期損害,污染問題隱蔽而復雜,加之長期以來忽視化學品問題,我國現階段化學品環境管理已明顯滯后于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
(1)環境管理體制不完善。我國現階段環境保護的重心仍偏重于常規污染物控制和末端治理,基于風險管理的化學品法律法規體系尚不完善,信息報告、風險評估和限制淘汰等相關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化學品環境管理邊緣化,成為環境保護的短板。化學品是環境污染尤其是化學污染的本質和源頭,因源頭管理缺乏,導致國外大量有毒有害化學品產能加速向我國轉移,發達國家通過強化立法加大了我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難度,通過限制某些產品中的化學物質以及加快替代品研制形成了新的壟斷,我國很多產品因發達國家對有毒有害物質的嚴格控制而缺乏國際競爭力,出口貿易因技術壁壘而遭受巨大損失。
(2)環境風險防控工作滯后。現階段,我國化工產業以及其他化學品相關行業仍在大量生產和使用具有潛在危害的化學品,我國也仍在承接國際上大量有毒有害化學品的產能轉移,化學品風險防控工作已明顯滯后,與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需求不協調,已對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制約。
(3)技術支撐能力明顯不足。我國化學品測試體系不完善,計算(預測)毒理發展緩慢,危害信息缺乏,化學品危害的識別和評估能力不足。環境中化學物質的遷移轉歸研究基礎薄弱,環境監測技術缺乏,風險評估技術方法體系不完善,化學品環境風險評估技術能力不足。我國化工產業低端產品多,技術附加值低,新產品研發的需求度不高、發展緩慢,無毒無害替代品研發技術能力不足。
(4)尚未形成多元化治理體系。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具有產業鏈長、多領域和跨部門的特征,多元化的格局決定了化學品環境管理必須加強社會共治,發揮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在環境治理中的協商合作、協調增效。一直以來,我國的環境管理工作都以行政為主,由政府負責多方面協調、整合人力和財力資源來解決經濟與環保并重下出現的問題,市場主體與社會主體參與不足,游離于決策過程和政策實施之外,政府、企業和公眾多元主體間未能形成互動合作共贏格局。
2.2 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戰略需求與目標
從國際經驗看,化學品環境管理的目標是預防和控制具有特定危害性的化學品進入環境介質,以避免和減少通過環境介質中有害化學品的暴露而引發的環境和人體健康危害及風險。立足我國已有實踐,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應以源頭控制和風險防范為根本原則,管理目標立足于化學品對健康和環境的損害發生之前的源頭預防和控制,抓緊制定化學品專項法規,建立管理制度,厘清國家與地方、管理部門之間、企業以及公眾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十三五”乃至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國都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新老化學品的環境風險將同時存在。只有制定和實施最嚴格的法律和制度,才能真正解決化學品管理的深層次問題,從根本上遏制日益嚴峻的化學品環境風險形勢,建立起我國化學品環境管理的長效機制。
為實現上述目標,要借鑒國際化學品環境管理的成熟經驗和我國已有的實踐經驗,遵循風險防范、全生命周期和優先性管理等原則,制定覆蓋全面、科學規范的化學品環境管理戰略,指導中長期化學品環境管理相關工作。化學品環境管理戰略應明確開展化學品環境調查、危害鑒別和環境風險評估的時間安排,提出開展限制和淘汰等管控技術可行性評估、管控的經濟社會影響評估的原則要求,提出制定科學的風險防范措施的原則和程序要求,推動使用毒性小的替代品以及減少有毒化學品的暴露,逐漸淘汰對生態環境構成不合理風險的化學品,最大限度減少和消除化學品全生命周期對生態環境的潛在風險。
3 化學品環境風險管理行動計劃(Action plans on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3.1 健全化學品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
加快推動制定化學品環境管理專項法律法規,構建以保護環境和人體健康為主旨的國家化學品環境管理制度體系。建立化學品環境風險評估制度,通過危害篩查制定發布優先評估化學品名錄,基于環境風險制定發布優先控制化學品名錄和禁止化學品名錄。完善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及風險評估制度,對新化學物質實行基于風險的分類管理,并與現有化學物質的各項環境管理制度合理銜接。建立企業信息報告和信息公開制度,推進化學品全球統一分類和標簽制度(GHS)實施,加強化學品安全數據表和標簽的推廣實施,在化學品生產、儲存、運輸、經營、使用和廢棄物處置等環節進行信息公示和傳遞,降低化學品環境與健康風險。完善化學品相關國際公約履約機制,開展公約管控物質的限制、淘汰和排放控制,完善國際化學品管理戰略方針(SAICM)部門協商機制,推動SAICM各項行動計劃逐步落實。建立化學品環境風險調查評估機制,定期組織開展環境介質、環境生物及人體中的化學品監測、調查和評估,為化學品環境和健康風險評估提供數據支撐。
3.2 系統開展化學品危害篩查和風險評估
制定化學品危害篩查與風險評估行動計劃,明確化學品危害篩查與風險評估目標、技術路線和分階段實施計劃。開展現有化學物質危害篩查,重點針對高產量化學品以及國內外管制或關注化學品、本國特有化學品等,收集化學物質危害數據,篩查有毒有害物質,建立優先評估化學品清單。開展優先評估化學品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通過對優先評估化學品全產業鏈風險分析和預測,篩選出具有潛在暴露風險的優先評估化學品,開展環境暴露相關數據收集,必要時開展化學品環境風險的監測調查,采用科學方法評估化學品的環境與健康風險,確定高風險化學品,為國家持續更新《優先控制化學品名錄》[23]和制定發布禁止化學品名錄提供支撐。
3.3 推動有毒有害化學品的限制與淘汰
制定完善國家產業政策,加強高風險化學品的國際貿易管控,防止跨境貿易導致的污染轉移。鼓勵環境安全替代品、替代工藝的研發和推廣應用,加快推進高風險化學品的限制淘汰。推動企業全過程采取有毒有害化學品減量降耗措施,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對經濟發展典型區域,加強有毒有害化學品建設項目的環境準入管理,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培育不破壞生態環境的綠色產業和企業。嚴格限制產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質,完善產品中有毒有害物質標識、信息傳遞制度,推行產品生態設計鼓勵綠色環保新材料、新技術產品的研發和應用,打造綠色品牌效應,加快推進產品的更新換代。加大產品消費稅調整力度,充分發揮產品消費稅的調控作用,對使用或添加有毒有害物質的消費品,提高消費稅征收額度,降低產品出口退稅比例或取消出口退稅,對綠色產品降低或免征消費稅,提高綠色產品出口退稅比例,引導和推動涉有毒有害物質的消費產品逐步退出市場。
3.4 加強有毒有害化學品環境污染防治
加大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控制力度,加強環境監測與污染治理,加快推動化工園區有毒有害化學品污染防治。制定完善行業特征污染物排放標準,強化環保督查和信息公開制度。加大重點行業有毒有害污染物減排力度,針對石油石化工業、紡織工業、橡膠和塑料工業、涂料工業和皮革工業等重點行業,推動制定有毒有害污染物減排行動計劃,明確減排目標和實施路線。加強有毒有害污染物環境質量監測與污染治理。開展區域、流域有毒有害污染物環境質量監測,組織對監測區域、流域的環境風險進行全面評估,識別污染因子和高風險因子。推動制定有毒有害污染物環境質量標準,建立有毒有害污染物環境監測機制,推動制定有毒有害污染物環境基準和生態紅線。加快推動化工園區有毒有害化學品污染防治,研究建立化工園區有毒有害化學品生產、使用和排放清單,制定落實有毒有害化學品減量減排措施和實施計劃,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化工園區有毒有害化學品精細化環境管理模式,逐步改善和提高生態環境質量。推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加大企業排污成本,激勵和促進企業減少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推動建立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內化環境成本,提高環境風險監管和損害賠償工作效率。
3.5 提升化學品風險評估與管理能力
加強化學品環境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建設國家級化學品風險評估信息庫和計算毒理模型信息平臺,為風險評估與管理決策提供數據支撐。完善化學品風險評估技術方法體系,制訂化學品風險評估配套技術規范。加強化學品風險管理能力建設,統籌現有實驗室資源,提高實驗室軟硬件配置,培養化學品風險評估專業人才,為國家開展化學品危害篩查和風險評估提供技術支撐。推動建立高水平、智庫型化學品風險管理技術支持機構,集中整合實驗室資源和相關科研資源,加強成果的政策轉化與應用,為國家化學品風險管理提供決策支持。加強地方化學品風險管理能力培訓,加強環境監測與管理人員隊伍建設,全面提升地方化學品環境管理能力和水平。
3.6 促進產業綠色發展
推動樹立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理念,打造綠色產業鏈和供應鏈,發展綠色化工產業,推動綠色化工產品和無毒替代品的開發和應用。發展循環經濟產業,降低有毒有害化學品消耗,減少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發展綠色制造業,在制造業實施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支持企業推進綠色設計,開發綠色產品。發展綠色建筑業,推廣使用綠色建筑材料,減少有毒有害化學品的使用和環境釋放。加強綠色供應鏈管理,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加強化學品合規信息公開和供應鏈信息交換,推動綠色產品供需市場的逐步壯大。改革優化供需關系,鼓勵涂料、金屬清洗等相關行業采用國際上推行的化學品租賃(Chemical Leasing)模式,由銷售產品逐步轉向銷售服務,加快推動化學品減量。
4 結論(Conclusion)
在全球化趨勢的推動下,化學品的跨境貿易變得越來越復雜,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轉移也日益加劇。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化工產業穩居世界前列,但化學品環境管理缺乏戰略支撐,瓶頸凸顯,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形成制約。通過梳理現狀,總結問題,直面需求,從化學品環境管理中長期發展角度,研究提出發展目標和主要行動建議,逐步完善化學品管理法律和制度體系,加強化學品環境風險評估和風險管控,提升化學品風險評估與管理能力,促進產業綠色發展,對我國建立健全化學品環境管理、補齊環境保護短板、縮小與國際社會差距等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