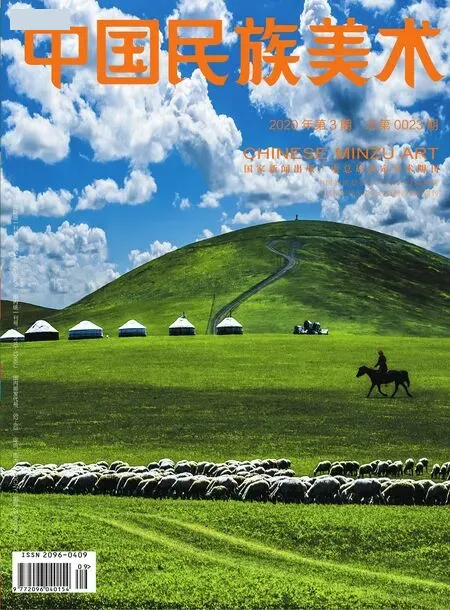油畫中的蒙古族女性形象審美特征及精神表達
文/圖:德德瑪 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2019 級博士研究生

虎仔 金高 油畫 66cm x 126.8cm 1986 年
蒙古族作為我國傳統的北方游牧民族,有其特定的風俗習慣。正如“地域環境具有基礎性潛在的影響力”[1],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特定的生活環境造就了特定的風土人情,“蒙古民族居住在遠離海洋的蒙古高原干燥的環境中。但是歐洲地圖一直把他的部落標記做‘水蒙古’,或者突厥語‘Sun Mongol’。一直待到17 世紀末,歐洲地圖上都是這樣標示的,但是似乎并未意識到這個名字和蒙古人賦予水的地球母親滋養生命的雌性力量之間的聯系”[2]。蒙古族女性的內在共性特征,也和她們生活的地域環境和游牧文化有很大的聯系。本文將蒙古族女性的共性特征歸納為三類。
一、如水般滋養萬物的母愛
在蒙古族人的眼中,河流像母親一樣滋養著萬物。蒙古族女性也像水一樣滋養著生命,蒙古族的母親形象不只是局限于對自己的孩子的愛,還有對其他的孩子,恰如羅曼·羅蘭曾說:“母愛是一團巨大的火焰!”那么,蒙古族的母親更像是寬廣深沉的湖水。電影《額吉》,還有電視劇《靜靜的艾敏河》,講述了蒙古族女性寬廣的母愛故事。20 世紀60 年代初,內蒙古收養了3000 名上海孤兒,蒙古族母親用自己的母愛詮釋了大愛無疆 。“生命”一詞用蒙古語來說就是“艾敏”,艾敏河的鏡頭從頭到尾在影片中一遍又一遍的出現。象征著蒙古族母親像河水一樣滋養著生命。除了愛孩子,蒙古族女性的母愛還表現在對生活在草原上的畜群和一切有生命的事物的愛。在草原上生活,畜群們生下小畜,有時難免會出現母畜不愿意撫養自己孩子的情況,這時,蒙古族女性會為它們唱勸奶歌來喚醒它們的母性,甚至會拉起馬頭琴,有時候會唱得母畜潸然淚下,即使不是自己親生的小畜,也會欣然接受。在描繪蒙古族女性形象的畫面中,常見蒙古族女性或母親,抱著小羊羔等小畜,給它喂養牛奶等。這一點充分體現了蒙古族女性的母性特點是博愛的,是像水一樣滋養萬物的。蒙古族題材記錄電影《哭泣的駱駝》,正是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牧民家中的母駱駝,因為產下小駱駝時痛苦的經歷,不愿意喂養她的幼崽。這時牧民家中的女主人專門從遠方請來了馬頭琴師,伴著她動人的歌聲喚醒母駱駝的母愛。母駱駝聽后感動得潸然淚下,欣然接受了自己的孩子。”
二、勤勞樸實

擠馬奶 金高 油畫 76.2cm x 101.5cm 1985 年

垛草的婦女 妥木斯 油畫 175cm x 175cm 1984 年(中國美術館藏)
除了母親的角色,蒙古族女性作為家族里的一員,勤勞成為了蒙古族女性的又一共性特征,更多的原因是來自于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首先是社會環境,蒙古族女性是家庭的后方主力,家里的一切雜物事,飲食起居無不包含在蒙古族女性的日常勞動中。“韃(靼)人的妻子、兒女、日常用具以及所需要的食物,都用車子運送,車子由牛和駱駝拉著前進。婦女經營一切買賣,家里的日常事務也都由婦女來管理。”[3]在一天的草原生活中,蒙古族女性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一大早就要起來擠牛奶,然后為一家老小準備早茶,之后要制作各種家庭所需生活用品,例如奶制品、肉制品,還有親手縫制蒙古袍等等。由此可見,蒙古族的婦女在家里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無論古今,在牧區的蒙古族男性,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放牧,蒙古族女性則承擔著輔助甚至同樣的任務。在暴風雨雪等惡劣的天氣來臨的時候,蒙古族女性也承擔著找回畜群,安頓好它們的工作。在我國的油畫作品中也經常可以見到蒙古族女性勞作的身影,例如妥木斯的油畫作品《垛草的婦女》中所描繪的正在勞動的蒙古族女性形象,讓觀者從畫面中感受到了蒙古族女性的勤勞,也透出一些和男性相同的能力與擔當。
三、珍愛生命,隨遇而安

蒙古的山 朝戈 油畫 124cm x 86cm 2006 年
對人對生命的尊重和隨遇而安的性格也是蒙古族女性的顯著特征,歌德詩曰:“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走向何方?走向一個更實在的人生,一個更有人情味的社會。”[4]正如蒙古電影《小黃狗的窩》中,牧民家的小女兒因為在山洞里撿來一只不明來歷的小狗,受到父親的指責,因為懼怕這只狗和狼有過瓜葛進而引來狼群侵襲家畜。這時影片中小女兒的母親只是輕描淡寫地表明了她的態度:“他會來我們家,搞不好是注定的!”(影片18 分39 秒處)電影中女主人公多次提到小黃狗與家人的緣分,體現了蒙古族女性對事物的接受、包容和順其自然的態度。蒙古族導演巴音的電影作品《諾日吉瑪》,正是道出了蒙古族女性的這一份人情味。電影講述了30 年代抗戰時期,在草原上撿回兩位身負重傷的敵我兩方的士兵,在精心幫助他們恢復健康的同時,還要竭盡全力阻止他們再次相互廝殺的故事,戰爭是殘酷的,但是電影中的蒙古族女性對生命平等的尊重和珍愛,讓人感動。

遠方 朝戈 布上坦培拉 76cm x 53cm 2003 年
我國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決定了蒙古族女性從小就沒有嬌生慣養的條件,她們大都在生活中扮演著和男性一樣重要的角色,同樣受到尊重。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決定了蒙古族女性必須在生活中參與大量的勞動,要從事所有家務,勞動量很大。穩重、踏實、勤勞是蒙古族女性的共性特征,遇上惡劣的天氣,蒙古族女性必須依賴自己來完成勞動,例如趕牲畜回圈等,體現了蒙古族女性獨立自理的能力。“文化是有適應性的,不同的文化都是適應不同的特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而產生的,所以說文化是適應環境的產物。因此就會有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平原居民的定居農業文化,江河海邊的漁業文化等。”[5]分析我國表現蒙古族女性題材的繪畫,除了作為母親哺育孩子的畫面,大部分都是蒙古族女性勞動的場景,例如照顧畜群、打草、擠奶、等待牧人歸來等等。“無論如何,當藝術家們希冀尋找一個民族的精神及其內在氣質并將它們在畫面上表現出來時,這些現實生活中反映出來的細枝末節都是萬萬不可忽視的。”[6]這些生活場景經過藝術家的精心提煉和描繪,轉移到畫面中,真實地再現了蒙古族女性的生活狀態。
1.母親哺育孩子
女巫一詞和大地女神在蒙古語里是一個詞:巫都干,其本義都有創立者的意思。“蒙古族稱天公地母,認為天是陽性根源,賦予生命,地是陰性根源,賦予形體。”[7]畫家筆下表現的蒙古“額吉”的形象,總是能以其真摯的情感,感動觀眾。例如,金高的作品就表現了蒙古族母子之間的親情關系,在《愛》和《虎仔》這兩幅作品中所刻畫的溫馨場景,就充分地表現了蒙古族女性溫暖、善良的心靈。《虎仔》描繪了母親與孩子溫馨的瞬間,母親身著黃色基調的衣服在視覺呈現上對整個作品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愛》同樣表現的是母子之間的關系,白色的畫面并沒有讓人們感覺出絲毫的寒意,溫暖人心的氣息溢滿整件作品。《綠色搖籃》這幅作品畫面中母親手里拿著正在編織的毛衣,坐在床上,用一只腳輕輕勾住搖籃,雙眼充滿愛意地望著搖籃中的孩子,表現了蒙古族女性溫柔的母愛。

等待醉歸丈夫的好力堡婦人 龍力游 油畫 112cm x 145cm 1995 年
2.擠奶
擠奶是草原上蒙古族女性必須具備的一項生活技能,這關系著家里的奶食來源,同時,奶食品也成了牧民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描繪蒙古族女性擠牛奶的作品很多,例如龍力游的《等待成長的季節》,畫面中站在中間回眸一望的蒙古族女性和遠處正在擠牛奶的蒙古族女性全部身穿布里亞特地區的長袍,因為在牧區,又是日常生活場景,所以并沒有佩戴布里亞特頭飾,而是頭扎亮色頭巾。除此之外,在牧區,蒙古族女性還會擠馬奶、擠羊奶,金高的《擠馬奶》就表現了蒙古族女性擠馬奶的生活場景。
3.打草
打草是草原上一項勞動生產內容,以此為題材最為著名的就是妥木斯的《剁草的婦女》,畫面中的蒙古族女性,身穿白色長袍,右手用一直木叉子剁草,神態悠然自得,仿佛一陣清風吹過,化解了勞動的辛勞。除此之外,妥木斯表現打草的作品還有《剁草》,同樣描繪了蒙古族女性打草的場景。
4.等待
除了描繪蒙古族女性勞動的場景之外,還有一種蒙古族女性生活狀態的定格畫面,就是等待,畫面中的蒙古族女性右手輕輕抬起,左手提著奶桶,眺望遠方,等待牧人歸來。這樣的畫面具有永恒的詩意。就像電影《諾日吉瑪》中的女主人公,經常站在草原的高處向遠方眺望,等待他的未婚夫,一等就是很多年。在油畫作品中,也有不少描繪蒙古族女性等待這一狀態的作品,如朝戈、龍力游都從不同的角度描繪這一瞬間。
朝戈的“等待”,更多的是將這一瞬間的動作化成了永恒的、雕塑紀念碑式的定格畫面。2006 年的作品《虹》畫面描繪了一位側身站立的蒙古族女性,她的右手半彎著舉起,仿佛在遮擋著陽光,又仿佛是在和遠方打著招呼。她的目光眺望遠方,神態淡然又若有所思。身后的一片雨后的彩虹,遠處傾斜的山坡,使主人公處在一個居高臨下的高度上。畫面中的蒙古族女性穿著傳統的蒙古長袍,簡單梳起并自然下垂的馬尾辮。而這幅作品還有一個幅是描繪男性的,就是1989 年的作品《紅光》,有著類似的姿勢和狀態。2006 年的作品《蒙古的山》,畫面主要描繪了蒙古族女性,她身穿藍色蒙古袍,面部呈現在高原日光下勞動所呈現的紅銅色,畫面中的蒙古族女性,神情淡然,幾乎沒有表情,顯得十分安靜,左手手背輕輕依靠在臉頰上,手臂與地面平行,這一刻,仿佛是一瞬間,又仿佛是雕塑般的永恒。斑駁的蒙古長袍和輕輕擦拭汗水的動作仿佛是泄露了蒙古族女性樸實勤勞的天性。遠處有山,但是與畫面最前面的大面積女性形象比較,顯然是十分渺小的。正如題目中描述的,《蒙古的山》,在這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山,而是這里的一位女性,或妻子或母親。從心理層面來講,蒙古族把母親在心里的位置或許看得比物理意義上的山還要高大。朝戈的作品《虹》和《蒙古的山》以及2003 年的作品《遠方》均以相同的姿勢描述蒙古族女性在草原上等待這一生活瞬間。其次,龍力游的《等待醉歸丈夫的好力堡婦人》和《別列古臺又喝醉了》從另一個角度,詼諧地描繪了蒙古族女性對家人的等待之情。
四、結語
蒙古族女性的內在共性特征呈現出的是一種富有自然氣息的淳樸母愛,坦率直爽、勤勞、堅韌、博愛等內在特征成為畫家在繪制蒙古族題材的繪畫時最常見的一種形象。這些具有共性的相貌外形與內在的性格特征,使之成為油畫藝術家們表現蒙古族女性形象時力求還原的形態。
注釋
[1]宋生貴.詩性之魅:藝術美學新論[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6:121.
[2]杰克.威澤佛德.最后的蒙古女王[M].趙清治,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19.
[3][意]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游記[M].肖民,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69.
[4]周國平.在維納斯腳下哭泣[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50.
[5]楊圣敏.民族學是什么[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2.
[6]康笑宇.由民族題材繪畫引發的思考[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4(4):64.
[7]平常.中國女性民俗文化[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8):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