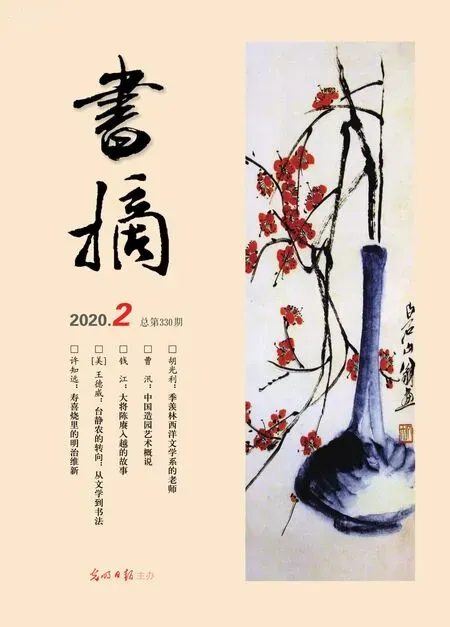我心歸處是敦煌
☉樊錦詩 口述 顧春芳 撰寫
幻想在現(xiàn)實(shí)中蘇醒
我常說自己幾次想離開敦煌都沒有離成,敦煌是我的宿命。
現(xiàn)在想起來,我和敦煌的關(guān)系開始于年少時(shí)的一種美麗的幻想。我小時(shí)候曾在中學(xué)課本上讀到過一篇關(guān)于莫高窟的課文。那篇課文說莫高窟是祖國西北的一顆明珠,有幾百個(gè)洞窟,洞窟里面不僅有精美絕倫的彩塑,還有幾萬多平方米的壁畫,是一座輝煌燦爛的藝術(shù)殿堂……我對這篇課文的印象很深,后來就比較留意和敦煌有關(guān)的信息。特別是念了大學(xué)以后,凡是和敦煌有關(guān)的展覽,包括出版的畫片和明信片,我都格外關(guān)注。因此,我早就知道常書鴻、段文杰這些人,始終很向往那個(gè)地方。
我與敦煌的結(jié)緣始于我的畢業(yè)實(shí)習(xí)。如果1962年的畢業(yè)實(shí)習(xí),宿白先生沒有選我去敦煌,也許就不會(huì)有后來我在敦煌的命運(yùn)。那一年敦煌莫高窟南區(qū)要進(jìn)行危崖加固工程,首先就要?jiǎng)涌咄獾孛嫦碌牡鼗.?dāng)時(shí)常書鴻先生任所長,他非常重視文物保護(hù)和考古研究。他意識(shí)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絕對不能隨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考古工作人員的介入。因此,常書鴻先生就希望北大可以調(diào)一些考古專業(yè)的學(xué)生來進(jìn)行莫高窟外的考古發(fā)掘。我被選中了。
正是1962年的這次實(shí)習(xí)改變了我的命運(yùn)。
記得在去敦煌的路上,我一直想象著常書鴻和段文杰這兩位傳奇人物,他們一定是風(fēng)度翩翩的藝術(shù)家。在此之前,我讀過徐遲的《祁連山下》,這篇報(bào)告文學(xué)的主人公就是以常書鴻為原型的。我覺得這個(gè)人太了不起了,留學(xué)法國,喝過洋墨水,居然放棄了優(yōu)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護(hù)莫高窟。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應(yīng)該是一個(gè)充滿藝術(shù)氣息的很氣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車就立刻傻眼了,這里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樣子。研究所當(dāng)時(shí)的工作人員,一個(gè)個(gè)面黃肌瘦,穿的都是洗得發(fā)白的干部服,一個(gè)個(gè)都跟當(dāng)?shù)乩相l(xiāng)似的。
原來,從1959年開始,我國經(jīng)歷了持續(xù)三年的困難時(shí)期,全國上下糧食短缺,甘肅當(dāng)時(shí)是重災(zāi)區(qū)。到了敦煌,我才真正感覺到這個(gè)地方的貧窮和落后。雖然當(dāng)時(shí)全國范圍最困難的時(shí)期已經(jīng)過去,但是甘肅敦煌地區(qū)依然食物緊缺,很多人只能打草籽充饑。
在莫高窟的畢業(yè)實(shí)習(xí)
1962年,是我大學(xué)生活的最后一學(xué)年。按照北大歷史學(xué)系考古專業(yè)的慣例,畢業(yè)班學(xué)生可以選擇洛陽、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遺產(chǎn)地參加畢業(yè)實(shí)習(xí)。當(dāng)時(shí)有不少同學(xué)都想選擇敦煌,因?yàn)槟呖咴诖蠹倚哪恐惺侵袊鸾淌咚逻z跡的典型。對我而言,敦煌同樣是內(nèi)心格外向往的地方,敦煌那么遠(yuǎn),如果能趁著畢業(yè)實(shí)習(xí)的機(jī)會(huì)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卻一樁心愿。
我們一到敦煌就迫不及待地想進(jìn)洞參觀,負(fù)責(zé)給宿白先生和我們幾個(gè)講解的是大名鼎鼎的史葦湘先生。史先生是四川人,說著一口四川話,我聽不太懂。但是史先生講起敦煌來,非常有激情,很吸引人。洞中的溫度遠(yuǎn)比我想象的要低,我感到有一股刺骨的寒氣從地層蔓延上來。然而看著洞窟四壁色彩斑斕的壁畫,我就忘記了寒冷。
1962年也是敦煌歷史上的一個(gè)重要時(shí)刻。正是這一年,周總理批示撥出巨款,啟動(dòng)敦煌莫高窟南區(qū)危崖加固工程。為配合加固工程,常書鴻先生向正在敦煌莫高窟帶著學(xué)生畢業(yè)實(shí)習(xí)的宿白先生提出,希望北大考古專業(yè)可以推薦四名參加實(shí)習(xí)的學(xué)生今后到敦煌工作。這四名學(xué)生,除我之外,還有馬世長、段鵬琦和謝德根。到了畢業(yè)分配的時(shí)候,宿白先生向常書鴻推薦了我和馬世長兩人。馬世長后來也是著名的佛教考古專家,回到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教書,從事中國佛教考古的教學(xué)與研究。
馬世長的母親聽到兒子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之后,號(hào)啕大哭。她所有子女里,只有馬世長是男孩。后來,馬世長的母親來火車站送別馬世長和我的時(shí)候,哭得像個(gè)淚人兒,特別囑咐我們要互相照顧。

敦煌石窟
我在畢業(yè)分配會(huì)后才被告知,為了我和馬世長到敦煌的分配,整個(gè)分配方案的宣布,推遲了兩三天。宣布會(huì)后,系里的領(lǐng)導(dǎo)找我談話。系里知道我的體質(zhì)很差,而且也已經(jīng)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還是希望我能夠去敦煌。因?yàn)槎鼗图毙杩脊艑I(yè)的人才,希望我和馬世長先去,北大今后還有畢業(yè)生,過三四年再把我替換出來。就是這個(gè)理由讓我看到了一點(diǎn)希望。
分配方案宣布之后,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沒想到,父親很快回信給我。這封信很厚,打開一看,信里夾帶著另一封寫給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和系領(lǐng)導(dǎo)的信,是囑我轉(zhuǎn)呈的。父親的來信我還記得,信是豎著寫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信里講了很多事實(shí)和實(shí)際的困難,主要是說“小女自小體弱多病”等諸如此類的話,希望學(xué)校改派其他體質(zhì)好的學(xué)生去。
但是,我看完父親的信就想,這能交嗎?仔細(xì)再一想,不行,絕對不能交。為什么?因?yàn)楫?dāng)時(shí)系里對畢業(yè)生進(jìn)行畢業(yè)教育的時(shí)候,鼓勵(lì)學(xué)生學(xué)雷鋒,學(xué)雷鋒就要看行動(dòng)。當(dāng)時(shí)的大學(xué)生奉獻(xiàn)國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發(fā)自真心的。國家需要我們到什么地方去,我們就到什么地方去。我自己已經(jīng)向?qū)W校表了態(tài),服從分配,如果這時(shí)候搬出父親來給自己說情,會(huì)給院系領(lǐng)導(dǎo)造成言而無信的印象。所以這封信我沒提交。
蘇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見
畢業(yè)離校前,發(fā)生了一件令我很難忘的事情。有一天,蘇秉琦先生突然派人來找我,專門把我叫到他在北大朗潤園的住處。蘇先生當(dāng)時(shí)是北大歷史學(xué)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與夏鼐先生齊名的考古學(xué)界的泰斗。那蘇先生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呢?
在校期間,我雖然沒有很多機(jī)會(huì)向蘇先生請教,但心里一直對蘇先生充滿敬意。此次蘇先生專門找我去,令我既倍感幸運(yùn),也有點(diǎn)忐忑。到了蘇先生的住處,他慈祥地對我說:“你去的是敦煌。將來你要編寫考古報(bào)告,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漢代歷史,人家會(huì)問,你看過《史記》沒有?看過《漢書》沒有?不會(huì)問你看沒看過某某的文章。考古報(bào)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樣,非常重要,必須得好好搞。”我突然意識(shí)到學(xué)校把我分配去莫高窟,其實(shí)是要賦予我一項(xiàng)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對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蘇先生臨走前的這一番叮嚀,現(xiàn)在回憶起來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完成這個(gè)使命。在步出朗潤園的那個(gè)時(shí)刻,我是恍惚的,我反復(fù)問自己:“我能完成嗎?”我沒有想到這一去,就是半個(gè)多世紀(jì)。我更沒有想到,敦煌石窟考古報(bào)告的任務(wù),我竟然長期未能交卷。經(jīng)過曲曲折折,反反復(fù)復(fù),歷經(jīng)近半個(gè)世紀(jì),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我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報(bào)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艱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夠堅(jiān)持下去的歷史重任。我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會(huì)讓我走上領(lǐng)導(dǎo)管理崗位。之后,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幾乎全都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護(hù)、研究、弘揚(yáng)和管理工作中。
去敦煌前,我回了一次家,在上海度過了大學(xué)時(shí)代的最后一個(gè)暑假。父親那時(shí)候已經(jīng)知道了我的決定,他也就不再多說什么,但是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沉重。最后我要?jiǎng)由淼臅r(shí)候,他只對我說了句話:“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就好好干。”我掉眼淚了。
“文革”之后,馬世長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他離開了敦煌。而我當(dāng)時(shí)正在干校,錯(cuò)過了北大的考研,也再一次錯(cuò)過了離開敦煌的機(jī)會(huì)。所以我說,我這個(gè)人命中注定,這一輩子就交給敦煌了。
重回莫高窟
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8月,我跟著宿白先生和幾個(gè)同學(xué)一起去做畢業(yè)實(shí)習(xí)。第二次去敦煌,就只有我和馬世長兩個(gè)人。我心里知道,這一次去敦煌就不是在那里待幾個(gè)月了,而是要長時(shí)間在那里生活。
火車行駛在河西走廊,經(jīng)過武威、張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爾可以看到遠(yuǎn)處的綠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涼寂寥。
我記得經(jīng)過三天三夜的長途跋涉,火車抵達(dá)了柳園這個(gè)地方。當(dāng)時(shí)敦煌沒有火車站,離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園火車站。從柳園到敦煌還有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這段路沒有火車,只能坐汽車,路途顛簸。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時(shí)候,我已經(jīng)是兩腿發(fā)麻,兩眼發(fā)暈,幾乎是搖搖晃晃地下了車。這兩次去敦煌,是截然不同的心情。唯一相同的是再次來到莫高窟時(shí),我還是急切地想進(jìn)洞看看洞窟里的壁畫。
第45 窟的塑像精美絕倫,那是整個(gè)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薩造像。站在這些塑像前,你會(huì)感到菩薩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菩薩像的表情溫柔而親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純真的少女,梳著雙髻,秀眉連鬢,微微頷首,姿態(tài)嫵媚,面頰豐腴,雙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菩薩像袒露上身,圓領(lǐng)無袖的紗衣,在肩部自然回繞下垂,紗衣上的彩繪花朵,色彩依舊鮮亮如新,一朵朵點(diǎn)綴在具有絲綢般質(zhì)感的衣裙上。菩薩赤足站于圓形蓮臺(tái),和那些天龍八部、金剛羅漢不同,他們仿佛就是有血有肉、有世俗感情的人。
第112窟的《反彈琵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敦煌的標(biāo)志性壁畫,是最能代表敦煌藝術(shù)的圖像。以前在畫冊上看到過,現(xiàn)在近在咫尺,感覺完全不同。畫面表現(xiàn)的是伎樂天神態(tài)悠閑雍容、落落大方,一舉足一頓地,一個(gè)出胯旋身凌空躍起,使出了“反彈琵琶”的絕技,仿佛能聽到項(xiàng)飾臂釧在飛動(dòng)中叮當(dāng)作響的聲音……

有一段時(shí)間,我特別喜歡在黃昏時(shí)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對鳴沙山崖體上的石窟,在那里可以望見整個(gè)莫高窟。我第一次看到崖體上的莫高窟的時(shí)候,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樣錯(cuò)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雙眼睛,每一雙眼睛里都充滿了滄桑和神秘。敦煌的天格外藍(lán),這種藍(lán)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純粹,更遼闊,更濃烈,不到大漠是不會(huì)知道世上有這樣幽藍(lán)幽藍(lán)的天空的。我有時(shí)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陽還沒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覺升起來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輝的景象。
初到莫高窟的時(shí)候,我常常想,為什么在被世人遺忘的沙漠里會(huì)產(chǎn)生如此輝煌的石窟藝術(shù)?為什么敦煌仿佛被遺棄在此長達(dá)幾個(gè)世紀(jì)?這些由壁畫和彩塑營造而成的佛國世界曾經(jīng)是什么面目?在這里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事情?在這個(gè)絲綢之路曾經(jīng)的重鎮(zhèn),莫高窟擔(dān)負(fù)著什么使命?那些金碧輝煌的壁畫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那些精美絕倫的壁畫是什么人畫的?……這些問題每天都縈繞在我的心頭。
所有種種,都在向我傳遞著一種強(qiáng)烈的信息,那就是敦煌的空間意義非同凡響,這里封存的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奧秘,這里是一個(gè)獨(dú)一無二的人類藝術(shù)和文化的寶庫。也許,我傾注一生的時(shí)間,也未必能窮盡它的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