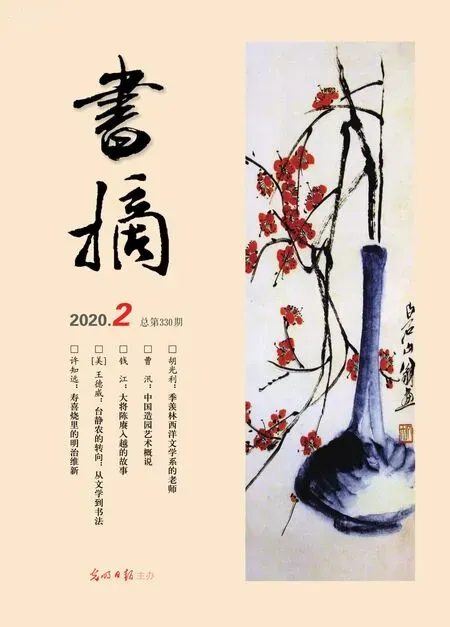意大利米蘭華人一百年經歷的風雨
☉[意]馬泰奧·德蒙特 柴·洛基 著 孫陽雨 譯
項目與展覽
“Chinaman”這一名詞曾被歐美國家專門用來稱呼那些于19 世紀左右零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那時歐洲列強帝國主義和迅速擴張的年輕美國在這些地域內鏟除森林、建造種植園、開礦、修造鐵路,以及從宏觀意義上講消滅當地人口、社會和文化。如今這個名詞帶有些許殖民意味,甚至很多中國人認為它具有侮辱性。不過這個詞也算是一種反映,為我們還原了初代華人移民的一種視覺形象,有一點悲劇色彩,如此遠離先祖生長的土地,但初次露面便令人震驚不已。他們幾乎全部是男人,因為20 世紀前期還很少有女性移民到西方國家。
這些中國人摻雜在外國人——“番人”的汪洋中,“番人”這個詞的寓意至今在青田方言中仍然能喚起西方人帶來的那種不可避免的怪異與差距感。作者選擇了如此一個滿載著失衡與發散的模糊感的詞匯,是期望將意大利歷史上被遺忘的這一章能再次嵌入整個歐洲及世界華人移民故事中。因為在意大利第一批中國人幾乎都是男性,對他們形象的描繪也都表現著同樣的自滿、同樣的天朝王國優越感,夾雜著殖民者的父權主義與異域的夢幻,當時所有西方世界的報紙都在談論他們。同時也是因為披著“Chinaman”的外衣就能意外地從傳統束縛中解脫出來。這意味著外國的中國移民要重新建立一種社會身份,即“華僑”:國際化、獨立性、闖蕩的勇氣。他們有著這樣一個形象:身著合體的西服、頭上斜戴一頂費多拉帽、姿態和語言根據經驗精心潤飾,在新社交圈內越來越得心應手,首先解決生計問題,然后一步步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
從浙江到歐洲
港口城市溫州的內陸是一片多山的地帶,坐落于中國浙江沿海地域的最南端部分,出生于那里的人們從19 世紀末就開始以一定的頻率造訪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了。不過直到20 世紀前二十幾年,來自浙江南部的中國商人才開始陸續參加國際展會,并為了尋求與歐洲穩定的貿易關系開始在一些歐洲城市組建小型集體的長居場所。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馬賽和的里雅斯特這樣的港口城市,或是莫斯科、柏林、巴黎這樣的大都會,為某些初代移民提供了充當中間人的機會,幫助那些想要以他們為模范的親友同鄉在歐洲尋找良機。這些第一批浙江移民起初主要都是做流動商販或海員,其中一些工作環境后來起到了擴大這張移民網的作用、讓他們長久以來一直能夠保持著流動性。
將移民的所有先驅以及來自更小村鎮的后繼者全部算上,我們可以只用一個直徑五十公里多一點兒的圓就將他們的家鄉村鎮整整覆蓋。起源的這個地帶圍繞著山脈延展,將甌江與飛云江相隔,也包括了一些在邊界上零散分布的小村莊,分割了如今麗水市青田縣與溫州市轄區的文成、瑞安與甌海。
從歷史上看,我們可以認為青田縣就是移民大潮的起源地、尤其是民國時期設立的青田縣。為了更好地理解究竟為何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國際移民潮之一發源于這樣一個偏遠的中國農村地帶,我們首先需要考慮到這片土地上的歷史特色生產資源之一——葉蠟石礦。這些石礦分布在山脈中,分隔了四都鄉和方山兩條山口附近的甌江支流。這種礦石在中國以“青田石”而聞名,很多世紀以來都是中國工匠所偏愛的石材,因為有著極高的審美價值與可塑性。青田石的表面十分致密、光滑,手感溫潤如玉,但遠比玉石質軟、易加工,因此從明代開始就是理想的印章雕刻藝術原材料。這些來自邊界山谷中用青田石制作雕刻品的石匠手藝十分精湛,讓這些手工制品的商業傳播越發廣泛。整個歐洲帝國主義時代,都彌漫著對異域物品的熱情,一些青田商人抓住良機,從19、20 世紀眾多商業展會中展示的中國商品中專門挑選了青田石小雕像和擺件進行推銷。初代移民中的一些華僑最初就是作為中國工藝品流動商販在歐洲開啟事業之旅的。而意大利自然而然就成為這些來自中國大陸,尤其是浙江省的移民大潮的主要目標之一。

上世紀20年代米蘭街頭的華人首飾商販
國際展會的重要性
大概最初吸引青田縣移民來意大利的契機就是1906年的世博會了,當時中國皇家代表團也受邀出席。沒落中的大清帝國只申請了一個小小的漁業展館,雖然引起了人們的好奇,但同時也不乏諷刺的聲音,如《信使報》于1906年8月20日就已表示擔憂:“奇怪的黃色危機形態:歐洲被炸魚侵襲了嗎?”而一些青田商人在經歷了法國巴黎和美國圣路易斯世博會后,最終在米蘭世博會向全權機構對意大利的訪問之旅提出投訴,稱在這些展會期間中國人經常被不尊重地對待。第一階段最著名的移民之一就是吳乾奎,他來自方山鄉的龍現村,于1905年至1906年造訪比利時和意大利,推銷自己的商品(青田石小雕像和名貴綠茶)。像吳乾奎一樣的人,他們親手編織了商貿關系網,比如與意大利進口商簽訂合約、引進中國和日本的特色商品,然后將米蘭列入未來同鄉移民可以落腳的城市名單中。10年后人們也看到,這些與展會密不可分的聯系也讓青田縣華人的命運與所謂的“洋蔥店城”連接在了一起。這一地區是緊鄰沃爾特門的城郊聚居區,集中了很多小型手工作坊,還有帶涼臺的公寓,沿著整個區域的中軸——卡諾尼卡路分布。這個地方距離世博會和之后其他許多展會的舉辦地森皮奧內公園只有幾步之遙,非常便利,因此對于奔波經商的人們來說是個舒適的落腳點,可以輕松尋覓到住所與伙食,而且價格低廉。
假珍珠、領帶、皮制品
1925年至1926年,一家總部設在上海、子公司設在巴黎的專營人造珍珠的法-日-中商貿公司為了開拓歐洲市場而雇用了大量的商業中介,于是數百名青田人向著法國起航,其中有很多人都曾經是日本華僑。可能是因為在法國合法流動經商受到限制,1926年2月至3月期間很多人又集體遷移到了意大利。正如當年報紙媒體描述的那樣,這次珍珠商販的“入侵”才真正標志著浙江南部移民進軍意大利的開端。此后20 世紀的每次移民潮,在某種程度上都和那些在歷史上首先發起移民的人們有關,直到2010年,盡管人數持續減少,但前往意大利的移民也還是來自同樣的那幾個鄉縣。
珍珠商史無前例的成功讓他們與公民權利機關的關系緊張起來。他們被指控有不當競爭行為,甚至被懷疑是為莫斯科服務的布爾什維克間諜。這些珍珠商人被不斷地疏散,30年代初就只在都靈和米蘭剩下了寥寥幾個核心人物,不過米蘭也與此同時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珍珠生意受歡迎的階段走到盡頭后,有膽量的流動商人開始從意大利批發商手中進貨,販賣領帶、女士肩帶、皮帶、針織衫和其他百貨商品。卡諾尼卡路上那些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出租的有涼臺的公寓又重新利用起來,形成了一個小型流動商販聚居地,幫助了他們之后向整個意大利北部各大展會市場進發。就是在這樣一種充滿艱辛的小人物聚集的環境下,這些人懷著夢想從自己的鄉村出發到了大都會的邊緣,其中一些人成功追求到了年輕的意大利女工。第一場意中婚姻于1934年結合,此后便源源不斷地涌現出跨國情侶、婚姻甚至是全家福。
意大利華人在集中營的拘禁生活
從1940年5月20日起,內務公共安全部總領辦公室要求,意大利王國各行政區要清點外國公民,因為意大利隨時可能與德國納粹并肩參戰,非意大利籍公民可能會被定義為“來自敵國的國民”。在可能成為敵國的名單中,中國也包括在內,被清查的共有431 名中國公民,主要定居在米蘭和博洛尼亞,此外還有人口相對較多的群體,分布在都靈、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1940年6月,意大利正式參戰,中華民國的“敵國”身份仍然不是很明確。從一方面來講,意大利在1937年11月與德國和日本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因此意中兩國關系大幅冷卻。但從另一方面來講,意大利并沒有直接利益促使其破壞與蔣介石政府的外交關系,同時也是為了繼續維護在中國境內仍然在名義上或實際上歸屬于中華民國的區域內,本國方面的外交與經濟使節。1940年9月27日,《三國同盟條約》的簽署標志著羅馬-柏林-東京中軸的誕生,無疑讓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國公民處境堪憂,可能最早于9月開始的幾次大范圍清掃活動也并非偶然,尤其是1940年 9月20日和 10月3日發生在米蘭的行動,導致41 名米蘭華人遭到拘禁。與蔣介石政府外交關系的徹底破裂直到1941年7月22日才正式確定,那時意大利與德國正式承認了汪精衛政權,但直到中國對意大利、德國和日本宣戰后,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國公民才正式被劃分為“敵國國民”。不過根本上的模糊性仍然存在,因為盡管這些公民仍然持有前任政府發放的護照,但大部分這些華僑都來自中國的同一地區,而這地區名義上仍然屬于由羅馬承認的汪精衛偽政權。因此,意大利對他們在參戰前采取的政策其實是帶有預防性質的,也就是說隨時可以快速執行遣返政策,就算條件不允許,那么也要確保這些中國公民處于嚴密的監控之下。

1945年米蘭部分華僑合影
1940年 6月10日,意大利對法國、英國宣戰。宣戰那幾天中,意大利南方一些省份和位于前線的一些省份開始在自己的領地內對中國公民執行拘捕行動,將他們發配至市政管轄的邊境地區,或是在證實了因英國海軍封鎖而無遣返可能的情況下,將他們關進集中營內。1940年,共有137 名中國公民被捕及拘禁,大部分是在米蘭、羅馬、那不勒斯、的里雅斯特、特雷維索、波拉遭到圍捕,搜捕的高峰集中在9月,因為《三國同盟條約》在9月簽訂。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1941年7月,意大利那時正在準備承認汪精衛的親日政權,與自由中國的外交關系即將破裂。一個新的逮捕與拘禁階段開始,這次主要牽扯到都靈以及的里雅斯特和熱那亞的港口地區,這些地方的小型華人群體主要是在往來于歐洲與東方之間的汽艇上做工。起初啟用的主要是阿布魯佐大區的托西恰和博亞諾集中營,以及莫利塞的奇維泰拉德爾特隆托集中營。不過從1941年起,指定的中國人集中營就逐漸轉向了伊索拉德爾格蘭薩索,1942年 5月16日有 116 名中國被拘禁的公民從托西恰轉至此,全部被拘禁的中國人人數提高到了175 名。盡管營內人滿為患,但伊索拉德爾格蘭薩索的條件要遠比博亞諾、奇維泰拉德爾特隆托和托西恰的集中營好很多,那些地方的衛生健康狀況差到極點。而在伊索拉德爾格蘭薩索,拘禁人員主要是在圣加布里埃爾教堂的客房區域居住,距離伊索拉德爾格蘭薩索市中心住宅區只有兩公里遠。集中營直接由當地市長接管,而警衛配備則是由一位軍士指派的幾名憲兵負責。
伊索拉的拘禁人員擁有一定的行動自由,盡管名義上他們禁止踏出任何集中營范圍的地方,如果違反將會有巨額罰款。不論這些小小的“逃跑”行為是否被正式準許,總有人經常違反規定,因為雖然相比起托西恰來說這里的拘禁生活條件并沒有那么嚴苛,但終歸缺乏高質量的飲食,缺少厚實的衣物和鞋子來度過島上那些年的酷寒冬季。1941年的記錄上,尤其是從7月意大利與蔣介石政府外交關系即將破裂開始,有超過一百名中國人被逮捕拘禁。7月末到9月初,在一系列極為頻繁的掃蕩行動之后,幾乎所有在都靈、的里雅斯特和熱那亞的中國人都被監禁起來了。定居都靈的中國人大多是領帶、針織品、錢包、肩帶和皮帶流動商販,與都靈和米蘭的意大利批發商擁有信用良好的合作關系。
此后這些中國人決定帶著自己的歐洲家庭(因為與中國國民通婚而放棄意大利國籍、加入中國籍的妻子和兒女)返回中國。1946年9月21日,奧特蘭托汽船從那不勒斯起錨,開往香港,將這些大部分來自德國和意大利的中國人帶回祖國,戰爭與監禁耗盡了他們的希望。同年,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國政府為300名左右經受了拘禁、炸彈襲擊、財產沒收或法西斯欺凌的中國人發放了將近十八萬里拉的戰爭補償(大致相當于一位工人兩年的薪水總和)。這個數字在當時十分可觀,足夠他們在中國重新起步。
戰后
選擇留在意大利的少數一些人,以及更少的成功回到中國卻又再次遇到內戰與革命的人們,他們的故事中始終貫穿著牢固的感情聯系,他們的家庭、同鄉以及同一城市同一社區的人們從未將他們拋棄。而且他們的故事是高度真實的社會救贖的歷史。他們勤勤懇懇日復一日地工作,只能在麻將牌的敲擊聲中才能化解勞頓。20 世紀80年代的華人社會再次迎來了向著意大利進發的移民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