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最干凈的葡萄酒
☉沈愛民
打開世界地圖,向南看,過赤道,南緯15至45 度之間,有兩個地方,一個大,一個小;一個是大陸,一個是島;一個叫澳大利亞,一個叫新西蘭。它們與地球其他地方相隔甚遠,安靜地相守在大洋中央。
去過兩次。寫這篇文字的時候,又讓我想起那個純凈的遠方。如果,我也會產生說走就走的沖動,那么,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了。
澳新都出好葡萄酒。說起那里的酒,只要有些葡萄酒入門知識,腦海里跳出來的第一個詞應該是“新世界”。第二個詞,也許是年輕,起碼對我而言是這樣。
沒錯,澳新的葡萄酒,都是典型的新世界酒。至于年輕,是說對它的感覺。年輕代表著清新,有活力,激情外溢,這些也正是澳新葡萄酒的標簽。它們柔和香郁,輕盈適口,笑呵呵地擁抱每一個接觸它的人。不像老世界的葡萄酒,戴著禮帽,矜持少語,讓你欲言又止,或者一言難盡。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作為獨立國家的歷史,都不算長。澳大利亞也就是一百來年,新西蘭還不到七十年,與老世界國家相比,確實還是一個年輕人。澳新釀造葡萄酒的歷史,也不長。澳大利亞的釀酒業比國家歷史還長些,有兩個世紀了吧,但真正發展起現代葡萄酒的釀造業,也就是近幾十年的事情。新西蘭發展葡萄酒的歷史更短,算是全球葡萄酒世界最年輕的小朋友之一,全國70%的葡萄樹的樹齡都在10年以內。
因為年輕,澳新都喜歡采用現代釀造方法,減少浸提時間,使用螺旋酒塞。老世界津津樂道的“年份”,在這里變得無足輕重。因為澳新氣候穩定,每年的雨啊光照啊都差不多。喜歡盲品的品酒客,如果意欲對澳新酒進行年份“垂直”盲品,估計要做好心理準備,勝算不大。
實際上,澳新的酒,都不適合陳年。年輕的酒,最適合年輕人在酒還年輕的時候喝。
雖然年輕,但是發展速度驚人,在全球各種葡萄酒評比中屢獲佳績,市場份額不斷擴張。更為難得的是,還形成了各自風格。正如提到勃艮第就會想到黑比諾,提到德國就會想到雷司令,澳大利亞把西拉子、新西蘭把長相思也都做到了極致。青出于藍勝于藍,這句話用在這里很恰當,從歐洲來的這些葡萄品種,在異國土地上大放異彩,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一個地方的葡萄酒,基本就是那里環境、文化的濃縮和名片。

初到澳新的人,尤其是來到新西蘭,最突出的感受應該是生態環境。無論走到哪里,到處都很養眼,綠色從來沒有斷裂,一直鋪在視線所及的任何地方。據說游客返程上飛機時,眼睛都冒綠光。
路邊都是高爾夫球場一樣的草地。實際上高爾夫球場也確實處處可見,按照這里的說法,隨便在哪兒挖幾個洞,就是高爾夫球場了。因此私人球場不少,高爾夫在這里是平民運動。
這里農民不知化肥與農藥為何物,因為不準使用。所以,蘋果擦擦就可以吃。水當然沒有污染,工業很少。據說曾有日本人把這里的空氣用易拉罐裝了,在氧吧里賣。
這里的人甚至不吃自家院子樹上的水果,要吃水果去超市買,長在樹上是用來裝飾的。大街上幾乎沒看到清潔工,也許是風把落葉和塵土帶走了,也許本來就沒有多少塵土。
這是一個溫柔的國家。有羊、牛和馬,卻沒有兇猛動物,沒有虎狼,甚至連蛇都沒有一條。
這里的人們很悠閑。人人有養老金,退休還可以拿退休金。有困難,可以申請補助。不工作,可以拿救濟金,救濟金每周二百多元,每年一萬多,相當于六萬人民幣,在這里也夠溫飽,甚至可以買臺二手老爺車。
所以,這里基本沒有小偷。按照向導老錢的話,偷東西翻墻多辛苦,還不如躺在沙發上領救濟金。他之所以放棄臺灣較好工作移民至此,是妻子當時來旅游時,看到每家門口的空牛奶盒子里都有當日奶錢,送奶車經過,把奶留下,把錢拿走,沒有聽說過有丟失奶錢的。現在,沒有這種送奶的方式了,但是,路不拾遺似乎仍然是這里大部分地區的現實。據說新西蘭人家里都沒有空調,因為用不著。也都沒有防盜網,因為也用不著。
環境影響的不只是人,更是所有生命,包括植物,包括葡萄釀出的酒。新西蘭葡萄酒有句著名廣告詞:“發現純凈。”澳大利亞也是如此,他們說,到澳大利亞來吧,“感受最干凈的葡萄酒。”正是新西蘭的酒莊,釀造了世界上首款獲得“零碳排放”認證的葡萄酒。
特殊環境造就了所謂的“新西蘭風格”。喝新西蘭的酒,能喝出清澈雨水、剔透冰峰、安靜夏日的味道。描述新西蘭葡萄酒香氣的品酒詞用得最多的是青草、青椒、青皮橘、青芒果等泛青味道,或者是鵝莓、蘆筍、西番蓮等清新果花香。沒有濃重、晦澀,只有輕盈在起舞,清冽多陽。
似乎不用品飲,輕輕一嗅之下,就到了綠島中央。
澳新的人,如同這里的空氣和海水,簡單,純樸,友善,一眼能看穿,特別好相處。這里的酒也如此。圈內有個說法,用快樂心情釀出的澳新葡萄酒,與世界其他產區同等價格的葡萄酒相比,質量要高出許多。另外,這里的酒有副好心腸,不挑剔,不很酸也不很澀,最適宜與各種不同食物聯姻,成就完美搭配。
其實,這也許只是澳新呈現的一個正面影像。它的背影,卻訴說著另外的味道。
大洋洲,地球上最小的大洲,四面都是汪洋。向北望,那些人類歷史上的繁華中心,都在赤道那一邊;向西看,波濤洶涌印度洋;向東看,浩浩蕩蕩太平洋;向南看,人跡罕見南極洲。
大洋洲,大洋匯聚,萬水中央。
它還有一個別稱:地球上最孤獨的大洲。
清晨六時,被瘋狂的吉他聲弄醒。在床上想象著彈奏者的樣子,他是誰,為了什么,要在一個清晨,如此需要傾訴。過了一會兒,吉他聲音消失了。我試圖縫合攪醒的睡眠,幾次努力失敗,睡不著了,起來打開窗戶,街上空空蕩蕩。吉他手吵醒一條街后,就消失了。
于是出門,在悉尼市區里隨意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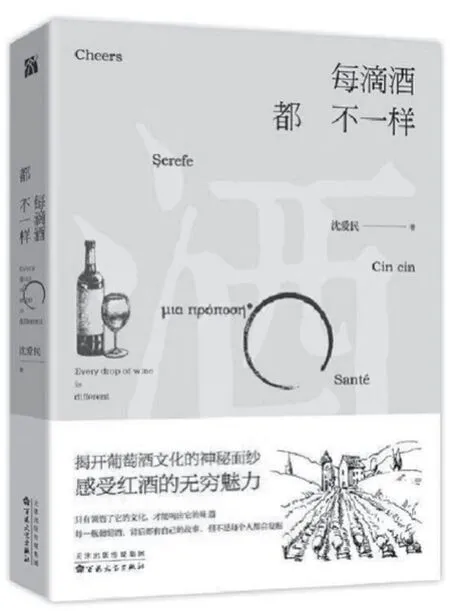
早上街上行人還不多,鴿子挺多。小店也很多,都沒開門,只有一個剛開門的年輕老板娘,帶著晚上的氣息坐在店門口的臺階上。我走過去,她沖我一笑,樣子很適合這個早晨。
傍晚,來到情人港。手冊上說這里有夕陽、海風、帥哥靚女。我坐在一個長條枕木上,沒看到夕陽,沒有海風吹來,也基本上沒有帥哥靚女,尤其是沒有靚女。
夜有些深了,往回走。發現真正人滿為患的場所,都是酒吧。燈光晦澀,人影憧憧,男人一般,女人肥美。女孩們穿得都少,香水味在人行道上出沒。人人端個酒杯杵在那兒,說些不咸不淡的廢話。
有數據說,澳洲人每年人均飲酒量為23升,是法國人的兩倍,在英語國家里排名第一。這些純樸友善的人,確實喜歡酒。我用拼音輸入法敲前面“友善”這個詞的時候,多敲了一個g,跳出來的詞是“憂傷”。
從悉尼乘車去堪培拉,三百多公里,大約4小時。資料上說這段路程會有大片草場和牛羊。其實沒有,或者說沒那么多。我曾經有一次乘飛機從這片土地上空飛過,挺荒蕪的。
很單調的路,兩旁只有桉樹林,比戈壁沙漠還單調。戈壁沙漠表情很多,這里只有一種,像是在不停地說,我是桉樹林,我是桉樹林。
住的汽車旅館倒是出乎意料地好,睡了個好覺。
早上出去晨跑,走了出來,空氣好,濕度和溫度都好,還有微風,令人舒適的要素很齊全。周圍開闊,干凈,安靜,冷清,看不到人,令人寂寞的要素也很齊全。
我有些納悶,這樣的地方,為什么沒聽說出過好作家?即使不適宜出作家,為什么也沒出過哲學家、思想家?或是為什么也沒出瘋子?我是說著名的瘋子。舒適和寂寞都占全的地方,容易出瘋子。
街區還沒醒。太陽剛出來。路上沒車。房子周圍沒人。這個還在睡的街區,疏影,花叢,平房,看起來很和諧。可是這些屋子里的人,過得好嗎?
路邊有個長椅,上面放著一個酒瓶。昨晚這里有人喝酒,顯然是一個人,也只喝了一瓶。他或她,在想誰嗎?
我曾在很多國家很多城市的清晨走過街道,經常看到摔碎的酒瓶碴。那些碎碴,來自宣泄和憤怒。看得出來,長椅上的這人并不憤怒,它看上去,只是一個孤獨的酒瓶。
也許,在這個大陸,有很多人,都會在某個夜里,坐在桉樹下的長椅里,喝上一瓶酒。
太陽升起來了。街區正在起床。有些房子,花還在,只是有些枯萎了。草也長亂了。門前臺階護欄上,有些斑駁銹跡。凌晨送來的報紙還扔在地上,沒人來撿。主人的日子似乎過得不是很精心,這也許是個不完整的家。女主人或者男主人不在,剩下的他或她也老了。
澳洲葡萄酒歷史雖然不長,卻有些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樹。比如在南澳的巴羅薩谷,這里是澳洲最著名的葡萄酒產區,有些家族的葡萄種植和釀造事業已經傳承到第六代了。這里由于與世隔絕,一些古老的葡萄樹,躲過了席卷整個歐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亞東岸的根瘤蚜瘟疫,得以幸存。用這些古老葡萄藤釀出的酒,倒有些老世界的滄桑味道。

新西蘭奧塔哥黑比諾葡萄產區
與老世界相像的,還有新西蘭的黑比諾。有資深酒評家曾經說,“我會毫不猶豫地儲存一瓶新西蘭黑比諾,甚至優先于勃艮第出品的。”新西蘭南島中部的奧塔哥,因其廣袤荒涼,成為《指環王》的拍攝地。這有新西蘭最極端的氣候,夏季炎熱干燥,冬日冰凍入骨,一般果樹在這里難以生存。出乎意料的是,養尊處優的貴族小姐黑比諾,在這個世界最南端的葡萄酒產區,竟然得其所哉,靜靜綻放。
據說,黑比諾最適合生長的地方,需要兼具內陸與海岸氣候特點,全球只有三個地方具備條件,北半球是法國的勃艮第和美國俄勒岡州的威拉麥狄谷,南半球就是新西蘭的奧塔哥。用這里的黑比諾釀造的葡萄酒,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優雅又敏感,復雜又純凈。
如果一個人具備這樣的特點,他(她)不會很幸福,他(她)多半會是個憂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