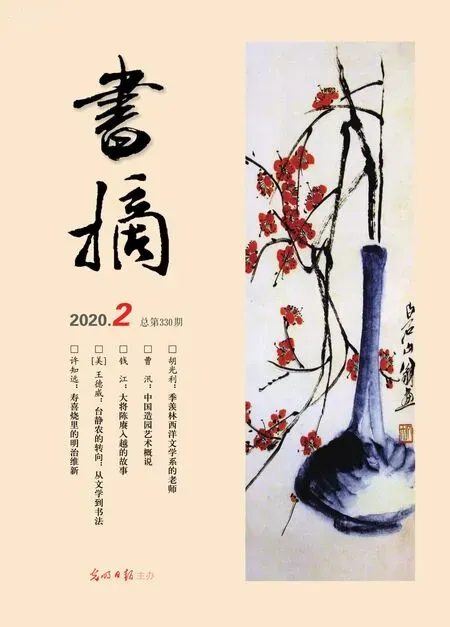夜晚的上海:古老“商業帝國”的韌性
☉鬼虎子
上海的韌性,一定要從它的歷史說起。
上海,簡稱“滬”,別稱“申”。大約在六千年前,現在的上海西部已成為陸地,東部地區成為陸地也有兩千年之久。相傳春秋戰國時期,上海曾經是楚國春申君黃歇的封邑,故上海別稱為“申”。
公元前223年,秦滅楚之后設立會稽郡,治所在蘇州。會稽郡轄繆縣、由拳縣和海鹽縣。繆縣包括今嘉定、上海兩縣及青浦、松江兩縣大部分和市區部分地區。
公元四五世紀時的晉朝,松江(現名蘇州河)和濱海一帶的居民多以捕魚為生,他們創造了一種竹編的捕魚工具叫“扈”,又因為當時江流入海處稱“瀆”,因此,松江下游一帶被稱為“扈瀆”,以后又改“扈”為“滬”。故稱上海為“滬”。
而上海真正建城又要等到近一千年之后了。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正式建“上海縣”,這是上海建城的開始。到了明代,上海地區商肆酒樓林立,成為遠近聞名的“東南名邑”。明末清初的時候,上海的行政區又進行了沿革,逐步形成了今天上海的規模。
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夕,上海縣東至川沙,南鄰南匯,西接青浦,北連寶山,已經頗具規模了,儼然一副大郡的樣子。這個時候的上海縣城里,有街巷63條,商店林立,鮮萃羽集,被稱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
但是上海進入現代城市的發展模式,還要從開埠說起。
鴉片戰爭失敗之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條約第三款規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清道光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
接著,英國又以“理定善后事宜”為借口,于1843年10月8日又同清政府簽訂了《虎門條約》。條約第九款規定:“在萬年和約(指《南京條約》)內言明,允許英人攜帶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但中華地方官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擬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和基地,系準英國人租賃。”
同年11月8日,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到任。他根據《虎門條約》向上海道臺宮慕久要求劃出一塊土地作“居留地”,專供英國僑民使用。宮慕久居然以為華洋分居能避免“糾紛”,默許巴富爾的要求。
巴富爾在11月14日發出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開埠。
在上海被迫開埠后的一百多年里,列強紛紛侵入上海,他們在上海競相設立租界。先是英國于1845年在上海建立租界,接著,美國和法國也分別于1848年到1849年間在上海建立租界。后來英美租界合稱為“公共租界”。從此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上海成了名副其實的“冒險家的樂園”。
那個時候國家積弱,租界成為海外列強蠶食中國利益的先遣陣地,最多的時候,全國一共有26 個租界,其中上海占了3個。“但上海租界的面積,是全國其他23 個租界面積總和的1.5 倍,上海租界設立最早,其他地方的租界,都是把上海租界制度搬過去的。”
租界的成立從另一個方面帶動了周邊經濟,把世界上最先進的商業模式帶來上海,給上海的服務業、金融業、商業還有市政建設打下了基礎。
最初設立的五個通商口岸(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上海居末席,為什么上海能成為五口岸當中最成功的呢?
廣州是最早接觸外國人的通商口岸,但是因為鴉片的傾銷,廣州人對外國人非常排斥。1843年開埠以后,外國人在十三行租了一些地方賣貨,而廣州人“一次又一次地扔石頭打他們”,一直反對了十幾年。后來外國人只好把廣州的租界設在沙面,也就是珠江上的一個小島,只有一條路通到岸上。如果您現在去沙面旅行,依然能看到很多歐洲風格的建筑。但是在近代史上,廣州沙面租界沒有多大的影響力。

英國人要求開福州為商埠,最重要的原因是看中了武夷山紅茶。但是閩浙總督劉韻珂設法把所有茶葉產地通到福州的路口全部堵死,不許茶商經過。英國人從福州想買茶葉做生意,但沒有人賣給他們。福州開埠以后,差不多有十年時間沒有多少生意。外國人不知道這些內幕情況,只是看到福州通商以后生意很不好。
另外兩個通商口岸,廈門租界設在鼓浪嶼,人氣不旺;寧波距上海太近,資源和人力最終流向上海。
而上海自宋元開始就有經商傳統,有獨特的韌性。
外國商人來了以后,上海人覺得跟外國商人做生意和跟外地商人做生意是一回事。優越的地位、廣大的腹地、深厚的人文傳統這三方面決定了上海是溝通外部世界最好的地方。
從那個時候就可以看出,相比較廣州的革命性、福州的官僚性、廈門的狹隘性、寧波的重復性,最終取勝的是上海的韌性。上海的韌性直到今天都是它商業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支持它在一次又一次的轉型過程中屹立不倒的法寶。
今天上海已經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也是國際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現在的上海是可以跟紐約、東京平起平坐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它既面向世界,又服務全國,帶動了整個“長三角”。
你很難想象,就這樣一個土地面積僅占全國0.06%,人口僅占全國1%的城市,每年完成的財政收入占全國的1/8,港口貨物吞吐量占全國的1/10,口岸進出口商品總額占全國的1/4。
同樣,上海的文化也獨樹一幟,它的文明程度、投資環境、商業氛圍、人才密集度首屈一指,全國沒有一個城市可以與其比擬,就算北京挾首都的威風也難以與上海抗衡。
特別是2016年,在世界經濟震蕩加劇,復蘇乏力,發達經濟體總需求低迷,長期潛在增長率下降,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體下滑,整個世界經濟非常脆弱,隱患頗多的時候,上海經濟依然堅挺。這一年上海消費品市場運行總體保持平穩增長,商業轉型升級穩步推進,新興業態快速發展,消費結構不斷優化。1月至11月,上海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964.87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8%。

而2017年也是多事之秋,英國脫歐、美國總統更替、意大利公投、法國總統選舉等持續沖擊,世界經濟進入波動加劇和不確定性升高的新階段。但是,上海經濟依然繼續保持穩健,經濟回暖初露尖角。
談完上海的歷史和現在,接下來可以談談上海的夜間經濟了。“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升平。”這首老歌從70年前一直傳唱至今,夜上海的歌舞升平、燈紅酒綠,是那個時代人們縱情狂歡、享受生活的標志。到了今天你會發現,這首歌中傳唱的上海仍然還在。
作為全球人都知道的國際大都市,“魔都”上海的一大“魔性”就在于,它豐富多彩的夜生活總是令人著迷淪陷,讓人無法拒絕。每當夕陽西下,華燈初上,各種欲望與瘋狂便開始蠢蠢欲動,讓這座城市展現出突破想象力的精彩。逛街的魅力、購物的沖動、美食的誘惑,一并在夜上海的各個角落上演著。
晚上的上海從來都是比白天更光彩奪目,那些白天腳步匆匆、轉戰職場的白領,到了夜晚,搖身一變,化身紅男綠女,融入滾滾紅塵。
上海到了晚上10點后仍在營業的店鋪超過了5600家,以上海2400萬的人口計算,也就是說,基本不到5000 人就會有一家“夜店”存在。這樣的人口覆蓋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國家規定的中小學配比標準了。
而上海市政府也在有計劃地推動夜間經濟的發展,軌交線路“加時運營”的提議,讓嗅覺敏銳的商家首先感到其中蘊藏的商機。在他們看來,周末軌交運營時長增加1小時,將為商業帶來可期的利潤增長。

說到上海的消費市場,就不能不談到上海從下至上的商業發展,從中能夠清晰地看出上海本地商業的韌性。
毋庸置疑,上海的購物已經多方面的全球化了,對高端品牌消費者和海外游客來說,在具有“上海第五大道”之稱的南京路上看到路易威登和古馳這樣全球一線奢侈品店,或者在位于金融中心的歷史悠久的外灘看到艾米里歐·普奇,毫不驚訝。影響上海經濟的主要是三個因素:全球化、外來人口和政策。
全球化對當地商業的影響不是從20 世紀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境外市場開放才開始的,而應該追溯至20 世紀20年代上海首次以國際大都市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的時候。
那個年代的發展反映了自1842年以來,上海作為英法兩國“通商口岸”的商業地位。殖民者在市中心和外灘的英、法、美租界建起了歐洲風格的商店、餐館、劇院和酒吧,為上海成為魅力都市奠定了基調。這些商業基地,雖然隸屬于殖民者,卻讓上海絢麗奪目。
外來人口一直是上海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上海居民人數從1842年的20 萬人,增長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的約五百萬人,到今天,上海已經有大約兩千四百萬的人口。涌進上海追求美好生活的外來人口,除了去工廠工作,很多人都被開店的機會吸引,做起了小飯店、小商店等服務類生意。
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本地商店發展了基礎商業設施,上海就難以容納如此大流量的外來人口。上海經濟生態系統的韌性,主要來自它“從下至上”的商業發展模式。
政府的政策一直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跟世界上其他大都市不同,在上海,來自政府層面的整體規劃一直都沒有停止過。上海作為體量巨大的經濟體,如果完全依靠野蠻生長,也許可以形成小規模的生態環境,但是在整體性上一定會呈現亂七八糟的感覺。今天上海的井井有條是離不開宏觀規劃的。
近年來上海市政府的舉措,是推出四至五個能體現上海飲食文化、民俗風情且滿足海內外游客多元消費需求的“地標型夜市”,形態有特色街、餐飲積聚型夜市廣場和商旅文體融合型夜市三大類。新天地和豫園、彭浦夜市和周浦夜市、七寶萬科和大寧寶燕商城分別為上述三種夜市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