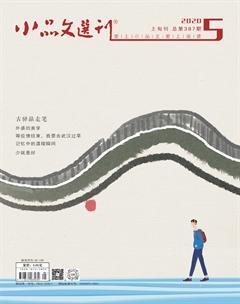蕎麥
賈哲慧
蕎麥播撒在西貝山村的東坡,早上醒來,男人提著褲子,女人端著尿盆上茅廁的時候,一眼就望見了那一道一道顏色,蕎麥花開,家家戶戶的炊煙開始升騰起充滿脂氣的薰味來。
就在幾個月前,地里還是滿目金黃的小麥呢。小麥收割不久,人們便撒上了蕎麥。其實,在農民的心里,蕎麥算不上一年的主口糧,但祖上說了:“有糧沒糧,存蕎麥幾擔。”祖上還說了,光緒三年,是蕎麥延續了西貝山村的煙火。
蕎麥生長期短,沒有屬于自己的領地,只能借著小麥的田開自家的花,結自家的籽。東坡是生產隊的小麥良田,金黃色澤剛從地里抹去,生產隊長便猴急猴急地帶領村民燒草木灰。人們將灌木、荊棘、蒿草堆成山峰,將田土覆在上面,一把火點了,黃土便燒得像又焦又坨的糞便,然后再擔幾擔茅糞和在一起,土肥得能將蕎麥烘出半人高。
這是一年當中村野最具詩意的季節,田地谷黍垂穗、豆莢綴串、瓜薯拖蔓;園里蔬菜蔥蘢、葵花俯首、鮮果飄香。一年一度,秋色最滋養山里人的日子。不曾想,蕎麥偏偏自信地開了,東坡的蕎麥花像霞,一道道白,一道道粉,一道道絳,一道道紫,于是家家洞門開窗,蕎麥花淡淡的清香馭風蕩漾。
父親準備將圪塔院的窯洞鏟平換成磚瓦房。先是雇人制坯,再是請人燒磚。燒磚師傅是母親的遠房親戚,我叫表舅,他挺拔俊朗,多才多藝,譬如畫畫、編籃、織席……沒有不會的。燒磚的日子,由于不能歇火,我與表舅作伴睡燒磚窯,燒磚窯在東坡。
村里的姑娘結伴兒來磚窯頂貼面餅,白面和糖。窯頂有幾百度的高溫,可以當鏊子用,貼出來的餅帶著別有的土香。蕎花跟著她娘也來了,蕎花走的時候,不僅給我和表舅留下了幾張香甜的面餅,還有脆生生的笑聲,那一夜,表舅的火添得很不專心。
蕎花再次來的時候手里提的不是盛面的箢子,而是一臺收音機。那時候農村有一臺收音機是不尋常的,蕎花家有,蕎花娘喜歡聽收音機,自留地干活的時候也攜帶著,趕巧蕎花娘的收音機壞了,她一刻也離不開它,聽說表舅會修收音機,便打發蕎花來找表舅幫忙。那晚,表舅領著蕎花去蕎麥地看月亮。其實表舅并不知道,蕎花爹先前不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漢,蕎花爹年輕的時候投機倒把,偷雞摸狗,后來便把蕎花娘給偷回來了。蕎花娘不像個村野姑娘,操著洋氣的口音,愛干凈,喜歡美,她的臉蛋不是太陽底下的紫紅,而是白白的嫩,嫩得能掐出水兒來。
蕎花娘喜歡西貝山村東坡里的蕎麥花,蕎花娘稀里糊涂跟著蕎花爹鉆進前不搭店后不挨村的西貝山村的時候,一眼就相中了那一梯梯五顏六色的油墨似的蕎麥。生蕎花的時候,恰巧東坡五彩繽紛的蕎麥花把蕎花家的窗戶映得滿屋生輝。蕎花爹問,娃她娘,給孩子起個名兒吧。蕎花娘說,就叫蕎花。這些村里人都知道,只是不知道蕎花娘是從哪里來的,其實不僅村里人不知道,蕎花也不知道,問娘,回答:你沒有姥姥姥爺,娘是從石頭縫兒里蹦出來的!
不像村里的女人剪齊耳短發,蕎花娘將頭發打成髻,然后插滿野花,蕎麥花開時節,更插成了花頭。有了蕎花后,蕎花娘便將這一喜好轉移到女兒的頭上。她不給蕎花綁小辮兒,而是松松地用手絹束一條馬尾,再別上綴滿野花的發卡,蕎花娘將蕎花扮成花兒一樣的姑娘,蕎花長得本來就出眾,有了這自信,蕎花打小兒性格就很開朗大方,漂亮的大眼睛看人很裸露。
燒磚窯前有棵核桃樹,白天沒啥事的時候,我便爬上樹捉蟬,摘核桃,或者干脆乘涼,我總能看見蕎花朝這邊兒偶不時地張望。表舅便對著蕎花的院子唱山歌,表舅的山歌不知從哪里學來的,從心底發出的聲音充滿磁性,蕎花情不自禁被一步一步吸來了。蕎花朝著表舅格格笑,笑完了就讓表舅教她唱山歌。這個時段,蕎花爹娘保準到地里上工了,否則,一定不準許蕎花靠近表舅半步。表舅托人給蕎花提親,蕎花爹說:“我家就一個閨女,招親行,娶不行!”蕎花爹知道蕎花喜歡表舅,盯得很緊。
蕎花來的時候,表舅便支使我靠在核桃樹叉上觀察蕎花家院子的動靜,蕎花娘看不到蕎花,便對著東坡使勁喊,喊完了就罵。蕎花和表舅從蕎麥地里慌慌張張爬出來,蕎花的頭發掛滿了零亂的蕎麥花,小臉白少紅多,似乎被蕎麥花浸染過。
后來,村里人開始有了閑話,蕎花并不顧忌,一往情深地同表舅廝守一起,蕎麥爹娘怕女兒做了與他們年輕時一樣不光彩的事,便逼女兒與表舅斷絕交往,蕎花不肯,與家里鬧將起來。那天蕎花爹將蕎麥打了,收工回來,蕎花已直挺挺躺在地上,刺鼻的農藥味道充斥著屋子。蕎花在蕎花娘搶天呼地的慟哭中被抬到公社醫院去了。后來,康復后的蕎花直接被爹送到山外的親戚家療養去了,其實是讓她斷了與表舅相好的念想。
表舅盡管憤恨蕎花爹娘的作梗,但出了這么大的亂子也覺得后怕,且對我父母也懷有歉疚,于是燒完磚便落寞地離開了。表舅走的時候,蕎麥花落已久,曾經浮在那里的繽紛色彩仿佛只是一場短暫的夢。
表舅走后,蕎花從親戚家回來了。蓬松的馬尾巴剪掉了,變成了時髦短發,口音也變了,穿戴打扮像個城里姑娘。蕎花一掃曾經的陰霾,臉豐腴了,變得妖冶了,比年輕時的娘還勝過不知多少倍。
后來,西貝山村腳下的鄉鎮煤礦紅火起來,蕎花爹給蕎花在礦上找了個充礦燈的工作,來礦上拉煤的年輕司機很多,漸漸地,蕎花跟某中一位廝混在一起。小伙長得挺利索,年紀雖然不比蕎花大多少,但已有了家室。蕎花爹唯恐再生事端,便讓蕎花辭工回家。回家后的蕎花并沒與司機了斷情緣,一個風清月明的深夜,與司機在村里蕎麥草垛下行云雨事的時候被村民捉了奸。被困于家中的蕎花最終還是從爹娘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蕎麥娘將新做的兩只銹著鴛鴦的蕎麥枕頭扔進火里。
西貝山村的風俗:人死送葬時家人將死人生前的枕頭焚燒,以示永訣。
選自《遼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