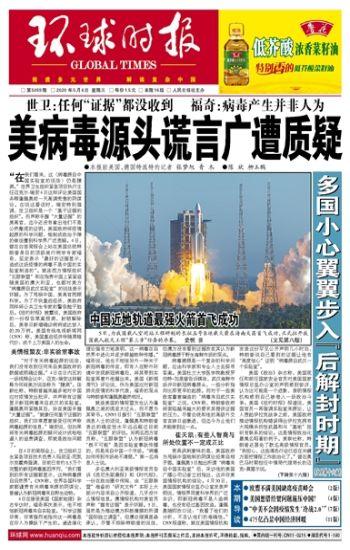疫情后,各國“整軍備戰”會加劇嗎(觀察家)
李巖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日前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軍費開支呈現10年來最大增幅,世界各國軍費總支出超過1.9萬億美元,創下冷戰結束以來新高。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對全世界和人類社會產生深刻影響,這場疫情會否改變國際社會的這種“整軍備戰”傾向和軍備競賽沖動,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過去十余年全球軍費開支保持總體上升態勢,存在兩個基本邏輯。一個邏輯是國家之間的傳統安全競爭不斷加劇,逐漸主導了國際安全形勢的演變。冷戰結束之后,國家之間的安全競爭并未大幅消退,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例如氣候變化、核安全、網絡安全、恐怖主義等,雖然成為新的安全關切,但顯然無法主導國際安全態勢。
2001年“9·11”事件對國際安全態勢的影響,也很快隨著美國對外戰略的轉向而讓位于傳統安全競爭。小布什政府“先發制人”的黷武傾向、奧巴馬政府推動“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布局、本屆美國政府上臺后以“大國競爭”為牽引的安全戰略,加之各類資源之爭、發展空間之爭引發的安全熱點與軍事沖突,牽引了國際安全形勢的演變,塑造了各國聚焦傳統安全的戰略取向。在這種背景下,基于確保國家生存的基本起點,“整軍備戰”成為各國戰略設計的基本傾向。
另一個邏輯是主要國家經濟的總體增長態勢,為軍費投入提供了基本財政支撐。以美國為例,“9·11”事件重新刺激了美國在國防領域的全面再投入,這是建立在“互聯網繁榮”時代經濟積累基礎之上;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十年經濟復蘇和增長,保證了這一時期美國軍費的不斷攀升。其他主要國家也大體如此。現代軍備研發部署所需要的巨大資源,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撐很難長期持續。
這次疫情會如何影響“整軍備戰”,也可以從這兩個邏輯的潛在變化中進行觀察。首先,疫情可能會加劇國家間的競爭局面,強化各國“整軍備戰”需求。面對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這一“看不見的敵人”,因為少數西方國家“甩鍋”和推卸責任之舉,國際社會基于共同利益進行政策協調、相互協助的局面并未及時出現,國際組織也因某些大國的自私之舉而無法發揮應有作用。更令人憂慮的是,疫情充分暴露了各國發展模式、治理方式、戰略思維、基本國情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與近年來不斷發酵的民族主義、民粹思潮相互疊加,對國際社會的疫情防控、乃至整個國際運行體系構成了重大沖擊。
同時,盡管疫情的潛在影響尚未全面展現,但由此催化的“百年變局”成為國際戰略界較為普遍的認識,圍繞資源、產業鏈、發展空間、地緣等的爭奪大概率會更為激烈。基辛格認為,疫情將永久性地改變現有國際體系、力量平衡和世界秩序,人類歷史將分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從目前各國圍繞疫情防控的互動情況看,國家間競爭加劇很可能成為“2020年之后”世界的底色之一。因此,從國家間競爭的邏輯看,疫情將更加凸顯各國對于生存問題的關注,可能加劇各國“整軍備戰”的既有趨勢。
其次,疫情導致的經濟蕭條,又可能極大制約各國在軍事領域的投入。目前看來,疫情大概率會引發普遍性的經濟衰退,甚至會引發新的持續多年的“大蕭條”,相關影響將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這一局面將極大破壞各國保持軍事投入的財政基礎。同時,各國面臨愈發嚴重的財政窘迫局面,也將不得不重新權衡軍事與非軍事領域的財政投入,重新評估“國家安全”的定義,引發對于傳統安全競爭主導國際安全態勢之利弊的新思考。就此而言,這次疫情可能有助于各國重新衡量軍費投入的成效、費效比問題,迫使各國克制“整軍備戰”沖動。
基于上述分析,這次疫情對于“整軍備戰”傾向的潛在影響目前尚難定論。安全需求的進一步上升,伴隨財政支撐的極大弱化,將使各國決策者面臨全新挑戰。
疫情對“整軍備戰”的影響,更應置于國際安全的宏觀視角、國際體系的長期變化之下進行觀察。“天下大勢,治亂相替而已”。疫情引發的國際體系“大亂”能否走向新的人類社會“大治”,這一問題根本上仍然取決于各國的戰略選擇。最近幾年,我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使之成為中國的外交理念;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思想,系統闡述11種安全,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發展和安全。當前全球仍處于抗疫的艱難時刻,人類面臨新的存亡與興衰考驗。“人類命運共同體”“總體國家安全觀”等中國理念的啟示意義更加凸顯,理應對各國安全思維產生觸動,從而在根本上解決“整軍備戰”及其帶來的負面效應。▲
(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