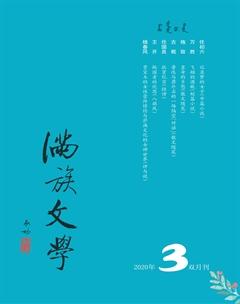叛國者的憂思
〔滿族〕王開
1
祖大壽是寧遠沉甸甸的分量,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他永遠經得起推敲,并且歲月越久,越能反射出耀眼光焰。或者說,讀透了祖大壽,你就讀透了遼西明清戰爭文化中的精彩篇章。祖大壽,不同于袁崇煥的千古奇冤,也不同于吳三桂蛟龍困于泥潭的掙扎,對他來說,叛國投敵的罪名太重,也不該由他一個人承擔。
本來,祖大壽是一位明清戰爭中的豪杰,但命運把他卷入《二臣轉》,抹殺了他的功績。二臣就是漢奸,男人最怕這兩個字摜在頭上,一旦摜上,自己及子孫的名譽都搭進去了,幾輩子不得翻身。漢奸這個詞大概出現于明末,最初含義并沒有這么尖銳,泛指有人心懷叵測、撥弄是非、造成社會不穩。到了晚清以后,漢奸的內涵發生嬗變,這個群體介于內外、敵我之間,認賊作父,為國家和民族所不容。若以這個定義來衡量祖大壽,顯然,他應排除在這個罪名之外。
祖大壽是土生土長的寧遠人,祖宗兒孫,親朋好友,同僚士卒,全在這塊土地上。祖氏一族,骨子里傳承著尚武精神。晉朝時,其遠祖任鎮西將軍,明初祖氏一族由滁州遷至遼陽,宣德五年(1430)再遷寧遠衛,之后,祖氏族中,有人歷任百戶、千戶、指揮僉事、指揮同知。較之先人們,祖大壽的父親祖承訓軍旅生涯波瀾壯闊,他參加過援朝抗倭戰爭,聲名也在抗倭戰爭中得以傳世。
祖大壽性格的形成,源自祖氏的一脈相承。祖大壽系祖承訓長子,字復宇,據說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祖大壽青年時代在廣寧軍中供事,受巡撫王化貞賞識,升為游擊。天啟二年(1622),后金突襲廣寧,王化貞雖組織抵抗,怎奈技不如人,將廣寧拱手相讓,祖大壽遂率部分遼兵撤駐覺華島。薊遼督師割韭菜似的換了兩茬,老臣孫承宗出關,與袁崇煥一起守遼。大壽就在關鍵時刻被重用,協助袁督師修筑寧遠城。
明天啟六年(1626)即清天命十一年正月,努爾哈赤來攻寧遠,祖大壽堅守城南,兼顧城東。激戰中,祖大壽指揮守軍積極防御,后金在城南與城東均未實現突破。第一次寧遠之戰宣告結束,祖大壽作戰有功,受朝廷封職獎賞。他和袁督師也在連天炮火中結下兄弟情誼。
2
我以為,寧遠最具魅力的不在溫泉,不在海浴,亦不在花花綠綠的泳裝產業。誠然,這些支撐了一座城市的GDP,讓城市風風光光。但若看看新磚老磚咬合的方城,看看延琿街的兩架牌坊,你方才覺悟,它們才是寧遠的精神內核。那兩架牌坊完全屬于明代,建筑背景、材質、雕工等等,均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和藝術特色。牌坊的另一番意義還在于,它們極力夸耀的兩個忠臣——祖大壽和祖大樂兄弟,后來都背叛了國家。但這樣的背叛,我們不該報以任何憎恨和鄙夷的態度,尤其祖大壽降清給我的悲涼況味,愈近寧遠時,愈發刻骨。甚至,我對祖大壽的叛國行為,持有敬重之心。
兩架牌坊中的一座,專為祖大壽所立,贊揚他效忠朝廷,鎮守邊疆,掃平戰亂的功績。如果仔細觀察,額枋邊柱刻著有趣活潑的一個人戎裝騎馬出征的浮雕,馬兒四肢粗壯而短,體現了明代動物雕刻的風格,最讓人浮想聯翩的是,誰全副武裝,欲馬上征戰?工匠通過畫面告訴你,此人乃祖將軍,他正為保衛遼西走廊奮勇戰場。
沉寂一年的皇太極卷土重來,直撲錦州,勢頭之猛烈甚于其父汗。袁督師兵力有限,考慮再三,派祖大壽、滿桂、尤世祿飛馳錦州。祖大壽等與錦州城內守軍里應外合,皇太極啃不動第一打擊目標,揮師轉攻寧遠。
祖大壽作為袁督師的干將,又一次與皇太極面對面交鋒,他和滿桂、尤世祿三人同心,力阻皇太極于寧遠城外。皇太極屢屢發動攻勢,祖大壽像根釘子,拔不掉,砸不彎,袁督師借機狂發炮彈,與皇太極互相炮擊。一時間,攻方與守方僵持,互不相讓。精明的皇太極料定這一仗仍難獲勝,以天熱為由撤退。
再戰寧錦不下,皇太極心焦惱火。而在明朝廷,卻于渺茫中看到一線希望,權貴們情緒熱烈,點數著誰該記功,記幾等功,數來數去,竟千人余。這么多有功之臣,連總指揮袁督師都排不上號,僅象征性地頒發一點物資獎賞了事,祖大壽自然也撈不到太多好。我據此相信,祖大壽出生入死,親歷戰陣,他一定對這次的功勛分配心懷不滿,為自己,為督師,為參戰遼軍鳴不平。
他若沒有思想波動,就不是血肉之軀,也不符合祖氏一門幾輩武將的特性——他們忠君愛國,也痛恨那些打著忠君愛國幌子圖謀私利的小人。
更讓祖大壽喉頭哽咽的是,袁督師在勝利的鑼鼓聲中離職了。徜徉商業氣息濃郁的延琿街,有那么一刻,我看見祖大壽穿越四百年時光,現身牌坊下,日影將他的沮喪拉得老長老長,黯然送別袁督師。爾后,他揮鞭打馬離去,頭也不回。
英雄的寧遠彌漫著失望情緒,祖大壽悲觀、落寞。但他不能放棄這座城,祖氏的傳統不允,袁督師行前也有囑托。還有,他的妻子兒女部屬親朋財產都在這兒,他必須頂住壓力,誓與城共存亡。
祖大壽在抑郁中守著寧遠,這期間,皇太極曾借給天啟帝吊喪,致書祖大壽,表達議和意愿。祖大壽看完信,一字未復。他也沒有意識到,隨著天啟皇帝的死,崇禎皇帝繼位,他和袁督師、皇太極之間重續了糾結關系。
我有一百種理由相信,祖大壽聽說袁督師再度啟用,擔任薊遼督師的消息時的振奮。他也為崇禎對袁督師說的那句“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話而歡欣,這讓他深切感受到朝廷對袁督師的倚重,袁督師地位高了,意味著祖大壽等猛將有了軸心,收復失地指日可待。
祖大壽的預計沒有錯,袁督師重返寧遠,祖大壽受封前鋒總兵,駐守錦州。此舉等于讓他站在抗擊滿洲的最前沿,替寧遠、山海關、乃至北京抵擋皇太極射來的當胸一箭,這是袁督師對祖大壽莫大的信任。
皇太極再攻前夕,打的還是投石問路的牌。史書說,他先后給袁督師發了六封議和信,試圖和平談判。不過,這一次皇太極判斷失誤,問題在于,袁督師已立下五年復遼誓約,豈能引滿朝文武恥笑,招致殺身之禍?而皇太極也從袁督師辣手整頓軍紀,斬殺毛文龍等果斷行為,看出議和是萬萬不能的。遂率領大軍,繞過關寧錦防線,取道蒙古,破邊墻入塞,殺奔崇禎的北京。
3
說不清為什么,寧遠的水文化與戰爭文化割裂開來,寧遠人向外來客介紹他們的溫泉,他們的海,以及那座古老的城,都是各講各的,好像它們之間沒有內在聯系。但那個大雨天,我乘車奔馳在寧遠的新城老城,在風雨渤海的岸邊駐足觀潮,心中想到最多的是,終年生活在這片海洋和陸地上的人就像一種兩棲動物,他可以騎著馬呼喝來去,也有閑暇漫步海岸,陶醉海風的吹拂,想著無限心思。我覺著,祖大壽和袁督師的生活中,一定有這樣的片段。極可能他們某一個靈感或成熟的思路,就從一次看似悠閑的散步中獲得。比如,袁督師寫給朝廷的奏疏。
袁督師說,臣在寧遠,敵人越關西進的算盤必不得逞;臣憂薊門薄弱,恐敵人鉆了空子,宜宿重兵把守。
觀此言,袁督師可謂苦口婆心,只是,崇禎和朝廷官員們終日忙碌,沒工夫搭理督師,結果不幸言中。
即便袁督師早有預測,一旦變成事實,也險些讓他亂了方寸。史書這樣記載道:
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十月二十九日,薊遼督師袁崇煥由寧遠往山海關,行至中后所,得報八旗軍團破大安口,立即部署趙率教點四千兵馬,弛救遵化。
三十日,皇太極抵遵化。袁督師緊急抽調祖大壽,隨其入京。
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崇禎于慌亂之中,諭選智略者御敵。這時,袁督師和祖大壽等正渾身汗水,策馬狂奔京師。
初四日,皇太極攻陷遵化。
初十日,袁崇煥得崇禎諭旨:“調度各鎮援兵,相機進止。”被迫調整防御部署。
十五日,袁崇煥和祖大壽抵河西,商議進京師援救。奈何崇禎下令,不準袁督師越薊州。
我們后來人都明白,事到此時,崇禎已被流言蜚語蒙心,不再信任袁督師。可憐袁督師置身其中,一心保衛圣駕,渾然不覺圣上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十七日,袁督師率祖大壽到達京師廣渠門外,忍著饑渴寒風,露宿扎營。
二十日,皇太極率八旗鐵騎滾滾而來。京師腳下,狼煙四起;京城之內,人心惶惶。遭遇勁敵,督師和祖大壽只有一個念頭:拼死抵抗,絕不能退半步。兩軍對峙,萬籟俱寂。不知過了多久,馬蹄聲、號角聲、喊殺聲,驟然響起,雙方人馬攪成一團,刀來劍往,難分彼此。那一天,在多爾袞三兄弟為首的左翼八旗旋風似攻擊下,袁督師與祖大壽背抵城墻,血濺薊門。目睹這場惡戰的朝鮮使臣向他的李氏國王如是描述:“賊直到沙窩門,袁軍門、祖總兵等自午至酉,鏖戰十數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賊退奔三十里。賊之不得攻陷京城者,蓋因兩將力戰之功也。”
然而,袁督師的拳拳報國心卻被閹黨流言所害。忠君與愛國,原不可混為一談。
祖大壽親眼看著督師被捕,驚得丟了三魂七魄。他悲傷、恐懼,憤然與何可剛總兵率遼軍離京出關。
誰能想到祖大壽離京時的表情?他必定咬著牙,青著臉,回望北京巍峨的城墻,狠狠地罵一句,策馬奔回遼西。
祖大壽一聲招呼不打,帶著人馬走了。接下來驚呆恐懼的是老臣孫承宗,他明白老部下為什么突然撤走,更擔憂祖大壽一走,京師怕是無人能保。
焦急萬分的孫承宗派人帶上自己和袁督師的手書,急切切追趕祖大壽。
祖大壽手捧督師親筆書信,義憤填胸,傷心哭訴。為解救袁督師,祖大壽披肝瀝膽:“京師城門口大戰堵截,人所共見,反將督師拿問。有功的人不蒙升賞,陣亡的人暴露無棺,傷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收復遵化,皇上哪知我們的功勞?既然說遼人是奸細,今且回去,讓他們廝殺!”
祖大壽一字一句,動容動情,遼軍一片嗚咽。那哭聲如海潮滾滾,隔著數百年時光,傳達我的耳畔。當時,我站在祖氏兄弟牌坊下,辨認著額枋上刻的 “廓清之烈”四個大字。
掃清夷患,忠貞者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可祖大壽哭也好,罵也好,卻不相信他們誓死捍衛的朝廷已無法理可講,亦不念人情道德。朝廷的所作所為,只是叫他傷感,他說出這番話,唯希望朝廷理解袁督師,理解為國守土的遼軍將士。他還幻想,憑著遼軍勞苦功高,拯救身陷牢獄的袁督師。而這正是祖大壽的可愛之處,讓我對一個叛將懷景仰之情,一走近他的紀念建筑,心底肅然起敬。
4
后來發生的讓我們知道,祖大壽的忠義并未感動崇禎,盡管他回師入關,在孫閣老領導下一口氣收復永平、灤州、遷安、遵化四城,崇禎仍然殺了袁督師。
由于史籍的疏漏,我們無法知悉袁督師死訊傳到祖大壽那里時,他是什么樣的心情。我覺著,祖大壽的第一反應,唯有慘然一笑。笑得天地千古寒。
皇太極計殺袁督師成功,也未必得意。一個沒有對手的人,會心生失落感。因此,他不想祖大壽重蹈覆轍。
在皇太極眼里,祖大壽不獨他一人,而是寧遠錦州乃至遼西走廊四百里的核心,他就是遼西的一桿大旗,有他在,遼西人的精神意志猶存,軍事防線就不會垮。反之,招降了祖大壽,意味著大明的寧錦防線全部垮塌。而對付大祖壽最有效的辦法是圍,困住這只虎,挫他的銳氣,磨他的勇氣,消解他的斗志。
崇禎三年(1630)即天聰四年七月,皇太極來了,困祖大壽于大凌河城。
彼時的大凌河城,包括祖大壽在內,副將八人,參將游擊約二十人,騎兵七千,步兵七千,夫役商賈約萬余人。祖大壽幾次突圍,均被皇太極逼回城內。山海關、寧遠、錦州方面的援兵也被八旗兵打得落花流水。內外阻隔的祖大壽,很快嘗到坐困的滋味。
皇太極拿捏著分寸,展開勸降手段。祖大壽仍采取置之不理的老辦法。皇太極不急不惱,端坐城外和祖大壽耗著。
大凌河告急,監軍道張春和吳襄統兵四萬,由寧遠飛馳來救。這一仗,以援軍覆滅、監軍道張春一干人等投降告終。十月底,張春為首的二十三名降將分別寫信勸降祖大壽,祖大壽毫無所動。皇太極的親筆招降信也打了水漂,激不起絲毫漣漪。
大凌河城內斷糧斷炊,人吃人的慘劇天天上演。
若保衛人民到自相殘殺的地步,保衛之意義何在?被保衛的人民為了活命,還原野獸本性,保衛者焉能不脊背生寒?祖大壽智慧,如何參不透這玄機,只好開城投降。但何可剛骨頭硬,死于八旗軍亂刀之下。餓瘋了的大凌河人沖上去,分食了他——一想到何可剛,我總為他悲切,他從寧遠轉戰錦州,錦州轉戰京畿,京畿戰到灤州永平,又從錦州戰到大凌河,結果和袁督師一樣,為人民而死,人民待他卻比豺狼還狠。我覺著,寧遠城該樹一座碑,悼念他的功績,瞻仰他的氣節,而不應只是在紙頁里看到短短幾行記述。
祖大壽降了,皇太極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一股腦贈送他,他的兄弟子侄副將統統厚待。可祖大壽的心里,只有他的國家、他的城、他的人民,他誆騙皇太極說,請放他到錦州,然后里應外合,占領錦州城。這貓三狗四的伎倆,由祖大壽使出來,有點兒詼諧,也隱著凜凜的成分。話說回來,祖大壽這般的效忠,于一個患上敗血癥的朝廷,無非讓它多遭幾天罪,歷史多了一段故事可講。另一方的皇太極呢,有意無意著了祖大壽的道兒,成全了祖大壽的計策。祖大壽一入錦州,再無音訊。滿洲高層異常惱火,集議殺掉祖大壽家人部將,因為自明清開戰以來,還沒有哪個降將敢開這么大的玩笑戲耍大清。面對祖大壽的去而不返,皇太極的做法則高明得多,他大度包容,采取政治攻勢和人情攻勢,加倍善待祖大壽的親人將官,希望感化他。
這些事情,錦州城里的大壽盡收眼底,但皇太極始終沒撼動他的心。接下來的七年間,祖大壽一直與皇太極為敵,兩人曾在中后所,也就是今天的綏中相遇過,皇太極再次勸他投降,祖大壽不理睬。后多爾袞統帥攻明,崇禎急調祖大壽入援。崇禎十二年(1639)十二月,清軍攻占濟南,祖大壽又往,直到三月才完成使命,奉詔返回寧遠。不久,祖大壽再次被派駐錦州,直到崇禎十四年(1641),皇太極再次來圍。
這一次,祖大壽自知難逃此劫了。他業已老邁,當年的少壯和慷慨激昂,都被時間退化成行動遲緩、須發飄然。但他不能脫下那身征袍,過去他是遼西的擎天一柱,到現在依舊主宰遼西人的精神世界,他必須戰斗到最后。
漫長的圍困開始了,皇太極表現出十足的耐心,氣定神閑地坐在城外,指揮兄弟子侄們輪番圍城。期間,皇太極輕松滅掉洪承疇十三萬援軍,洪軍門被押解盛京,不日降清。最有可能救錦州于水火的洪軍門投降了,明朝廷再無合適人選來挽救祖大壽,他只能靜候死神。
一年后,錦州城尸骨遍地,慘不忍睹,若再堅持下去,城亡人也亡。直到末路,祖大壽信念不改,倒是祖夫人不忍百姓無辜受死,苦勸祖大壽歸降。祖大壽走投無路,一聲嘆息,由部下抬他出城。而他走后,祖夫人悄悄上吊自殺。
祖大壽降清,不削弱他的英雄氣概。說到底,他不是敗在軍事行動上,而是敗于腐敗的朝廷。還有祖夫人,一個懂大節義的女人,讓我想起九一八事變時,遼寧省長臧式毅的母親,當臧式毅的老母親得知兒子降日,絕食三天,自盡而亡。
在寧遠的時候,我吃了太多的海鮮和遼西豆腐,也切身感受了寧遠溫泉與海的魅力,了解了溫泉與海給予寧遠無窮的發展潛力。但我特別想去祖家舊址祠堂或者墓地,拜祭祖大壽和祖夫人。可惜,祖家舊址無跡可循,祖家墓地在文革中遭毀,這也算祖大壽及夫人的又一個遺憾了。
〔特約責任編輯 李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