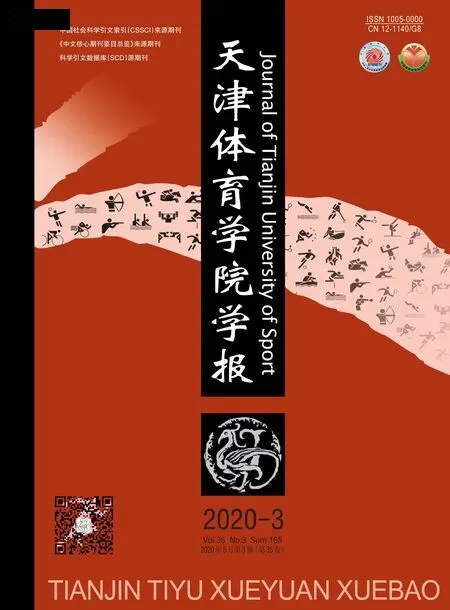自愿轉輪運動對慢性應激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前額葉皮質炎癥因子及NGF/TrkA信號通路的影響
崔建梅,王卓琳,郭燕蘭,李中華,于 芳,李洪濤,蘇曉云
精神疾病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研究認為,抑郁障礙和焦慮障礙是高度共病的,并且應激是2 種疾病的共同危險因素[1]。多數學者研究發現,外部應激因素(如應激生活事件)和內部應激因素(如慢性炎癥)可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功能的應激性改變,使大腦小膠質細胞產生促炎細胞因子[2],而促炎因子可通過影響神經回路和神經遞質引起抑郁樣行為,包括快感缺乏、睡眠變化和社交活動減少等[3]。并且R.KRISHNADAS等[4]發現,對傳統抗抑郁藥不起作用的抑郁癥患者可表現出一種獨特的促炎傾向。前額葉皮質與思維和行為調節密切相關,H.ANISMAN等[5]報道,應激會增加前額葉皮質促炎細胞因子水平(IL-1β、IL-18、TNF-α等),導致細胞增殖減少和神經發生障礙,與抑郁及焦慮行為發生有關。神經生長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在神經發生和突觸可塑性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并且腦內NGF 活性主要由其受體酪氨酸激酶A(TrkA)介導,對維持損傷神經元的結構,促進神經生長和修復具有重要作用[6]。通過臨床及動物實驗證實,NGF 與抑郁樣行為有關,已經被視為抗抑郁藥的作用靶點[7],但是通過NGF通路治療抑郁癥的機制尚不清楚。A.H.MILLER 等發現,促炎因子活性增加可能會通過降低NGF水平,從而改變神經發生和可塑性,最終導致抑郁[8],而給與抗抑郁藥NGF可通過影響大腦細胞炎癥因子活性改善抑郁癥狀[9]。因此可以認為,NGF/TrkA通路及神經炎癥因子可能在慢性應激誘導的抑郁及焦慮樣行為中發揮重要作用。
臨床試驗表明,體育鍛煉可以產生抗抑郁和抗焦慮作用[10],同樣在抑郁和焦慮樣行為的動物模型中也觀察到類似結果[11]。并且在臨床和嚙齒動物研究中均發現,運動可以通過調節某些神經遞質和神經營養素的表達改善抑郁模型大鼠抑郁及焦慮樣行為。有證據表明,運動誘導的NGF上調及炎癥反應減弱對海馬結構和功能的改變是重要的,在突觸功能和學習記憶方面起重要作用[12]。但是,運動改善慢性應激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是否與大腦前額葉皮質NGF通路及炎癥因子改變有關,相關文獻較少涉及。因此,本研究通過復制CUS抑郁模型,探討4周自愿轉輪運動對CUS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的影響,及確定這些影響是否與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PFC)炎癥因子(IL-6、TNF-a及抗炎因子IL-10)及NGF/TrkA通路有關。
1 材料和方法
1.1 動物及分組
44只雄性成年SD(Sprague-Dawley)大鼠(山西醫科大學實驗動物中心),重(200±20)g,被安置在室溫(22±2)℃、濕度50%±10%、12 h晝夜循環光照的動物飼養室,大鼠可自由攝食及飲水(除禁水、禁食期間)。大鼠購回適應飼養室環境1周后,所有大鼠被隨機分為4 組,即安靜對照組(control group,C)、運動組(exercise group,E)、應激模型組(CUS group)和應激運動組(CUS treaded with exercise group,CUS+E)。
CUS 組及CUS+E 組大鼠單獨喂養,其中,每組6 只大鼠用于前額葉皮質炎癥因子含量測試,其余每組5 只大鼠用于測量前額葉皮質NGF及TrkA表達。
1.2 CUS模型建立
適應實驗室環境1 周后,CUS 組及CUS+E 組大鼠根據H.ZHENG 等[13]采用的慢性不可預知應激方法制作大鼠抑郁模型。每周7 種應激刺激順序隨機安排,且每種刺激在每一輪中出現的次序不同(1 種應激/每天),連續刺激28 天,應激刺激見表1。

表1 大鼠慢性不可預知應激7種應激程序Table1 Stress Program of Chronic Unpredictable Restraint Stress
1.3 自愿轉輪運動方案
(1)CUS 組大鼠從第2 周(第8 天)開始,接受為期4 周的CUS。(2)CUS+E 及 E 組大鼠在整個實驗過程中從第 2 周開始接受自愿轉輪運動,籠內有1 個可自由轉動的跑輪(直徑33 cm,寬度10 cm),動物可自由進跑輪進行鍛煉,為期4 周,紅外線檢測裝置和數據分析系統自動采集數據,同時每天接受1 次CUS 程序。非應激模型組大鼠除必要的例行鼠籠清潔,不做任何干擾。
1.4 高架迷宮實驗(elevated plus maze,EPM)
第36天進行EPM實驗,評估嚙齒動物的焦慮水平,高架迷宮包括2 個開放臂和2 個閉合臂,中間有一平臺連接開放臂和閉合臂。自愿轉輪運動及應激程序結束后第2 天,所有大鼠接受EPM測試,大鼠被放置在迷宮中心平臺(面對開放臂)探索迷宮5 min,迷宮軟件記錄并分析大鼠的焦慮樣行為。
測試指標:開放臂時間(time spent in the open arm,OA),閉合臂時間(time spent in the closed arm,CA),進入開放臂次數(open arm entries,OE)及閉合臂次數(closed arm entries,CE)。統計指標:OA%=OA/(OA+CA);OE%/(OE+CE);焦慮指數:1-(OA%+OE/%),比值越大,表明大鼠的焦慮程度越嚴重。
1.5 開場實驗
EPM 結束后24 h(第37 天),所有大鼠進行開場實驗測試。開場實驗箱(1 m×1 m×0.5 m),底面用黑線分成25 個方格。將大鼠放在試驗箱中央,自由探索5 min,上方攝像頭記錄大鼠實驗箱內的行為學指標:跨格次數(以3 只腳爪進入1 個新格為準,次)、中央格時間(s)和糞便顆粒(顆)。為減少人為誤差,2人同時觀察并記錄每只大鼠實驗數據,取平均值。
1.6 前額葉皮質炎癥細胞因子水平測量
開場實驗測試結束后,即刻將每組6只大鼠斷頭取腦,冰生理鹽水沖洗干凈后迅速分離前額葉皮質稱重,并用生理鹽水按(1:9)的比例制成10%前額葉皮質組織勻漿,離心(12 000 rpm/min,10 min)后取上清液,采用ELISA(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法,參照試劑盒說明進行前額葉皮質炎癥因子IL-6、TNF-a水平和IL-10水平的測定。
1.7 大鼠前額葉皮質NGF及其受體TrkA免疫組化檢測
開場實驗測試結束后即刻對每組剩余5只大鼠經水合氯醛(10%,150 mg/kg)麻醉后,4%多聚甲醛溶液心臟灌注取腦,石蠟包埋腦組織,前額葉皮質經石蠟切片機連續冠狀切片(片厚5 μm),切片依次經梯度乙醇脫蠟、脫水后滴加30%H2O2室溫孵育30 min,PBS液漂洗3次后滴加兔抗大鼠NGF及TrkA單克隆抗體(1:200),4 ℃過夜,PBS液漂洗3次后滴加生物素化山羊抗小鼠NGF及TrkA二抗孵育(37 ℃、30 min),PBS液清洗后DAB室溫顯色10 min,蘇木素復染2~3 min,梯度乙醇脫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樹脂封片。
根據大鼠腦立體定位圖譜確定大鼠前額葉皮質位置(見圖1),用數碼顯微鏡拍片(每個切片在前額葉皮質同一區內取3個視野),應用江蘇捷達形態學分析系統對大鼠前額葉皮質NGF及TrkA 陽性神經元的表達進行分析,計數NGF 及其受體TrkA免疫陽性細胞數量及面積(μm2)。

圖1 大鼠腦立體定位圖Figure1 Stereotactic Image of Rat Brain
1.8 統計學處理
數據統計采用SPSS18.0 軟件,數據結果用M±SD表示,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學指標及前額葉皮質炎癥因子(TNF-a、IL-6、IL-10)和NGF及TrkA表達采用雙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差異比較采用LSD post hoc法,P<0.05為顯著性差異,P<0.01為極顯著性差異。
2 結 果
2.1 自愿轉輪運動對CUS大鼠焦慮樣行為的影響
雙因素方差分析顯示,慢性應激顯著影響大鼠高架迷宮實驗中開放臂次數、時間比例及焦慮指數(F(1,43)=9.830,P=0.003;F(1,43)=6.993,P=0.012;F(1,43)=6.502,P=0.015),而運動除顯著影響開放臂次數比例外(F(1,43)=5.543,P=0.024),對開放臂時間比例及焦慮指數均無顯著影響(F(1,43)=2.090,P=0.156;F(1,43)=2.266,P=0.140)。并且,運動和慢性應激對開放臂時間比例均有顯著交互效應(F(1,43)=5.152,P=0.029),對開放臂次數比例(F(1,43)=1.185,P=0.283)和焦慮指數(F(1,43)=0.533,P=0.470)均無顯著交互效應。
與C 組比較,CUS 組大鼠高架迷宮實驗中開放臂時間(P=0.042)及次數比例(P=0.005)均顯著下降,焦慮指數顯著增加(P=0.026);而經過4 周自愿轉輪運動,CUS 運動組大鼠與CUS組大鼠比較,開放臂時間(P=0.018)及次數比例(P=0.019)均顯著增加,但對焦慮指數無顯著影響(P=0.122);而與C組比較,運動組大鼠開放臂時間(P=0.996)、次數比例(P=0.376)和焦慮指數(P=0.376)均無顯著改變(見圖2)。
2.2 自愿轉輪運動對CUS大鼠抑郁樣行為的影響
雙因素方差分析顯示,慢性應激和自愿轉輪運動顯著影響了大鼠跨格次數(F(1,43)=21.671,P=0.000;F(1,43)=4.201,P=0.047)和糞便顆粒(F(1,43)=33.353,P=0.000;F(1,43)=4.464,P=0.041),而只有慢性應激影響了大鼠中央格時間(F(1,43)=6.855,P=0.012);并且,運動和慢性應激對糞便顆粒(F(1,43)=3.353,P=0.075)、中央格時間(F(1,43)=0.215,P=0.645)和跨格次數(F(1,43)=1.836,P=0.183)均無顯著交互效應。

圖2 各組大鼠高架迷宮實驗中開放臂時間比例(OA%)、開放臂次數比例(OE%)及焦慮指數結果比較。Figure2 Comparation of the OA%,OE%and Anxiety Index in EPT in Various Groups
與C 組比較,CUS 組大鼠開場實驗中跨格次數顯著減少(P=0.000),中央格時間和糞便顆粒顯著增多(P=0.035,P=0.000)。經過4周自愿轉輪運動,CUS+E組大鼠與CUS組大鼠比較,跨格次數顯著增多(P=0.021),糞便顆粒減少(P=0.008),而中央格時間無顯著改變(P=0.260);且與C 組比較,運動組大鼠開場實驗中跨格次數、中央格時間和糞便顆粒均無顯著改變(P>0.05)(見表2)。

表2 各組大鼠開場實驗中跨格次數、中央格時間及糞便顆粒結果(M±SD,n=44)Table2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Crossings,Time Spent in the Center and Fecal Particles in OFT Test in Various Groups
2.3 自愿轉輪運動對CUS大鼠前額葉皮質IL-6、TNF-a及IL-10水平的影響
雙因素方差分析顯示,慢性應激顯著影響大鼠前額葉皮質IL-6(F(1,23)=15.761,P=0.001)、TNF-a(F(1,23)=4.201,P=0.013)和IL-10(F(1,23)=4.201,P=0.002)水平;運動只顯著影響前額葉皮質TNF-a(F(1,23)=4.201,P=0.013)水平,對 IL-6(F(1,23)=0.597,P=0.449)和IL-10均無顯著影響(F(1,23)=1.976,P=0.175);運動和慢性應激對 IL-6(F1,23=0.205,P=0.655)、IL-10(F(1,23)=1.921,P=0.181)和TNF-a水平(F(1,23)=4.197,P=0.054)均無顯著交互效應。
與 C 比較,CUS 組大鼠促炎因子 IL-6 和 TNF-a 水平顯著增加(P=0.005,P=0.008),增加幅度分別為24.35%和20.45%;抗炎因子IL-10水平顯著下降(P=0.001),下降幅度為22.69%。經過4周自愿轉輪運動,CUS+E組與CUS組大鼠比較,TNF-a水平下降(P=0.024),IL-10 水平增加(P=0.022),IL-6 水平無明顯變化(P=0.396);與C組比較,運動組大鼠前額葉皮質IL-6、TNF-a和IL-10水平均無顯著改變(P>0.05)(見表3)。

表3 各組大鼠前額葉皮質炎癥因子IL-6、TNF-a及IL-10水平結果(M±SD,n=24)Table3 Result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flammatory Biomarkers(IL-6,TNF-a and IL-10)in Various Groups
2.4 自愿轉輪運動對慢性應激大鼠前額葉皮質NGF表達的影響
雙因素方差分析顯示,慢性應激及自愿轉輪運動顯著影響前額葉皮質 NGF 個數(F(1,39)=66.128,P=0.000;F(1,39)=7.960,P=0.008)和面積(F(1,39)=100.150,P=0.000;F(1,39)=19.160,P=0.000);運動和慢性應激對前額葉皮質NGF 個數和面積均無顯著交互效應(F(1,39)=0.003,P=0.956;F(1,39)=0.275,P=0.603)。
與 C 組比較,CUS 組大鼠前額葉皮質 NGF 個數(13.40±1.35)和面積[(1 274.41±114.51)μm2]均明顯下降(P=0.000),下降幅度分別為35.58%和36.10%。經過4 周自愿轉輪運動,與CUS 組大鼠比較,CUS 運動組大鼠前額葉皮質NGF 個數(16.00±4.54)和面積[(1 609.56±315.97)μm2]均明顯增加(P=0.049,P=0.001),增加幅度為19.40%和26.29%;與C 組比較,E組大鼠前額葉皮質NGF 個數(23.30±2.21)和面積[(2 257.90±159.38)μm2]均明顯增加(P=0.048,P=0.010)(見圖3、圖4)。

圖3 各組大鼠前額葉皮質NGF及TrkA比較Figure3 Comparation of NGF and TrkA Expression in PFC Among Each Groups

圖4 前額葉皮質NGF陽性神經元分布的免疫組織化學圖;Figure4 The Distribution of NGF Immunoreactive Neurons Within Prefrontal Cortex;
2.5 自愿轉輪運動對慢性應激大鼠前額葉皮質TrkA表達的影響
雙因素方差分析顯示,慢性應激及自愿轉輪運動顯著影響前額葉皮質 TrkA 個數和面積(F(1,39)=72.223,P=0.000,F(1,39)=27.489,P=0.000;F(1,39)=4.514,P=0.041;F(1,39)=4.265,P=0.046),運動和慢性應激對前額葉皮質TrkA 個數和面積均無顯著交互效應(F(1,39)=2.006,P=0.165;F(1,39)=0.592,P=0.447)。
與C組比較,CUS組大鼠前額葉皮質TrkA個數(3.90±0.74)和面積[(648.93±87.78)μm2]均顯著下降(P=0.000),下降幅度分別為51.85%和41.76%。經過4周自愿轉輪運動,與CUS組大鼠比較,CUS+E 組大鼠前額葉皮質TrkA 個數(5.40±1.35)和面積[(868.44±171.73)μm2]均顯著增加(P=0.045,P=0.049),增加幅度為38.46%和33.83%;與C 組比較,運動組大鼠前額葉皮質TrkA 個數(8.40±1.17)和面積[(1 214.89±257.97)μm2]均無顯著改變(P=0.048,P=0.010)(見圖3、圖5)。

圖5 前額葉皮質TrkA陽性神經元分布的免疫組織化學圖;Figure5 The Distribution of TrkA Immunoreactive neurons within prefrontal cortex;
3 討 論
3.1 自愿轉輪運動對慢性應激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的影響
研究認為,生理和心理壓力與許多疾病有關,如精神障礙、焦慮和抑郁。高架迷宮實驗(EPM)和開場實驗(OFT)被廣泛用于檢測動物的神經精神變化,是用來評估嚙齒類動物焦慮及抑郁行為的經典模型。前期學者通過EPM及OFT實驗證實,CUS可增加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14];并且對野生小鼠研究發現,注射CORT 導致的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可持續5~7 天,說明慢性應激可導致行為的長期變化[15]。本研究得到相同結果,大鼠經過4 周CUS 發現,與安靜對照組大鼠比較,CUS 組大鼠高架迷宮實驗中開放臂時間及次數比例均顯著減少,焦慮指數顯著增加;開場實驗中,CUS組大鼠跨格次數顯著減少,中央格時間和糞便顆粒顯著增多,與前期學者研究結果一致。
研究認為,對于焦慮及抑郁個體來說,體育鍛煉可能是一個副作用較小、低成本、容易獲得的治療選擇。R.D.GOODWIN等[16]對8 098 名成年人的研究發現,與久坐相比,規律鍛煉人群被診斷為焦慮癥的風險更低;W.DZIUBEK等[17]發現,腎病病人進行6 個月(每周3 次)體育鍛煉可顯著改善焦慮及抑郁水平,并且認為,運動可以作為重度抑郁癥患者藥物干預前或藥物干預外心理障礙的輔助治療措施;W.T.WATANASRIYAKUL 等[18]也證實,自愿運動可以改善社交孤立結合慢性應激雌性田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本研究得到相同結果,與CUS 大鼠比較,高架迷宮實驗中,CUS運動組大鼠開放臂時間和次數比例均顯著增加,而焦慮指數無顯著改變;開場實驗中,CUS運動組大鼠跨格次數顯著增多、糞便顆粒減少,而中央格時間無顯著改變。以上結果說明,自愿轉輪運動對CUS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據報道,HPA軸功能紊亂與CUS導致的大鼠焦慮及抑郁行為有關[19]。且本課題組前期研究發現,自愿轉輪運動改善CUMS 大鼠抑郁行為可能與此運動降低慢性應激大鼠腎上腺皮質增生及血漿皮質醇含量、拮抗HPA軸功能亢進有關[20]。而 I.J.SANTOS-SOTO 等[21]發現,4 周自愿轉輪運動可顯著改善小鼠焦慮樣行為,然而與安靜對照組小鼠比較,運動組小鼠血漿皮質酮水平沒有顯著差異,表明自愿動物改善小鼠焦慮類行為與皮質酮水平下降無關,認為大腦中其他分子或生化變化可能與自愿轉輪運動抗焦慮及抑郁作用有關。
3.2 自愿轉輪運動對CUS大鼠前額葉皮質炎癥因子IL-6、TNF-a和抗炎因子IL-10的影響
以往研究表明,慢性應激引起的神經炎癥在慢性應激性腦損傷中起重要作用,阻斷炎癥因子信號通路和限制小膠質細胞活化均能改善慢性應激所致的腦功能障礙[22]。B.MISIAK 等[23]認為,血液中炎癥因子濃度與抑郁癥狀嚴重程度(包括睡眠受損、認知功能障礙等)呈顯著相關,并且抑郁癥患者炎癥標志物的增加在抗抑郁藥物治療成功后恢復到控制水平,而對抗抑郁藥物治療無效的抑郁癥患者炎癥標志物增加,提示炎癥因子在抑郁癥的發病機制中起關鍵作用。TNF-a是一種重要的促炎因子,并通過刺激巨噬細胞介導IL-6、IL-8和IL-1等多種細胞因子的釋放,引起炎癥、凋亡細胞死亡,導致神經元損傷,與抑郁及焦慮樣行為有關[24]。而IL-10 被認為是一種強大的抗炎細胞因子,在限制炎癥反應和防止組織損傷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25]。I.GOSHEN等[26]發現,慢性溫和應激可增加海馬促炎因子白介素IL-1β 水平,與應激導致的抑郁及焦慮樣行為有關,而阻斷IL-1信號通路可以防止慢性應激小鼠出現抑郁及焦慮樣癥狀。另一項研究發現,產前應激誘導大鼠焦慮和抑郁樣行為與海馬炎癥介質 IL-6 及 TNF-α mRNA 表達增加有關[27]。并且 C.A.BRüNING 等[28]發現,腦室內注入TNF-α,強迫游泳實驗中大鼠靜止時間明顯增加。本研究結果發現,與安靜對照組比較,4周CUS使前額葉皮質促炎因子IL-6和TNF-α水平顯著增加,抗炎因子IL-10 水平下降。認為,急性心理或生理應激可激活HPA(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活性,增加糖皮質類固醇(Gc)過度分泌,導致促炎和抗炎細胞因子平衡失調,提示腎上腺糖皮質激素在細胞因子介導的慢性應激引起的情緒障礙疾病中發揮重要作用[29]。M.KUBERA 等[30]認為,TNF-α 可通過影響垂體和下丘腦細胞,激活HPA軸,增加ACTH及糖皮質激素(GC)水平。因此,本研究CUS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可能與慢性應激激活HPA 軸引起的前額葉皮質促炎和抗炎細胞因子失衡損害前額葉皮質結構和功能有關。
眾所周知,體育鍛煉可通過抗炎作用發揮神經保護作用[31]。M.CHENNAOUI 等[32]發現,7 周跑臺運動可減少正常大鼠海馬TNF-α 和IL-6 蛋白含量。但本研究發現,4 周自愿轉輪運動對正常大鼠前額葉皮質促炎因子TNF-α和IL-6水平,及抗炎因子IL-10 水平均無顯著影響,這種差異可能與運動時間及強度有關。S.G.WANNAMETHEE等[33]對4 252名60~79歲老年男性進行研究發現,體育鍛煉與促炎因子呈顯著負相關。C.LAVEBRATT等[34]對抑郁癥患者進行12周中等強度有氧運動發現,運動改善抑郁癥患者抑郁癥狀與IL-6水平下降有關。且研究已經表明,運動可抑制促炎癥細胞因子IL-1β 及TNF-α 積累和增強抗炎細胞因子IL-10 水平,這可能有助于創傷性腦損傷的恢復[35]。此外,J.A.FUNK 等[36]發現,自愿轉輪運動可通過下調海馬TNF-α 及IL-6 水平,升高IL-1 拮抗劑水平,從而起到保護神經、促進大腦修復的作用。本研究得到相同結果,經過4周自愿轉輪運動,CUS運動組大鼠前額葉皮質促炎因子TNF-α水平顯著下降,抗炎因子IL-10水平增加,但對促炎因子IL-6水平無顯著影響,說明此運動具有一定的抗神經炎癥作用。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4 周自愿轉輪運動可通過抑制慢性應激導致的神經促炎和抗炎細胞因子平衡失調,從而改善CUS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具體機制需進一步研究。
3.3 跑臺運動對慢性應激大鼠前額葉皮質NGF、TrkA表達的影響
研究認為,慢性應激可激活人體應激系統,與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有關。NGF廣泛分布于中樞神經系統,在神經元的發育和維持中起重要作用,并參與突觸可塑性、神經元回路形成和神經元存活。抑郁癥的神經營養假說認為,神經生長因子(NGF)及其受體(TrkA)在應激相關的情緒障礙發病機制中起關鍵作用。并且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大腦NGF在調節應激導致的焦慮及抑郁樣行為中起關鍵作用[37],但是應激對NGF水平變化的研究存在爭議。研究認為,急性及慢性應激暴露均可導致大鼠前額葉皮質NGF水平顯著下降,而抗抑郁藥治療可增強前額葉皮質 NGF 蛋白表達[38]。此外 Y.DWIVEDI 等[39]發現,28 名抑郁癥自殺患者海馬及前額葉皮層NGFmRNA水平下降,提示NGF 可能在抑郁癥自殺患者的病理生理學中發揮重要作用。然而有研究得到不同結果,P.J.FOREMAN 等[40]發現,大鼠經歷一次或多次冷刺激后,海馬NGF mRNA 水平升高,但在社會隔離和足部電擊刺激后海馬NGF mRNA 水平保持不變[41]。因此可以認為,應激導致大腦NGF表達不同可能與應激源及應激強度不同有關。前期學者研究表明,PFC在功能上與幾個大腦結構相連,參與調節情緒及認知過程,并對應激高度敏感。因此本研究聚焦PFC,通過4周慢性不可預知應激,發現與正常大鼠比較,CUS 模型組大鼠前額葉皮質NGF 及TrkA 表達顯著減少。因此可以認為,本實驗中CUS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可能與CUS抑制PFC區NGF和TrkA表達有關。
多數學者認為,運動鍛煉可以改變某些神經遞質及神經蛋白的表達,NGF與其受體TrkA結合,在突觸可塑性及神經發生中發揮重要作用,被認為是運動干預最重要的調節因子之一[42]。前期研究表明,不同方式的運動(跑臺及自愿轉輪運動)均可以增加嚙齒動物大腦NGF及TrkA的表達[43]。T.W.LIN等[44]發現,8周跑臺運動顯著增強了嚙齒動物海馬NGF 及其受體原肌凝蛋白受體激酶A(TrkA)的表達,NGF與TrkA結合可刺激下游轉錄因子CREB,誘導與細胞存活和神經可塑性相關的各種基因轉錄,最終增強神經可塑性。然而本研究發現,4周跑臺運動顯著增加了正常大鼠前額葉皮質NGF 表達,但對TrkA 表達無顯著影響。王瑋等[45]發現,腦卒中后抑郁大鼠前額葉皮質NGFmRNA 表達顯著降低,而TrkA mRNA 蛋白表達無顯著變化,認為NGF在前額葉皮質的表達存在自分泌和旁分泌2種方式,NGFmRNA 以旁分泌的形式轉移至其他部位。因此,本研究自愿轉輪運動對正常大鼠NGF及其受體TrkA水平表達不一致,可能與NGF及TrkA存在不同分泌方式有關,具體機制需進一步研究。
自愿轉輪運動已經被證明可以改善慢性應激引起的情緒障礙及認知功能下降,而運動導致NGF的增加可以通過作用于trkA受體,促進神經元的存活和突觸的形成,有助于改善應激導致的抑郁及焦慮樣行為[46]。Y.P.HONG等[47]發現,規律的跑臺運動可增加社交孤獨大鼠海馬NGF及BDNF的表達,可提高神經元的可塑性和存活,從而改善社交孤獨大鼠抑郁樣行為。本研究得到相同結果,與CUS 組大鼠比較,CUS 運動組大鼠PFC 區NGF及TrkA表達顯著增多。NGF可以保護中樞神經元免受損傷,通過開場實驗及糖水偏愛實驗證實,小柴胡湯可通過增強海馬NGF 及其受體TrkA 表達,改善慢性不可預知應激大鼠抑郁樣行為[48]。此外,Y.ZHU等[49]發現,中藥開心散可通過增強應激大鼠海馬NGF 及其受體TrkA 表達,改善應激大鼠抑郁樣行為,提示NGF-TrkA 信號通路對抗抑郁藥物的治療作用至關重要。因此,本實驗中,自愿轉輪改善CUS 大鼠焦慮樣行為可能與此運動激活前額葉皮質NGF/TrkA 信號通路有關,NGF 與TrkA結合可誘導大量突觸可塑性相關基因的表達,這些基因可能在結構和功能上啟動突觸,可調節突觸穩定性,改善慢性應激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近年來研究表明,NGF 與TrkA 的結合可激活抗炎信號通路,導致炎癥細胞因子的水平下調,并誘導抗炎介質IL-10 和IL-1ra 等水平升高,而阻斷TrkA 可導致單核細胞IL-6 和IL-1b 的分泌增加,IL-10 分泌減少,認為TrkA表達水平的改變可能是NGF 介導生理抗炎的重要機制[50]。以上研究表明,NGF-TrkA 信號通路的抗炎作用可能在慢性應激導致的情緒障礙的病理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可以推測,本實驗中自愿轉輪運動改善CUS 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可能與此運動增強前額葉皮質抗炎能力、激活NGF-TrkA信號通路,從而糾正CUS 誘導的前額葉皮質功能紊亂起到腦保護作用有關。但是,自愿轉輪運動導致CUS大鼠前額葉皮質抗炎能力增強是否與NGF/TrkA通路的激活有關,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4 結 論
4 周自愿轉輪運動可有效改善CUS 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前額葉皮質炎癥反應減弱,NGF 及TrkA 表達增加。提示,前額葉皮質可能是自愿轉輪運動改善CUS 大鼠焦慮及抑郁樣行為的作用腦區之一,且這一作用可能是由前額葉皮質抗炎能力增強、NGF-TrkA信號通路上調共同介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