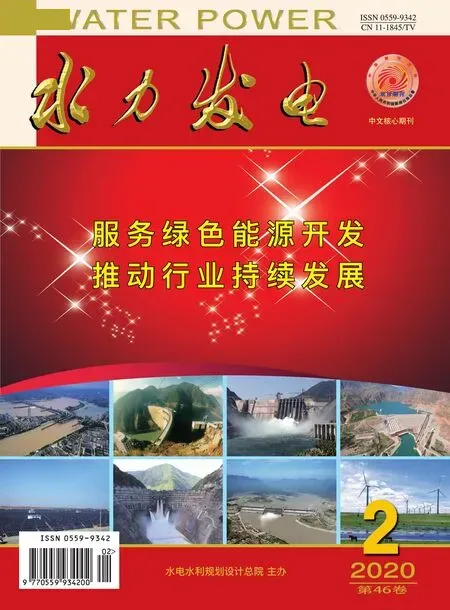近50年來烏江水沙特征變化研究
郭文獻,李 越,查胡飛,王鴻翔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河南 鄭州 450045)
烏江是長江上游南岸的最大支流,也是我國十三大水電能源基地之一[1-2],對流域內的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隨著人類活動頻繁加劇,特別是水利工程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烏江水沙特性發生改變。水利工程的攔截作用改變了下游河流自然流動狀態,這勢必會對流域內水沙和生態造成一定影響。近幾十年來,國內同時出現大量的科學文獻以研究人類活動對河流水沙狀況的影響[3-7]。鑒于以往單獨對烏江控制水文站武隆站研究較少,且有關研究采用的方法較為傳統且單一,不能系統闡述其水沙特征變化規律。本文通過烏江流域武隆站實測徑流泥沙數據資料,采用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法,均值差異T檢驗,雙累積曲線法和小波分析等方法對烏江水沙特征及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以便更好的了解人類活動對烏江流域水沙特性的影響。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及數據
研究區域為烏江流域,流域集水面積87 920 km2,干流全長1 037 km,天然落差2 124 m,為長江上游右岸的最大一級支流,流域內多年平均徑流量為4.82×1010m3,多年平均輸沙量為1.92×107t。其中,武隆水文站位于烏江下游,為烏江匯入長江的控制水文站;故研究采用武隆水文站1956年~2015年的徑流量、輸沙量數據資料分析近幾十年來烏江徑流泥沙演變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其中的徑流泥沙數據來源于長江流域水文年鑒。
1.2 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法
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通過計算時間序列數據的標準化變量UF,與某一置信水平α(取0.05)下的臨界變量對比。當UF為正表示有上升趨勢,為負則表示有下降趨勢;當UF超出臨界值時表明上升或下降趨勢顯著。同時對原時間序列的逆序列進行同樣的統計量計算,使UB=-UF,若兩條曲線在95%置信度水平內出現交點,表明在該時間點發生突變,方法具體計算參考文獻[7- 8]。
1.3 均值差異T檢驗法
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不受樣本值和分布類型的干擾,但是檢驗過程中可能出現多個突變點,需要對這些突變點進行驗證。均值差T檢驗法假定時間序列某一時段的平均值與另一時段平均值之間差異具有充分的統計顯著性,則認為在給定信度范圍內的選定時間點上出現了突變現象[9]。即,可以針對某一基準點進行突變性檢驗。具體步驟如下。
定義樣本長度為N的序列突變指數為
AI=|X1P-X2P|/(S1+S2)
(1)
式中,X1p和S1為基準年前M1年的平均值和標準差;X2p和S2為后M2年的平均值和標準差。計算時采用連續移動基準年的方法,就可得突變指數AI的時間序列。
定義統計量
t=(X1p-X2P)/[Sp(1/M1+1/M2)1/2]
(2)
(3)
式中,M1和M2為基準年前后兩段序列的樣本長度;SP為聯合樣本方差。統計量t服從自由度為M1+M2-2的t分布。當給出一定的顯著水平α,如t 小波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一簇小波函數系來表示或逼近某一信號或函數。在小波變換中,比較常用的小波函數有Mexican Hat小波、Dmey小波和Morlet小波等[12]。本研究選取復Morlet小波對烏江流域水沙時間序列進行周期性分析。復Morlet小波函數是小波分析的關鍵,小波分析是指具有震蕩性、能夠迅速衰減到零的一類函數,亦即小波函數φ(t)∈L2(R)且滿足 (4) 式中,φ(t)為基小波函數,可通過尺度的伸縮和時間軸上的評議構成一簇函數系 (5) 式中,φa,b(t)為子小波,若φa,b(t)是由式(5)給出的子小波,對于給定的能量有限信號f(t)∈L2(R),其連續小波函數為 (6) 雙累積曲線是檢驗兩個參數間關系一致性及變化的方法,通過在直角坐標系中繪制同時期內一個變量連續累積值與另一個變量的連續累積值關系曲線,可用于水文氣象要素一致性檢驗、缺值插補及趨勢性變化和強度分析[14-15]。 為揭示烏江流域多年徑流泥沙變化趨勢,采用武隆站徑流泥沙多年統計資料點繪出武隆站1956年~2015年的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相關圖(見圖1)。 圖1 武隆站年徑流量和輸沙量變化 從圖1可以看出,在研究區間內除1966年、1981年和2006年(1966年和2006年為枯水年,1980年烏江渡水電站正式蓄水)年徑流量出現較大波動外,年徑流量整體上無明顯變化。年輸沙量和年徑流量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保持較好的一致性,基本呈現大水大沙、小水小沙的狀態;中期后輸沙量開始呈下降趨勢,到2000年后基本已不足1×107t,下降趨勢極為明顯。 由于武隆站徑流量和輸沙量年際變化波動性較強,直觀地觀察其變化規律存在一定局限;為定量評估年徑流量和年輸沙量變化趨勢,采用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進行趨勢性變化評價。經計算,年徑流量、輸沙量的Mann-Kendall標準化變量UF分別為-0.50,-7.14。取顯著性水平α=0.05,則對應的臨界值UFα=1.96;而|UF|徑流量<|UF|α,|UF|輸沙量>|UF|α。因此,烏江流域近50年來年徑流量無明顯下降趨勢,而年輸沙量下降趨勢顯著,通過95%置信度檢驗。 根據Mann-Kendall統計檢驗結果分析(見圖2),武隆站多年徑流量基本處于0.05顯著水平范圍內,年徑流量UF和UB曲線交點出現在2010年且交點均落入0.05顯著性水平內,表明徑流量突變點可能發生在2010年。輸沙量在1958年~1975年呈增加趨勢,1975年后開始呈減少狀態,1980年后超出95%置信度檢驗,且下降趨勢不斷增強;年輸沙量UF和UB曲線相交于1992年,但交點并未落入0.05顯著性水平范圍內,但考慮到20世紀80年代末烏江流域內已建電站1 630座[16],總庫容達到44.06億m3,水庫攔沙效果顯著,因此也將1992年考慮為可能突變年份。 圖2 武隆站徑流量、輸沙量Mann-Kendall統計值 為了檢驗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法對武隆站突變結果的準確性,采用均值差異T檢驗對上述突變結果進行驗證。選取顯著性水平α為0.01,其對應的臨界值tα為2.704,計算結果參見表1。對于年徑流量,當M=55時,突變指數為0.35,對應的統計量1.59 表1 武隆站年徑流量和輸沙量均值差異T檢驗 從圖3小波分析中可看出,徑流量存在著明顯的年際變化特征。在較大時間尺度上,20世紀80年代之前主要存在25~28 a的周期變化規律,經歷了豐→枯→豐3次交替變化;20世紀80年代后變化為徑流量為20~25 a的周期變化規律,經歷了枯→豐→枯→豐4次交替并且兩個階段的周期變化表現都較為穩定。在小尺度周期上,主要存在13~15 a,8~11 a和3~5 a的周期性變化規律,且小尺度周期上豐枯變化較為頻繁。由徑流量小波方差圖(見圖3)可以看出,年徑流變化的主周期為28、15、11 a和5 a,其中,以28 a未主周期的小波方差最大,說明烏江徑流在28 a時間尺度上的周期性最為顯著。 圖3 武隆站徑流量小波分析等值線圖和小波方差 圖4 武隆站輸沙量小波分析等值線圖和小波方差 從圖4可以看出,在較大時間尺度上,20世紀70年代中期前主要存在20~25 a的周期變化規律,經歷了豐→枯→豐3次交替變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周期變長且不連續,分析其原因與烏江流域梯級水電站開發導致輸沙量顯著下降有關,在小尺度周期上,主要存在8~10 a和3~6 a的周期性變化規律。從小波方差圖中可以看出,輸沙量變化以25、10、6 a為主周期。 雙累積曲線法主要利用水沙累積的變化特點研究徑流泥沙的變化,當雙累積曲線為一條直線時,表明徑流泥沙無明顯變化;若累積曲線在某點發生明顯轉折,則表明水沙關系發生顯著變化[17]。根據上述徑流泥沙趨勢性、突變性分析和武隆站徑流量—輸沙量雙累計曲線(見圖5),將大通站徑流泥沙時間序列劃分為1956年~1976年,1977年~1993年,1994年~2015年3個階段。從圖5中可以看出,3個階段的線性擬合方程斜率表現為減小趨勢,1974年~1993年線性擬合方程斜率減少相對平穩,而1994年~2015年線性擬合方程斜率明顯降低,說明武隆站年輸沙量在近20年來迅速減少。通過武隆站徑流量—輸沙量雙累積曲線的線性擬合方程估算各階段累積輸沙量相對于上一階段的減少量,具體計算方法參見文獻[18]。分別將1993年和2015年武隆站累積徑流值(184.31×1010m3和289.01×1010m3)分別帶入公式y=0.741 3x-0.080 1和y=0.419 4x+26.878,可得1993年和2015年在曲線轉折前的累積輸沙量分別為136.54×107t和148.09×107t。將1993年和2015年武隆站的累積徑流值分別帶入y=0.419 4x+26.878和y=0.094 4x+88.241,可得1993年和2015年在曲線轉折后的累積輸沙量104.18×107t和115.52×107t。亦即,1977年~1996年和1997年~2015年兩個階段的累積減沙量分別為32.36×107t和32.57×107t。 圖5 武隆站徑流量—輸沙量雙累積曲線 圖6 武隆站年徑流量與輸沙量關系 影響流域內徑流量和輸沙量的因素主要包括流域內下墊面條件、自然災害、氣候降雨、人類影響等[21],其中又以降雨和人類活動對河流產水產沙影響較大。烏江流域多年來年均降水量略有減少[22],且沿江取水稍有增加,但變幅不大,造成年徑流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少。這與上述Mann-Kendall分析中烏江年徑流量無明顯減少相一致;同時,各水文站Mann-Kendall趨勢檢驗的水沙趨勢性變化也不相同。這說明年徑流量的減少對年輸沙量顯著減少造成一定影響外,人類活動對年輸沙量減少也存在重要影響。人類活動主要包括水庫蓄水攔沙、水土保持措施等綜合因素,考慮到水土保持造成減沙量在200萬~300萬t[16],對烏江流域輸沙量減少可忽略不計,因此本文重點考慮水庫蓄水攔沙對烏江流域年輸沙量的影響。 為了評價水庫蓄水攔沙對烏江流域年輸沙量的影響,以武隆站作為總控制站分析烏江流域內大型水庫建設情況與武隆站輸沙量年際變化的關系,繪出烏江流域的水庫建設總庫容與年輸沙量變化關系曲線(見圖7)。從圖7中可看出,流域內水庫建設總庫容增加與年輸沙量減少之間存在著良好的對應關系。截止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烏江流域建成一些水庫,但由于庫容相對較小,因此對武隆站輸沙量減少造成的影響較小,輸沙量在3.44×107t上下波動,無明顯的下降趨勢。截止到1979年烏江上第一座大型水電站烏江渡水電站建成蓄水后,水庫攔截大量泥沙,造成武隆站年輸沙量顯著減少,年輸沙量下降到1.88×107t左右,下降幅度達到45.35%。2000年后,隨著洪家渡、構皮灘、思林等水電站陸續建成,水庫的攔沙效應也不斷增大,基本攔截河流泥沙,年輸沙量下降到0.49×107t,武隆站年輸沙量進一步減少。 圖7 武隆站輸沙量和累積庫容變化過程 (1)通過徑流泥沙的趨勢性分析,武隆站徑流量無明顯變化,其Mann-Kendall標準化變量為-0.50,未通過95%置信度檢驗;輸沙量的Mann-Kendall標準化變量為-7.14,通過95%置信度檢驗,表明輸沙量下降趨勢顯著。 (2)根據Mann-Kendall非參數檢驗法和均值差異T檢驗法對武隆站徑流泥沙進行突變分析,結果表明年徑流量未發生突變,年輸沙量在1992年發生突變,突變點對應的統計量t為8.32。 (3)通過小波分析可得,烏江流域武隆站徑流泥沙序列存在多時間尺度變化特征,徑流量和輸沙量分別存在4類和3類時間尺度周期,年徑流量變化以20~23 a為主要周期,年輸沙量變化以25~28 a為主要周期。 (4)由徑流泥沙的雙累積和水沙關系階段性分析將武隆站劃分為1956年~1976年,1977年~1993年,1994年~2015年3個階段。其中,1971年~1996年和1997年~2015年2個階段的累積減沙量分別為32.36×107t和32.57×107t,且水沙關系、輸沙能力在1974年~1993年變化最為明顯。 (5)通過對烏江流域水庫蓄水攔沙對年輸沙量的影響分析可知,流域內水庫建設總庫容增加與年輸沙量減少之間存在著良好的對應關系,隨著累積庫容不斷增加,年輸沙量逐漸減少,說明水庫蓄水攔沙是導致輸沙量顯著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1.4 小波分析


1.5 雙累積曲線法
2 結果與討論
2.1 徑流泥沙趨勢性分析

2.2 徑流泥沙突變性分析


2.3 徑流泥沙周期性變化分析


2.4 徑流泥沙雙累積分析

2.5 水沙關系階段性變化分析

3 徑流泥沙演變影響因素

4 結 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