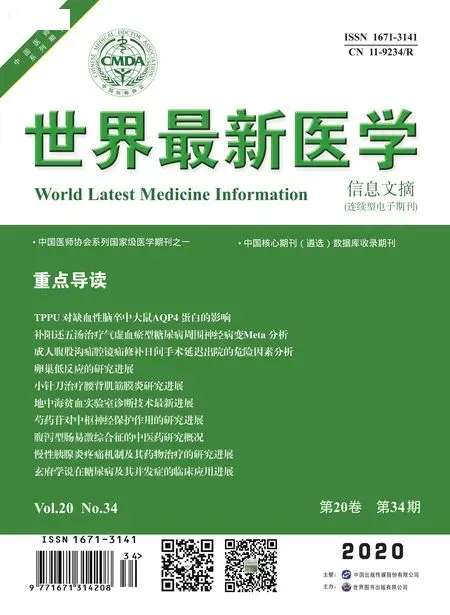基于中醫傳承輔助平臺分析中醫藥治療糖尿病前期的用藥規律
李佳,宋朝
(1.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2017 級碩士研究生,山西 太原;2.山西中醫藥大學2017 級碩士研究生,山西 太原)
0 引言
我國2 型糖尿病患病率逐年增高,2013 年公布普查[1]結果顯示我國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為35.7%,對于糖尿病前期的發病機制,目前醫學界尚無統一認識,仍處于研究探討階段,但認為其與家族遺傳性及個體生活環境等因素有關的這一觀點目前被多數醫家所認可;而關于影響糖尿病前期轉歸的因素,多數認為與胰島素、腸促胰島素、胰高血糖素、瘦素、胰淀素等多種胃腸激素及全身脂代謝、糖代謝等各系統的代謝異常改變有關,對于該病的治療,西醫學主張首先進行生活方式的干預治療,對于干預效果不明顯者,可適當配合藥物,但無明確指南推薦,中醫藥有多靶點作用模式,在治療糖尿病前期方面有獨特的優勢,但因辨證特點使中醫處方靈活多變,藥物劑量難以把握,給臨床用藥及經驗傳承帶來一定的困難。本文旨在應用中醫傳承輔助平臺分析其組方規律,發掘新處方,為臨床運用中醫藥治療糖尿病前期提供新的思路。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檢索
文獻來源于中國知網(1985-2018 年)所收錄期刊:在中國知網檢索模塊,點擊高級搜索按鈕,以糖尿病前期、糖代謝紊亂為主題,檢索從1985 年1 月1 日至2018 年12 月31 日與“糖尿病前期”相關文獻。
1.2 分析平臺
中醫傳承輔助平臺(V2.5),該平臺軟件由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提供。
1.3 方藥納入標準
選取有關中醫藥治療和中西醫結合治療糖尿病前期的相關文獻;且中藥處方中藥物組成及劑量明確;臨床研究或試驗。
1.4 排除標準
綜述類文獻;方劑組成或劑量介紹不明確者;動物實驗;少數民族醫藥診治;外用、針灸、灌腸、穴位貼敷等治療;膠囊或液體等制劑;理論探討等。
1.5 篩選結果及規范用語
在檢索所得3377 篇文獻中共篩選出符合條件文獻共68 篇。中藥參考《中國藥典》(2010 版),將山萸肉統一為山茱萸;夜交藤統一為首烏藤;川斷統一為續斷。
1.6 數據錄入及核對
將檢索收集到的符合條件處方藥物依次錄入中醫傳承輔助平臺中,在錄入完畢后,由兩人再次將收集到的處方與錄入數據進行校對,以確保錄入數據的準確性及完善性。
1.7 數據挖掘與分析
在“中醫傳承輔助平臺”中“數據分析”頁面中進入“方劑分析”模塊,對錄入的方藥進行分析。具體方法為: 提取出錄入系統中的治療糖尿病前期的全部方藥,通過“頻次統計”、“用藥模式”、“組方規律”、“規則分析”、“新方分析”等模塊功能分析用藥規律,得到結果并發現潛在的新組方。
2 分析結果
2.1 所得方藥一般情況
本次研究共收集符合條件處方101 首,納入藥物148 味,合計1021 次。
2.2 用藥頻次分析
處方中藥物頻次≥20 次的藥物共有12 味,見表1。

表1 糖尿病前期中藥物頻次統計情況(≥20)
2.3 性味、歸經分析
(1) 中藥四氣分析結果:如下圖1 所示,101 例處方中所涉及的中藥四氣按所占比重從高到低排列依次為:溫348(36.14%),寒314(32.61%),平207(21.5%),涼82(8.52%),熱12(1.25%)。

圖1 使用中藥在四氣中所占比重統計
五味分析結果:如下圖2 所示,101 例處方中五味各自占比情 況 為:甘565(37.02%),苦504(33.03%),辛331(21.69%),酸73(4.78%),咸38(2.49%),澀15(0.98%)。


圖2
藥物歸經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101 例處方中中藥歸經占比前六位的依次為:脾經、胃經、肺經、肝經、心經、腎經。

表2 中藥歸經分析統計表
2.4 基于關聯規則的處方規律分析
2.4.1 表3 顯示,設定“支持度”為15,“置信度”設為0.6,點擊“用藥模式”得到常用藥物組合16 個,點擊“規則分析”分析所得組合的規則。

表3 處方中頻度≥ 15 的藥物組合情況
2.4.2 基于改進的互信息法的藥物間關聯度分析
將相關度設置為5,懲罰度設置為2,進行聚類分析,演化得到潛在核心藥物組合6 個(見表4),進而在核心藥物組合的基礎上聚合生成新處方3 個(見表5)。

表4 基于復雜系統熵聚類的處方藥物核心組合

表5 基于嫡層次聚類新處方

圖3 新方藥物組合關聯網絡圖
3 分析及討論
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是在我國發病率高達35.7%,且呈逐年升高趨勢,現代醫學界對于糖尿病前期的發病機制尚無明確定論,多數認為其與遺傳敏感性及環境等因素有關[2]。西醫學治療經飲食、運動控制不佳的患者時,通常加用口服藥物以達降糖效果,但目前尚無充分的證據表明藥物干預具有長期療效和衛生經濟學益處,同時藥物毒副作用給患者的損傷不可忽視。祖國醫學將其歸屬為“脾癉”范疇之中,《素問·奇病論》中記載:“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明確闡述了由正常肥胖狀態到糖代謝紊亂,再由糖代謝紊亂進展而成糖尿病病理狀態的過程。隨著眾學者不斷地研究,對于此病的認識也不斷地深入,大多醫家認為脾癉屬“本虛標實”[3]之證,本虛在于脾、肝、腎三臟,標實在于虛熱內生,傷津耗液,久滯成瘀、痰等實邪。
表1 分析藥物頻次可知,治療脾癉用藥多從“內熱”、“脾虛”入手,補氣藥中黃芪、山藥、白術用藥頻次高,清熱藥中黃連、葛根、生地等用藥頻率較高。黃芪為補氣之要藥,《藥性賦》謂其可“溫分肉而實腠理,益元氣而補三焦,內托陰證之瘡瘍,外固表虛之盜汗。”現代藥理表明黃芪[4]不僅具有補氣升陽,固表利水之功,還具有降低血糖的功能;茯苓為性平味甘淡,甘則能補,淡則能滲,藥性平,故即可祛邪,又可扶正,為利水消腫之要藥,主治脾虛、痰飲等證。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茯苓[5]還具有增強免疫力、護肝、降血糖、增強心肌收縮力等功效。從表1 中發現,用藥頻次較高的藥物多為健脾利濕,清瀉內熱之品。
通過基本信息中的性味、歸經分析得出,藥物歸經多為脾經,藥性偏為苦甘辛的運用,澀味最少。《素問·金匱真言論》曰“中央黃色,入通于脾……藏精于脾”,又如《素問·經脈別論》所記載:“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水氣四布,五經并行”,可見脾之運化正常對機體功能正常運行至關重要。《內經》中言“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故五味中注重辛苦甘的運用,既能散邪實,又可益正氣。甘味藥主要歸脾經,可以得出脾癉病位主要在脾臟,與肺密切相關。
據表3 常用藥對組合可得到頻率前三的為葛根-黃芪、陳皮-茯苓、黃芪-茯苓,由此可分析可知脾癉用藥多以清熱利濕、補氣健脾為重,以達到濕熱除則脾氣旺,脾氣旺則濕熱無由所生之目的。此也符合《素問·奇病論》中關于脾癉“治之以蘭,除陳氣也”觀念。梁曉春[6]等認為脾癉“責之濕熱”,提出治療以清熱健脾祛濕為主;施今墨老先生提出糖尿病前期的主要治療原則為健脾益氣。綜合上述醫家之觀點不難發現,本病綜述本虛標實,多數醫家治療多從脾虛出發,兼以清熱、利濕、化痰、祛瘀等。
運用中醫傳承輔助平臺的數據分析,得到治療脾癉的3 個新處方。新方一:具有燥濕化痰,補氣清熱之功效,可用于脾虛濕滯兼痰熱之證;新方二:具有補氣滋陰,清熱涼血之功,“陽化氣,陰成形,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故予黃芪、陳皮等補陽氣以滋陰,適用于氣陰兩虛之證;新方三多為活血藥,血為氣之母,氣為血之帥,輔以補氣清肺潤燥之品,氣行則血行,氣順則瘀漸消,適用于氣虛內熱兼血瘀之證。總之,3 個新處方藥味雖簡,組方偏奇,但充分的體現了脾癉病的病因病機,即:脾氣虧虛、陰虛燥熱、脾虛痰瘀內阻致津液運化失常,久之成痰、瘀等實邪,導致糖代謝紊亂的發生,同時也進一步提示脾癉治療時不可一味進補,應當清補雙顧,補而不滯,使中氣得健,陰津自生,內熱得消。
綜上所述,糖尿病前期的治療具有多樣性和相似性,本文通過中醫傳承輔助平臺分析了治療糖尿病前期的用藥規律,同時分析得到了治療此病的核心組合及新處方,但仍需進一步臨床驗證。中醫傳承輔助平臺對中醫藥臨床經驗的總結和傳承提供了科學有效的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