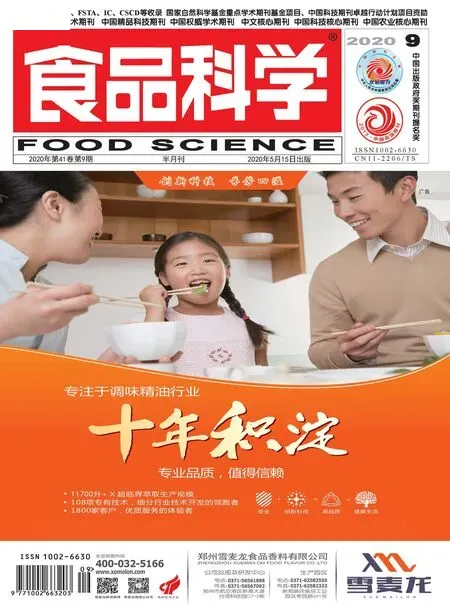咖啡苦味特性研究進(jìn)展
陳鈺瑩,孫紅波,宋蕭蕭,柴 玉,王博覽,冷小京*
(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食品科學(xué)與營養(yǎng)工程學(xué)院,食品精準(zhǔn)營養(yǎng)與質(zhì)量控制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功能乳品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北京 100083)
咖啡豆是茜草科咖啡屬植物的種子,是一種重要的熱帶經(jīng)濟(jì)作物[1]。近幾十年來,咖啡的全球消費(fèi)量每年增長1%~2%[2]。中國是世界上咖啡消費(fèi)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國內(nèi)咖啡市場(chǎng)以每年20%的速度擴(kuò)大,呈現(xiàn)良好的發(fā)展勢(shì)頭與前景。云南和海南為中國咖啡主產(chǎn)地,全國咖啡種植面積12余萬hm2,鮮果產(chǎn)量70多萬t,總產(chǎn)值達(dá)16.24億 元[3]。咖啡能夠流行的原因除其具有提神醒腦的功能外,主要與其特征香氣及特征苦味有關(guān)。咖啡的苦味可直接影響消費(fèi)者對(duì)咖啡的接受度[4]。在人的基本味覺里,苦味最具有矛盾性,既易導(dǎo)致人產(chǎn)生不悅甚至排斥的感覺,被認(rèn)為是抵御有毒物質(zhì)的防御機(jī)制[5],又可參與食品風(fēng)味的構(gòu)成,增強(qiáng)食品感官吸引力,如咖啡、茶、啤酒和柚子等食品中苦味是受歡迎的[6]。
咖啡的苦味來源于豆體所含的苦味物質(zhì)及烘焙過程中形成的苦味化合物。咖啡因、葫蘆巴堿、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生的非揮發(fā)性雜環(huán)化合物,如呋喃衍生物、吡嗪以及2,5-二酮哌嗪等被認(rèn)為是咖啡苦味的主要貢獻(xiàn)者[7]。然而,研究發(fā)現(xiàn)綠原酸(咖啡酰奎寧酸)受熱產(chǎn)生的苦味同樣具有代表性,如綠原酸內(nèi)酯化生成的綠原酸內(nèi)酯[8]或通過4-乙烯鄰苯二酚(4-vinylcatechol,4-VCA)途徑所生成的多羥基苯基林丹類化合物[9],但目前對(duì)綠原酸烘焙產(chǎn)物的苦味物質(zhì)研究尚不深入。
人體對(duì)咖啡味覺特性的認(rèn)知受多種因素干擾,不僅與人體的苦味生理機(jī)制有關(guān),也與理化分析技術(shù)和品鑒方法有關(guān)。與咖啡揮發(fā)性物質(zhì)的研究相比,目前對(duì)咖啡苦味物質(zhì)的研究偏少,且系統(tǒng)性不足[8]。本文基于人體味覺的苦味通路特性,從咖啡烘焙條件出發(fā),主要對(duì)比了生物堿、綠原酸產(chǎn)物及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等苦味物質(zhì)的特性,歸納了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常見的鑒定方法,以期為咖啡產(chǎn)品質(zhì)量控制及加工工藝的改進(jìn)提供參考。
1 苦味信號(hào)轉(zhuǎn)導(dǎo)通路
人體苦味的感知源自味覺細(xì)胞的苦味受體TAS2Rs家族對(duì)苦味物質(zhì)的感知。TAS2Rs是一類由多肽鏈形成的具有7 個(gè)跨膜螺旋結(jié)構(gòu)的G蛋白偶聯(lián)受體[10]。TAS2Rs通過與苦味物質(zhì)的結(jié)合而激活,經(jīng)G蛋白變構(gòu)或促使第二信使環(huán)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濃度降低,導(dǎo)致cAMP離子通道抑制作用解除,或刺激肌醇三磷酸的磷脂酶Cβ2合成,引發(fā)內(nèi)質(zhì)網(wǎng)儲(chǔ)存的Ca2+釋放,使苦味受體細(xì)胞去極化,釋放神經(jīng)遞質(zhì)[11]。此外,升高的Ca2+水平也可打開瞬時(shí)受體電位陽離子通道TRPM5,導(dǎo)致細(xì)胞膜去極化和神經(jīng)遞質(zhì)釋放,向大腦發(fā)送苦味信號(hào)[12]。
苦味物質(zhì)的識(shí)別依賴于相關(guān)TAS2Rs基因的表達(dá)。在TAS2Rs基因家族中,已知的人類苦味受體基因有10 個(gè),分別是hT2R4、hT2R16、hT2R7、hT2R10、hT2R14、hT2R43、hT2R44、hT2R38、hT2R47和hT2R46[13],遠(yuǎn)少于自然界中苦味物質(zhì)的數(shù)量,這意味著人體對(duì)苦味類型的識(shí)別并不精準(zhǔn)。此外,人體對(duì)苦味物質(zhì)識(shí)別的過程還會(huì)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如咖啡因,其能被TAS2R7、TAS2R10、TAS2R43、TAS2R46同時(shí)識(shí)別,是典型的苦味物質(zhì)。但咖啡因可阻止腺苷與受體結(jié)合,提高多巴胺的利用率,興奮中樞神經(jīng),弱化對(duì)苦味的排斥反應(yīng)[14]。
味覺受體能對(duì)苦味物質(zhì)產(chǎn)生明確生化反應(yīng),但苦味信息的整合處理需經(jīng)腦神經(jīng)中樞執(zhí)行。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shù)對(duì)靈長類動(dòng)物單個(gè)神經(jīng)元興奮性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味覺信息在味覺通路中的影響遍及孤束核、丘腦、腦島、額葉島蓋及眶額皮質(zhì)尾側(cè)等[15]。腦島及額葉島蓋為初級(jí)味覺中樞,眶額皮質(zhì)尾側(cè)為二級(jí)味覺中樞[16]。其中苦味的作用多表現(xiàn)在前額葉背側(cè)皮質(zhì)、前額葉前皮質(zhì)腹側(cè)部、前額葉前區(qū)、海馬旁皮層等的激活[17]。雖然神經(jīng)元對(duì)味覺刺激的反應(yīng)具有特異性,但不同的味覺區(qū)域在大腦中交匯會(huì)導(dǎo)致味覺之間存在影響[18],使人對(duì)苦味認(rèn)知反應(yīng)不一致。
2 咖啡中主要苦味物質(zhì)
咖啡豆分為‘阿拉比卡(Arabica)’、‘羅布斯塔(Robusta)’、‘利比里亞(Liberica)’三大原種,最具有商業(yè)價(jià)值的是‘阿拉比卡’咖啡豆和‘羅布斯塔’咖啡豆,烘焙后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比‘羅布斯塔’咖啡豆具有更豐富的香氣,而‘羅布斯塔’咖啡豆具有更強(qiáng)的苦味[19]。云南和海南為中國咖啡主產(chǎn)地,由于氣候環(huán)境等原因,云南咖啡主要為‘阿拉比卡’咖啡豆,海南興隆地區(qū)主要生產(chǎn)‘羅布斯塔’咖啡豆。
咖啡按照烘焙程度可分為淺度、中度及深度烘焙3 種。熱風(fēng)烘焙是常用的咖啡烘焙方式,烘焙時(shí)間通常為2~25 min,烘焙溫度為200~250 ℃,表1顯示了特定烘焙溫度下,達(dá)到某種烘焙強(qiáng)度所需要的時(shí)間。咖啡的烘焙程度決定了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的種類及數(shù)量[20]。一般認(rèn)為隨著烘焙強(qiáng)度增加,咖啡的苦味物質(zhì)不斷增多,另外咖啡的研磨程度和沖泡方式也會(huì)影響咖啡的苦味程度,目前已知的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主要為生物堿、綠原酸烘焙產(chǎn)物、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等。

表 1 咖啡烘焙強(qiáng)度與溫度和時(shí)間的關(guān)系[20-22]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ffee roasting degree and roasting temperature and time[20-22]
2.1 生物堿
生物堿是一類存在于生物體內(nèi)的含氮堿性有機(jī)化合物,多數(shù)具有復(fù)雜的含氮雜環(huán),在植物中常與有機(jī)酸結(jié)合成鹽而存在,還有少數(shù)以有機(jī)酸酯、糖苷和酰胺的形式存在[23]。生物堿是咖啡生豆中主要苦味物質(zhì)來源。咖啡中的生物堿包括咖啡因、葫蘆巴堿、可可堿等。咖啡因在‘阿拉比卡’咖啡生豆中的質(zhì)量分?jǐn)?shù)為0.8%~1.4%,在‘羅布斯塔’咖啡生豆中為1.7%~4.0%[24]。咖啡生豆中葫蘆巴堿質(zhì)量分?jǐn)?shù)為0.83%~1.13%,可可堿質(zhì)量分?jǐn)?shù)為0.004 8%~0.009 4%[25],研究發(fā)現(xiàn)咖啡因占咖啡生豆苦味強(qiáng)度的30%,葫蘆巴堿占1%[24]。
2.1.1 咖啡因
咖啡因是一種甲基黃嘌呤,具有神經(jīng)中樞興奮作用。咖啡因在‘羅布斯塔’咖啡生豆中的含量高于‘阿拉比卡’咖啡。咖啡因的苦味閾值約為500 μmol/L。咖啡因熱穩(wěn)定性強(qiáng),烘焙后質(zhì)量不會(huì)發(fā)生明顯改變[26],但烘焙過程中水分的蒸發(fā)會(huì)導(dǎo)致咖啡因含量相對(duì)提升,提升水平約為0.002%~0.227%[27]。咖啡因雖然不是烘焙咖啡主要的苦味貢獻(xiàn)者,但作為功能性成分,能明顯影響消費(fèi)者對(duì)咖啡的接受度。
2.1.2 葫蘆巴堿
葫蘆巴堿是經(jīng)植物體內(nèi)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和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代謝或轉(zhuǎn)化生成的一種生物堿[23],具有降血糖、抗腫瘤的作用。葫蘆巴堿具有苦澀味,烘焙溫度180 ℃以上時(shí),50%~80%的葫蘆巴堿會(huì)發(fā)生降解。隨著烘焙程度增加,‘阿拉比卡’咖啡豆中葫蘆巴堿含量降低至0.553%~1.293%,‘羅布斯塔’咖啡豆中降低至0.571%~0.902%[28],該降解過程產(chǎn)生了重要化合物——水溶性煙酸(又稱尼克酸或VB3)[29]和芳香化合物吡啶和吡咯[30],對(duì)咖啡飲料的質(zhì)量產(chǎn)生影響。
2.2 綠原酸烘焙產(chǎn)物
綠原酸烘焙產(chǎn)物和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生的苦味物質(zhì)是烘焙咖啡中主要的苦味物質(zhì)來源。綠原酸又稱咖啡酰奎寧酸(caffeoylquinic acid,CQA),是由咖啡酸和奎寧酸縮合而成的羥基肉桂酸類化合物[31]。綠原酸在咖啡生豆中的含量很高,質(zhì)量分?jǐn)?shù)約為6.7%~12%,‘羅布斯塔’咖啡生豆中綠原酸含量比‘阿拉比卡’咖啡生豆高25%左右[32]。高溫烘焙會(huì)導(dǎo)致綠原酸的損失。一般烘焙后咖啡豆中的綠原酸質(zhì)量為咖啡豆干質(zhì)量的2.7%~3.1%。咖啡中常見的綠原酸單體為5-CQA、diCQA以及阿魏酸酰奎寧酸。其中5-CQA的含量最高,約占到咖啡中總綠原酸含量的72%[33-34]。
2.2.1 奎寧酸
綠原酸受熱分解會(huì)產(chǎn)生咖啡酸和奎寧酸。‘阿拉比卡’生咖啡豆中奎寧酸質(zhì)量分?jǐn)?shù)約為0.55%,‘羅布斯塔’生咖啡豆中約為0.35%,中度烘焙咖啡豆中為0.63%~1.16%[35],深度烘焙咖啡豆中為0.97%~1.24%[36]。10 mg/L奎寧酸溶液會(huì)呈現(xiàn)出類似阿司匹林的苦澀味[37]。由于奎寧酸在烘焙過程中其含量可超過味覺閾值20 倍,因此被認(rèn)為是導(dǎo)致咖啡苦味的原因之一[38]。
2.2.2 綠原酸內(nèi)酯
綠原酸加熱會(huì)發(fā)生內(nèi)酯化反應(yīng)生成綠原酸內(nèi)酯。Blumberg等[9]對(duì)比了不同溫度(190~280 ℃)下烘焙6 min咖啡豆中綠原酸內(nèi)酯生成量的變化,發(fā)現(xiàn)在240 ℃下烘焙的咖啡豆中綠原酸內(nèi)酯含量最高。當(dāng)烘焙溫度從190 ℃升高至240 ℃時(shí),單酰奎寧酸內(nèi)酯質(zhì)量濃度從17.5 mg/L增加至174.5 mg/L,而當(dāng)烘焙溫度繼續(xù)升高至280 ℃時(shí),單酰奎寧酸內(nèi)酯質(zhì)量濃度降低至190 ℃時(shí)的水平。由此可見,綠原酸內(nèi)酯含量在中度烘焙條件下最高,深度烘焙條件下會(huì)發(fā)生分解。綠原酸內(nèi)酯的苦味閾值較低,為9.8~180 μmol/L[37],是咖啡中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苦的物質(zhì)。盡管綠原酸內(nèi)酯在咖啡中的含量很低,但對(duì)咖啡質(zhì)量的影響是顯著的[9,39]。
2.2.3 多羥基苯基林丹

圖 1 多羥基苯基林丹生成途徑[37]Fig. 1 Route map of reactions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bitter compounds multiply hydroxylated phenylindanes[37]
多羥基苯基林丹是綠原酸和咖啡酸通過4-VCA途徑生成的一類化合物(表2),具體反應(yīng)途徑如圖1所示。綠原酸水解生成咖啡酸和奎寧酸。咖啡酸脫羧反應(yīng)生成4-VCA[40],綠原酸也可以發(fā)生synperiplanar消除反應(yīng)直接生成4-VCA。4-VCA與其質(zhì)子化產(chǎn)物4-乙烯鄰苯二酚氧鎓離子(4-vinylcatechol-H+,4-VCA-H+)二聚生成關(guān)鍵中間體4-VCA二聚體氧鎓離子。
4-VCA二聚體氧鎓離子通過分子內(nèi)重排生成苦味物質(zhì)反式-1,3-雙(3’,4’-二羥基苯基)丁烯(trans-1,3-bis(3’,4’-dihydroxyphenyl)-1-butene,3,4-DHP-B)(化合物3)。4-VCA二聚體氧鎓離子經(jīng)還原產(chǎn)生苦味物質(zhì)四羥基苯基丁烯(化合物4)。4-VCA二聚體氧鎓離子的不飽和邁克爾系統(tǒng)與其另一個(gè)1,2-二羥基苯的鄰位發(fā)生分子內(nèi)閉環(huán)反應(yīng)生成4 種4-羥基苯基林丹(化合物1、2、5、6)。苦味物質(zhì)3,4-DHP-B在閉環(huán)時(shí)與另一分子的4-VCA-H+縮合生成苯基林丹(化合物9a和9b)。苯基林丹1和苯基林丹2與4-VCA-H+聚合生成4-乙烯基兒茶酚三聚體(化合物7和8)。化合物7、8、9為6-羥基苯基林丹的同分異構(gòu)體(表2)[37]。

表 2 多羥基苯基林丹的苦味閾值[37]Table 2 Human bitter recognition thresholds of multiply hydroxylated phenylindanes[37]
多羥基苯基林丹具有強(qiáng)烈持久的苦味,其苦味閾值為32~178 μmol/L,苦味特征類似于深度烘焙的意式濃縮咖啡。與綠原酸內(nèi)酯不同,隨著烘焙溫度升高,多羥基苯基林丹類化合物總含量不斷增加。研究發(fā)現(xiàn)當(dāng)烘焙溫度從190 ℃升高至280 ℃時(shí),多羥基苯基林丹類化合物質(zhì)量濃度由0 μg/L增加至452.6 μg/L[9]。Mancini等[41]研究發(fā)現(xiàn)多羥基苯基林丹化合物能夠抑制β-淀粉樣蛋白和Tau蛋白聚集,降低阿爾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發(fā)病風(fēng)險(xiǎn);Fukuyama等[42]發(fā)現(xiàn)苯基林丹能夠降低黃嘌呤氧化酶的活性,起到抑制痛風(fēng)的作用。
2.3 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
咖啡生豆中多糖質(zhì)量分?jǐn)?shù)為35%~45%,蛋白質(zhì)量分?jǐn)?shù)為12%。‘阿拉比卡’咖啡豆中蔗糖質(zhì)量分?jǐn)?shù)約10%,‘羅布斯塔’咖啡豆中約為3%~7%,具備美拉德反應(yīng)的發(fā)生條件。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又稱類黑精,是一類結(jié)構(gòu)復(fù)雜、棕褐色含氮化合物,占咖啡豆干質(zhì)量的25%[43]。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生的苦味物質(zhì)主要為哌嗪、呋喃、吡咯類等非揮發(fā)性的雜環(huán)化合物[39]。
2.3.1 2,5-二酮哌嗪
2,5-二酮哌嗪類化合物,又稱環(huán)二肽,是食品中常見的苦味物質(zhì),由美拉德反應(yīng)或多肽受熱降解產(chǎn)生。自然界中2,5-二酮哌嗪類化合物一般由L-氨基酸縮合環(huán)合形成,其苦味閾值跨度較大,為190~1 280 μmol/L[7]。在10~50 mg/L下,該物質(zhì)呈現(xiàn)苦澀味、金屬味和鮮味。研究發(fā)現(xiàn),2,5-二酮哌嗪對(duì)其他苦味物質(zhì)如可可堿等具有協(xié)同增強(qiáng)的作用[44]。2,5-二酮哌嗪類化合物的苦味與其環(huán)狀結(jié)構(gòu)和含有的疏水性氨基酸的數(shù)量和種類有關(guān)。通常苦味會(huì)隨著疏水氨基酸數(shù)量的增加而增強(qiáng),Ney[45]建立了Q值原則,即以氨基酸鏈從乙醇相轉(zhuǎn)移到水相所需要的自由能為Q值,發(fā)現(xiàn)在分子質(zhì)量小于6 000 kDa的多肽中,Q值大于1 400 kcal/mol的多肽為苦味肽,Q值小于1 300 kcal/mol的多肽為非苦味肽。例如,苯丙氨酸本身帶有微弱苦味,但當(dāng)其氨基末端和羧基末端分別被乙酰基和乙氧基修飾后,相應(yīng)肽的苦味會(huì)大大加強(qiáng)[46]。然而,Q值原則未考慮多肽空間參數(shù)對(duì)苦味的影響,苦味與特定氨基酸是否存在及其空間結(jié)構(gòu)有關(guān),只有當(dāng)側(cè)鏈骨架上含有3 個(gè)以上的碳時(shí)才能產(chǎn)生苦味[47]。另外TAS2Rs空腔壁具有疏水結(jié)合區(qū),苦味肽具有結(jié)合位點(diǎn)(binding unit,BU)以及刺激位點(diǎn)(stimulating unit,SU),只有BU與SU兩者同時(shí)存在且與TAS2Rs結(jié)合時(shí)才能產(chǎn)生苦味[48]。圖2為苦味肽與TAS2Rs結(jié)合的示意圖,2,5-二酮哌嗪BU和SU之間的距離為0.41 nm,能夠作用于TAS2Rs空腔(直徑1.5 nm)的底部,刺激苦味產(chǎn)生。

圖 2 苦味肽與TAS2Rs結(jié)合的示意圖[49]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binding of bitter peptide to TAS2Rs[49]
2.3.2 5-羥甲基糠醛
5-羥甲基糠醛(5-hydroxymethylfurfural,5-HMF)由焦糖化或美拉德反應(yīng)生成。果糖或葡萄糖在酸性條件下加熱分解脫去三分子水后生成5-HMF;另外還原糖與氨基酸首先生成Amadori重排產(chǎn)物,Amadori重排產(chǎn)物在1、2位烯醇化,消去C3位的羥基,與水生成3-脫氧已酮糖,最后脫水形成5-HMF[50]。咖啡豆中5-HMF的含量為0.452~6.27 mg/g[51],苦味閾值為1 280 μmol/L。綠原酸可通過降低體系pH值和增強(qiáng)己糖脫水促進(jìn)5-HMF生成[52]。由于5-HMF在體內(nèi)的代謝產(chǎn)物磺酸氧甲基糠醛和5-氯甲基糠醛具有致癌性[53],并且咖啡中5-HMF含量隨烘焙程度加深而增加,因此,5-HMF被認(rèn)為是咖啡中的內(nèi)源污染物[54]。
美拉德反應(yīng)生成的呋喃類化合物苦味閾值為100~537 μmol/L,呋喃衍生物糠醇苦味閾值為190 μmol/L,脯氨酸和碳水化合物形成雙吡咯烷酮和吡咯烷酮己糖還原酮,苦味閾值分別為20 μmol/L和40 μmol/L[55]。此外,在加熱條件下,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還可與綠原酸反應(yīng)產(chǎn)物發(fā)生反應(yīng),生成新的苦味化合物。Kreppenhofer等[56]發(fā)現(xiàn)綠原酸受熱產(chǎn)生的二羥基苯酚/三羥基苯酚能夠與糠醇反應(yīng)生成苦味物質(zhì)呋喃-2-甲基苯酚,其苦味閾值為100~537 μmol/L。
總體來看,在中度烘焙過程中,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主要來自綠原酸內(nèi)酯和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而對(duì)于深度烘焙咖啡,起決定性的苦味物質(zhì)更多來自苯基林丹類和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
3 咖啡苦味物質(zhì)的鑒定方法
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鑒定方法主要為將理化儀器分析與感官分析相結(jié)合的方式。圖3為咖啡中新的苦味物質(zhì)鑒定流程。

圖 3 咖啡中新的苦味物質(zhì)鑒定流程Fig. 3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new bitter substances in roasted coffee
3.1 理化鑒定方法
3.1.1 模型烘焙實(shí)驗(yàn)
針對(duì)咖啡提取物中苦味物質(zhì)種類較多,部分苦味物質(zhì)含量較低而無法檢測(cè)分析等問題,實(shí)驗(yàn)過程中以某種苦味物質(zhì)的假定前體為原料,模擬咖啡烘焙條件,將形成的烘焙產(chǎn)物進(jìn)行分離鑒定,并與真實(shí)咖啡飲料中的苦味物質(zhì)進(jìn)行比對(duì)。模型烘焙實(shí)驗(yàn)有助于判斷苦味物質(zhì)產(chǎn)生的來源和反應(yīng)途徑。Kreppenhofer等[56]將呋喃衍生物(糠醇、呋喃-2-醛和5-羥甲基呋喃-2-醛)與二羥基苯酚、三羥基苯酚分別混合后烘焙,并用液相色譜-串聯(lián)質(zhì)譜(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LC-MS/MS)及1D/2D核磁鑒定烘焙產(chǎn)物,共檢測(cè)出10 種新的苦味化合物,經(jīng)對(duì)比,其中4 種能夠在咖啡飲料中檢測(cè)出,因此判斷該4 種化合物為咖啡中的苦味物質(zhì),并確定該種苦味物質(zhì)是由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與綠原酸烘焙產(chǎn)物在加熱條件下生成。
3.1.2 儀器分析
液相色譜是咖啡因、葫蘆巴堿及綠原酸的主要測(cè)定方法[57]。邱碧麗等[58]用高效液相色譜同時(shí)測(cè)定咖啡中綠原酸、葫蘆巴堿、奎寧酸和咖啡酸的含量,綠原酸和咖啡酸的檢測(cè)波長為330 nm,葫蘆巴堿和奎寧酸檢測(cè)波長為210 nm,結(jié)果表明,綠原酸、葫蘆巴堿、奎寧酸、咖啡酸在0.499 5~4.995 0 μg/mL質(zhì)量濃度范圍內(nèi)與峰面積線性關(guān)系良好(r為0.999 98~1.000 00),加標(biāo)回收率為93.28%~97.46%。Czerwonka等[59]用反相液相色譜在檢測(cè)波長285 nm、柱溫45 ℃條件下,用體積分?jǐn)?shù)4.4%甲醇-乙酸(10∶1,V/V)進(jìn)行等濃度洗脫,用C18柱檢測(cè)烘焙咖啡中的5-HMF含量,受咖啡豆品種、烘焙時(shí)間、烘焙溫度影響,不同品牌烘焙咖啡豆中5-HMF含量差異較大,最低含量為85.9 mg/kg,最高含量1 574.4 mg/kg,平均含量為347.6 mg/kg。
質(zhì)譜是分析天然產(chǎn)物分子結(jié)構(gòu)最靈敏可靠的方法之一。LC-MS是分離、分析復(fù)雜有機(jī)混合物的有效手段[29]。然而化合物通過LC-MS分析所得到的質(zhì)譜圖通常只給出分子離子峰及極少的碎片離子峰。MS/MS技術(shù)能夠?qū)σ患?jí)質(zhì)譜選出的離子進(jìn)行進(jìn)一步碰撞誘導(dǎo)解離[60],提高了檢測(cè)靈敏度和選擇性。Frank等[61]在多反應(yīng)監(jiān)測(cè)模式下進(jìn)行LC-MS/MS檢測(cè),證實(shí)了咖啡飲料中3-咖啡酰奎寧、4-咖啡酰奎寧等綠原酸內(nèi)酯的存在。Kreppenhofer等[56]用LC-MS/MS確定了咖啡飲料中4-呋喃-2-亞甲基苯-1,2-二醇、4-呋喃-2-亞甲基-5-甲苯-1,2-二醇和3-呋喃-2-亞甲基-6-甲苯-1,2-二醇等化合物為咖啡中新的苦味物質(zhì)。
高速逆流色譜(high-speed countercurrent chromatography,HSCCC)技術(shù)是一種新型液-液分離技術(shù),由于不采用固體支持物,因此被廣泛應(yīng)用于天然產(chǎn)物的分離[62]。Kaiser等[63]使用HSCCC法分離出毫克級(jí)的綠原酸內(nèi)酯,并用一維和二維核磁共振鑒定了3-咖啡酰奎寧、4-咖啡酰奎寧和5-咖啡酰奎寧的結(jié)構(gòu)。張曉霞[64]采用HSCCC法分離咖啡豆中的綠原酸,得到最佳分離條件為V(甲醇)∶V(乙酸乙酯)∶m(硫酸銨)∶V(去離子水)=3.2∶3∶1∶7,轉(zhuǎn)速800 r/min,分離溫度25 ℃,流動(dòng)相速率2 mL/min,綠原酸保留時(shí)間為236~296 min。
3.2 感官分析法
味覺感官分析是基于評(píng)價(jià)人員的味覺感官系統(tǒng),針對(duì)特定樣品進(jìn)行分析型或嗜好型鑒定的方法。該方法以心理物理學(xué)為理論依據(jù),一般有味覺稀釋、標(biāo)度法及閾值檢驗(yàn)3 類方法。
3.2.1 味覺稀釋法
味覺稀釋法主要用于確定食品中苦味物質(zhì)的味覺強(qiáng)度,該方法常與分離、提純、鑒定等操作結(jié)合,具體方法如下:首先將食品中各組分用液相色譜分離、收集并提純,冷凍干燥后將提純的化合物連續(xù)稀釋,建立濃度梯度;評(píng)價(jià)員被要求評(píng)估味道質(zhì)量,用三點(diǎn)檢驗(yàn)法分析樣品,將樣品與空白樣品之間最小區(qū)別水平時(shí)的稀釋倍數(shù)定義為苦味稀釋因子,隨后對(duì)具有較大苦味因子的組分用高效液相色譜、質(zhì)譜及核磁進(jìn)行結(jié)構(gòu)鑒定[65]。Frank等[37]用高效液相色譜分離咖啡酸烘焙產(chǎn)物,得到24 個(gè)分離組分,用味覺稀釋法對(duì)該24 個(gè)組分進(jìn)行感官評(píng)價(jià),再用半制備反相高效液相色譜將苦味稀釋因子最高的8 個(gè)組分進(jìn)行分離,確定咖啡酸烘焙后產(chǎn)物為多羥基苯基林丹類物質(zhì)。該方法能夠從復(fù)雜物質(zhì)中提取到主要苦味物質(zhì)的味覺特性,但因分離提純操作大多需要使用化學(xué)試劑[66],因此利用此法需嚴(yán)格按照標(biāo)準(zhǔn)操作規(guī)范進(jìn)行。
3.2.2 標(biāo)度法
標(biāo)度法是指對(duì)不同濃度的溶液做苦味分析,根據(jù)需要可設(shè)定一定的標(biāo)度,即通過能表述程度的量化詞來描述苦味強(qiáng)度[67]。Frank等[24]依次用戊烷、乙酸乙酯、氯仿和水提取咖啡成分,以25 mmol/L的咖啡因作為最強(qiáng)的苦味對(duì)照(5 分),用標(biāo)度法對(duì)提取物進(jìn)行苦味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如表3所示。其中咖啡中非揮發(fā)性成分苦味強(qiáng)度為4 分,揮發(fā)性成分苦味強(qiáng)度為0 分,乙酸乙酯提取物苦味強(qiáng)度為3.5 分,水提物苦味強(qiáng)度為0 分,因此判斷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主要為疏水性非揮發(fā)物。與味覺稀釋法相比,標(biāo)度法較適合于粗提物的感官鑒定。

表 3 標(biāo)度法對(duì)咖啡中成分的苦味強(qiáng)度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24]Table 3 Yields of fractions isolated from coffee beverage and their bitterness intensity evaluated by scaling method[24]
3.2.3 閾值檢驗(yàn)
閾值檢驗(yàn)通常以評(píng)價(jià)員感知到的樣品最低濃度為察覺閾,并在此基礎(chǔ)上確定絕對(duì)閾值范圍[68]。常用的確定察覺閾值的方法包括順序檢驗(yàn)法和三點(diǎn)檢驗(yàn)法。采用順序檢驗(yàn)法時(shí),首先讓評(píng)價(jià)者用清水漱口,然后由測(cè)試者用滴管向其舌面快速滴加5 滴測(cè)試液,并要求評(píng)價(jià)者在1 min內(nèi)作出味覺判斷。如果評(píng)價(jià)者不能識(shí)別,則再用相同溫度清水漱口,增加測(cè)試液濃度,直至察覺苦味。此濃度即為該評(píng)價(jià)者在此溫度下的苦味察覺閾[69]。采用三點(diǎn)檢驗(yàn)法時(shí),每次同時(shí)呈送給評(píng)價(jià)員3 個(gè)樣品,其中2 個(gè)為水,即空白對(duì)照,第3個(gè)為苦味樣品。預(yù)先告知評(píng)價(jià)員3 個(gè)樣品中有2 個(gè)相同,并要求選出不同的樣品。以評(píng)價(jià)員能識(shí)別的苦味最低濃度為該物質(zhì)的察覺閾。
4 苦味對(duì)咖啡偏好度的影響
目前個(gè)體對(duì)食物的偏好性選擇有2 種假設(shè)性機(jī)制:一種是個(gè)體通過經(jīng)驗(yàn)性行為而習(xí)慣某種味道,進(jìn)而增加對(duì)該種味道的偏好性[70],例如,歐美消費(fèi)者偏好咖啡飲料,中國消費(fèi)者偏好茶飲料;另一種是個(gè)體的聯(lián)想學(xué)習(xí)能力會(huì)將食物與獲取食物后獲得的感官快感或功效相結(jié)合,前者稱為享樂性機(jī)制,后者稱為激勵(lì)價(jià)值機(jī)制,進(jìn)而增強(qiáng)對(duì)該種食物的嗜好性。例如,吃甜食以后產(chǎn)生的愉悅感為享樂性機(jī)制;有神經(jīng)興奮需要或者壓力大的人會(huì)選擇喝更多咖啡為激勵(lì)價(jià)值機(jī)制[71]。另外苦味食品的嗜好性也會(huì)受個(gè)體基因差異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咖啡的偏好度受環(huán)境因素(61%)和基因因素(39%)共同影響[72]。對(duì)6-N-丙基硫脲嘧啶(6-N-propylthiouracil,PROP)的口腔感知強(qiáng)度是一種基因介導(dǎo)的個(gè)體口腔感覺變異指數(shù),PROP敏感者比PROP不敏感者有更強(qiáng)的味覺敏感度。PROP敏感度較高的人群對(duì)純咖啡溶液和咖啡因的偏好度低[73],二者呈弱相關(guān)性。TAS2R38作為一種TAS2R基因,通過單核苷酸多樣性會(huì)產(chǎn)生2 種常見的單倍型——PAV和AVI;對(duì)118 名60 歲以上婦女研究發(fā)現(xiàn),AVI/AVI型受試者比PAV/PAV型受試者飲用咖啡的頻率更高[74]。因此,對(duì)苦味食物的嗜好性可能會(huì)受生活習(xí)慣、環(huán)境、激勵(lì)價(jià)值機(jī)制及基因等因素的影響。
中外消費(fèi)者對(duì)于咖啡苦味的嗜好性具有一定差異性。胡雙芳等[75]研究了不同品種咖啡豆的化學(xué)組分,發(fā)現(xiàn)咖啡感官評(píng)分與苦味物質(zhì)咖啡因、葫蘆巴堿含量呈負(fù)相關(guān)。翟曉娜等[76]研究我國青年消費(fèi)者群體對(duì)不同方式處理的咖啡樣品的喜好度,發(fā)現(xiàn)糖與奶粉能提高對(duì)咖啡的喜好度。Hu Xiaojia等[77]對(duì)每周喝咖啡3 次以上、年齡19~65 歲的中國和韓國消費(fèi)者進(jìn)行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咖啡樣品苦味越濃消費(fèi)者越不喜歡。因此,國內(nèi)咖啡消費(fèi)者對(duì)苦味與咖啡嗜好的關(guān)系可能呈現(xiàn)負(fù)相關(guān)。Geel等[78]將南非咖啡消費(fèi)者分為4 種消費(fèi)群體:純咖啡愛好者(23%)、咖啡混合飲料消費(fèi)者(30%)、普通咖啡消費(fèi)者(37%)和不嚴(yán)重咖啡消費(fèi)者(10%),發(fā)現(xiàn)純咖啡愛好者更喜歡純咖啡樣品的澀味、苦味、烤味、堅(jiān)果味和濃郁的味道;咖啡味較低、但甜味較高的速溶咖啡是咖啡混合飲料消費(fèi)者的首選;普通咖啡消費(fèi)者似乎是出于習(xí)慣而飲用咖啡,對(duì)咖啡的特殊感官特性關(guān)注度較小。生活習(xí)慣和飲食文化的差異會(huì)影響中外消費(fèi)者對(duì)于咖啡苦味的嗜好性,而基因差異產(chǎn)生的影響并不清楚,需進(jìn)一步探究。
5 結(jié) 語
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主要由生物堿、綠原酸烘焙產(chǎn)物以及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組成。生咖啡豆中咖啡因和葫蘆巴堿為其主要苦味物質(zhì)。在中度烘焙過程中,咖啡中苦味物質(zhì)可能主要由綠原酸內(nèi)酯和美拉德產(chǎn)物組成,而深度烘焙過程中,起決定性的苦味物質(zhì)可能為多羥基苯基林丹類和美拉德反應(yīng)產(chǎn)物。目前對(duì)咖啡中新的苦味物質(zhì)的鑒定方法主要為感官分析與儀器鑒定相結(jié)合。
咖啡中某種具體的苦味物質(zhì)對(duì)咖啡感官嗜好性的影響尚不清楚。一方面,烘焙產(chǎn)生的苦味物質(zhì)種類繁多,并非所有的苦味物質(zhì)都能被精準(zhǔn)檢測(cè)到;另一方面,咖啡因雖然本身具有苦味,但其提神醒腦的功能能夠降低人對(duì)咖啡苦味的排斥。苦味物質(zhì)雖然能致人產(chǎn)生不悅,但苦味也是咖啡的重要特征,經(jīng)驗(yàn)性行為或者激勵(lì)價(jià)值機(jī)制能夠增加消費(fèi)者對(duì)苦味的喜好度,另外中國消費(fèi)者對(duì)于咖啡選擇的偏好性是否受基因因素的影響并不清楚,需要進(jìn)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