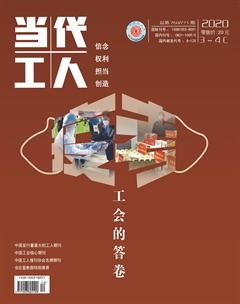炸裂志
張章



站上撫順東部東西長5.7公里、南北寬1.9公里的礦坑邊緣,一聲巨響后往下遠望,猶如螞蟻大小的電鏟、電力機車在一排排灰綠色的巖層前忙碌著,源源不斷產出的油頁巖,被運到地面,送至車間經加工煉制成油……
此時,一輛載滿的班車從坑底盤桓至坑口,向車間緩緩駛去。早6點半至下午4點,掌握從石頭里“炸”出寶藏絕技的神秘隊伍——撫順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十一廠爆破車間的爆破工,結束了忙碌的爆破工作。
炸裂,嚴寒酷暑
“今天的著裝,有點兒搶眼。”
10月初的天氣,依舊很暖,可身處露天礦坑底,氣溫至少“下降”10攝氏度,再加上四處沒有遮擋,冷風呼嘯,穿棉褲、棉襖都不為過。這天,陰雨將至,從6點30分站上坑底的作業面,等待接卸火工品(炸藥)的3名爆破工,好不容易熬過兩個小時后,冷得實在有些扛不住,把準備包火工品的大塑料袋套在身上。看著穿著“裙子”的彼此,他們邊打趣邊用力地抽吸凍得不透氣的鼻子。
“爆破工是苦差事,等接卸的爆破工則苦上加苦。”組長吳英適坦言,坑里不可以用電子設備,又沒個落腳的地方,若當天的火工品被排在后期送達,等待三四個小時是家常便飯。爆破工能做的,除了原地站立,就是盡可能地多穿、多活動胳膊腿。
最難挨的要屬盛夏。“如火的太陽炙烤著礦坑的每一個角落,空氣都凝固了,一絲風都沒有,雙腳像踩上了煎鍋,滾燙”“地面氣溫接近50攝氏度,剛灑了水的地面,轉眼就干了,流下的汗,落在石頭上很快被蒸發”……大家七嘴八舌地描述著,黝黑的臉頰微微揚起,好似在訴說自己的功績。
所言非虛,這確實就是爆破工日常工作的生動寫照。
到達,無聲的命令
在撫順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十一廠爆破車間,共有43名爆破工,清一色的男兒郎,年齡最大的退休返聘,年齡最小的33歲,他們分成4組,倒班制上工。
每個作業的班組內部,又細分出輪班制:1人將每天需要使用的火工品運上火車,跟車押送;因為運火工品的鐵路運輸線繁忙,不便準確預估到達作業面的時間,所以需要2人-3人在6點30分左右,到達作業面等火工品到來進行卸貨;其余工人,在火車即將駛入作業面前到達作業面,而后就是全員一起做爆破前的下藥、鋪雷管等工作了。
今天還算幸運,9點剛過,爆破所需的火工品就已運送到指定地點。在吳英適的帶領下,組員各負其責。吳英適挨個測量孔深,每測量好一個孔深,隨即就會有一名隊員扛著火工品走過來,放到指定位置,另一名隊員手里拿著導爆管雷管走過來,進行裝藥操作。他先是將雷管干線理順,待長度足夠用之后,再蹲下身子,加工起爆藥包,而后彎著腰把炸藥一點點放入孔內,直至放入孔底。
“午飯?如果預判下午1點前能完成爆破,就回車間吃,如果不能,車間會把盒飯送到作業面,大家或站或蹲,扒拉一口飯,然后接著作業。”副總工程師兼爆破車間主任周洪波介紹。
爆破工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工作節奏,也早已適應了這樣的工作狀態。沒有人抱怨,沒有人喊苦叫累,更無需召喚,無需安排,只要火工品到達現場,就是無聲的命令。只見隊員走到各自所負責的區域,立刻忙碌起來。
巨響,最大的意義
“大多數人的生活,上班下班,按部就班,平淡無奇,我們可不一樣,我們是戰天斗地,又驚天動地。”
的確,每天最少一次的爆破聲,不僅代表著安全完成爆破、當天工作的結束,更嵌入骨髓,成為他們生活中最大的意義,甚至讓身處城市川流不息的車流和五色斑斕的霓虹之外的他們,多了幾分踏實和堅定。
“讀技校學的是駕駛大型設備車,因為自己暈車,實在無法操作,只能轉行。”就這樣,吳英適成了車間年紀最小的爆破工。他白天看隊友爆破作業,晚上學習爆破知識,爆破技術不斷進步,職位在不斷高升,成了車間最年輕的班組長。爆破遇到難題時,他總能提出想法,讓老工友很是贊賞與欽佩。
“爆破是個特種行業,很好。不干這個,還能干啥?”他對這份工作有著隱隱的驕傲。
當然,感到自豪和驕傲的,還有所有的爆破工。僅2019年上半年,在全體干部員工的共同努力下,爆破車間不僅實現了創效540余萬元的佳績,還贏得了客戶的一致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