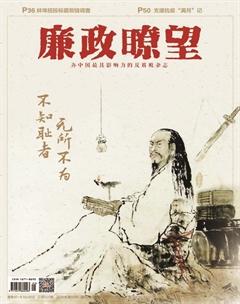古代“吹哨人”的命運
木杉
福建泉州開元寺內,有東西二塔,西邊仁壽塔的須彌座上,有一尊托塔力士浮雕,頭頂石塔,將右手拇指、食指吮于口中,鼓著腮幫子,作出吹哨狀。
相傳明朝萬歷年間,泉州發生了強地震,波及城內每一個角落,但吹哨者穩穩托負石塔,還不停發出報警的哨聲,滿城百姓得以平安脫險。
這尊浮雕,鐫刻于南宋時期,已歷經近800年的風雨洗禮,當年的工匠應該不會想到,這個“吹哨人”的形象能在后世的特殊時期引人矚目。
古人怎樣“吹哨”?
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先把視線放在現代。“吹哨人”這個概念其實是個舶來品,水門事件曝光后,美國國會立法通過《吹哨人保護法案》。這部法律鼓勵公民(包括公職人員)通過參與到旨在維護社會公正的行動中,特別是公職人員在其履職過程中,發現存在貪腐、影響公共利益、國家安全的行為,有權以告密(包括向媒體報料)的方式進行檢舉。
再看我國古代,那時候當然沒有成形的媒體,“吹哨人”反映問題的范疇、渠道和效率都與當今不可同日而語,但其方式也可謂五花八門。
最常見的是對著一國之君“吹哨”,常見于對君主的施政綱領、領導方式等進行預警,但“吹哨”都是在“眾人裝醉、唯我獨醒”的情況下進行的,甚至要豁出命去,需要更強大的內心。
此類故事有很多,比如漢武帝追求驕奢淫逸的生活,不免勞民傷財。有次他準備建一個大規模的林苑供自己打獵和閑暇游樂,一眾臣子紛紛點贊,唯獨東方朔敢站出來否決——雖然這個“哨”沒吹響,因為漢武帝并沒有改變主意,卻十分欣賞東方朔。

泉州開元寺仁壽塔西側的“吹哨人”雕像。
在個別情況下,普通百姓也能成為“吹哨人”。北宋年間,山東青州一個名叫趙禹的人,給朝廷寫了一封信,中心思想只有一個:西北的李元昊一定會造反,請朝廷早做準備。至于他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作為普通百姓,更普遍的“吹哨”方式是政治民謠。《漢書》有言:“言上號令不順于民心,則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正因如此,先秦時期的“采詩觀風”制度,在后世也以不同的形式進行了傳承。比如清代有民謠“官屋漏,官馬瘦”,反映的正是官員漠視公共利益和財物的風氣。
這種政治民謠,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民眾的意愿,統治者自然也會有所重視,而各級地方官員、監察官員也會上奏影響力大的民謠,一些官員還會就當時流傳的民謠進行議事。
美國傳教士杜列圖曾描述了福建當地關于祭祀瘟神“五帝”的傳統,一名高官乘轎子經過城里的大街時正遇上迎五帝的游行隊伍,游行者非但沒有給官員的轎子讓路,反而要求官員的轎子后退,或先避到路邊。在神話世界中,五帝的地位自然是要高過俗世的官員。
君主對“吹哨人”的態度
瘟神信仰在各地根深蒂固,但只有得到皇帝加封認可的神靈才能算是“正神”,所以五帝仍是邪神,故而屢次被朝廷毀禁。不過,朝廷卻將處理相關事宜的權力下放給了地方官員,而地方官員原本就與地方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往往只有在發生瘟疫,或者存在聚眾鬧事、危及自身政績時,才會采取措施。
對于實實在在的“吹哨人”,結果當然有好有壞。李元昊造反前,宰相呂夷簡接到趙禹信件的時候很苦惱,他不是不知道情況,但是他對皇帝和對百姓的口徑都是,李元昊的行為,可防可控。
為了防止趙禹再“吹哨”,呂夷簡做出了一個最簡單的決定:以“狂言”的名義為其定罪,然后把他發配到了建州(今福建建甌)。后來,李元昊稱帝,創立了西夏王朝,公開跟北宋叫板,直到那時全國上下才知道,李元昊這個人既不可防、也不可控。
唐朝名將李靖原本也只是一名小官吏,他看到自己的領導李淵招兵買馬,料到李淵會造反,就想去江都(今揚州)給隋煬帝“吹哨”。但為了不引起李淵的懷疑,就假裝犯法,被朝廷治罪,讓人把自己押進囚車去面圣。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囚車剛到長安(今西安),李淵已經開始行動,天下大亂,路已經被截斷,信送不出去。后來李靖被李淵活捉,還被發現企圖給皇帝送信。好在李淵賞識他的才識和膽氣,并沒有殺他,這才有了后來一代名將的故事。
西周末期,周厲王暴虐無道。百姓怨聲載道。一次,老臣召公實在看不下去了,就提醒周厲王,這樣下去可不得了啊。厲王一聽覺得老被民眾議論確實不好,就馬上調來軍隊,傳旨“誰敢在背后說我的壞話,就給我抓起來,開刀問斬!”
為了監控百姓言論,周厲王專門請來一個巫師,但凡發現誰宣講了對天子不利的話,格殺勿論。這么一來,百姓別說“吹哨”,話都不敢隨便說了,熟人在路上碰了面,都只能互相遞個眼色。
召公見天子如此,只能繼續“吹哨”勸誡,奈何周厲王仍舊我行我素。三年后,百姓終于起來造反,把他趕出了京城。
民眾的期盼
對于“吹哨人”來說,意見建議被采納甚至形成制度法規是再理想不過的結局。盛行于唐朝的告密之風,成為黨同伐異的手段,造成了很多無辜冤案。直到宋仁宗時期,監察御史陳旭等看形勢不對,就對皇帝“吹哨”,指斥繳納私人往來信件、并以之定罪等做法,引發了朝廷之中揭人陰私、相互告發的惡劣風氣,并請嚴禁此類行為,“仁宗從之”。
此后,有人還拿著說一些大臣壞話的書信去給諫官韓絳打小報告,韓絳不敢隱瞞,告知皇帝,但仁宗叫他拿回家燒掉。幾年后,仁宗又采納了殿中侍御史呂誨的建議,頒布詔書,告誡那些打小算盤的人。到高宗時,還發生了一次有9個人因為利用同事的私人信件搞文字獄被革職懲處的案例。
但在古代,幾句話就帶來變革的典故并不多見,有些事主政者自己也搞不明白。在距離我們較近的清朝,京城常鬧天花,統治者畏之如虎,順治帝和康熙帝都下過嚴令:“凡民間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傳染也。”
康熙年間,有一個名叫趙開心的御史,給這種狀況吹了“哨”:城中居民得了瘟疫,往常只驅逐、不救助,逼得人家露宿在外,兒女無人照顧,飽受饑寒之苦。以后應該在京城四郊各劃出一個村莊,讓感染者集中居住,官府給予補貼,如果有人拋棄兒女,則由官府嚴加懲辦。康熙聽取了這個建議,但是官府財力有限,基層官員執行力又太差,只搞了一年就恢復了老辦法。
所以有時候古代人信仰神靈也是無奈之舉,前面提到的瘟神五帝,在成書于元明之際的《三教搜神大全》記載中,是五個天外來客,可以在人間散播瘟疫,并以此超能力恐嚇皇帝。但民間流傳至今的卻是另一種敘事——五帝生前只是五個普通書生。
古時人們相信,如果鬼怪向水井中投放引發瘟疫的毒藥,人們在接觸之后便會感染患病。于是五人決定放棄事關前途的考試,分別把守城中水井,勸阻人們不要取水,提防瘟疫。然而,人們卻認為他們是在傳播謠言,惑亂人心。于是,五人只好喝井水自證,直到死后人們才相信,瘟鬼井中投藥確有其事,一場威脅全城的瘟疫得以消弭。五位烈士被人銘記,人們為報恩情,建廟祭祀。
而比五帝影響力更大的瘟神溫瓊,在民間傳說中和五帝的境遇如出一轍,同樣是投井后被水中瘟藥毒死,可見,當瘟神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