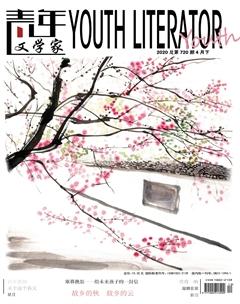郁達夫前中后期小說中的零余者形象流變
摘 ?要:本文從文本出發,結合作者的個人經歷和社會背景,概括升華出不同時期零余者的形象內涵。研究發現前期的零余者形象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中期的零余者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后期的零余者面對精神困境,選擇了不同的自我救贖道路。
關鍵詞:郁達夫;零余者;《沉淪》
作者簡介:魏昕(2001.6-),女,滿族,遼寧大連人,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12-0-02
郁達夫作為現代文學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創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前期從郁達夫在日本留學到1922年回國,這一時期,其作品多描寫理想破滅的知識分子的頹廢。中期從郁達夫回國到1925年他到廣州參與革命,這一時期的作品多表現現實壓迫下,人生的苦悶和社會的苦悶。后期從1926年底回到上海到1935年小說創作結束,雖然一部分作品流露出郁達夫因找不到中國的出路而產生的絕望和悲痛,但另一部分作品也寄托了作者對田園生活的向往之情。郁達夫在不同時期塑造了一系列經典的“零余者”形象,文章旨在通過探究不同時期的零余者心態,深化對郁達夫創作的認識。
一、早期零余者:悲觀的浪漫英雄
郁達夫青年時期曾留學日本,在此期間接觸到了浪漫主義文學。他曾閱讀過一千多部俄德英日法的小說。在這些作品中,歐洲浪漫主義作家,如:華茲華斯,盧梭,歌德……的作品,都深受郁達夫的喜愛。受他們的影響,郁達夫早期創作的抒情主人公--零余者也帶有浪漫主義色彩。
郁達夫筆下早期的零余者形象和歐洲浪漫主義維特型人物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他們的人格往往充滿矛盾:自命不凡,對社會的庸人感到厭倦,可是又敏感憂郁,常常自卑自賤;憂國憂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可是缺乏斗志,只是馳于空想,騖于虛聲,從不付諸于行動,只是自我頹廢,逐漸地向命運屈服。
關于近代歐洲浪漫主義主人公,有評論家曾指出:它們大致可分為拜倫式英雄和維特型人物兩種類型……所謂維特型人物也與社會處于對立之中,他們把個人的權利個人的內在活動看成比外在的行為標準與道德習俗更為重要,他們的痛苦來自“人的激昂熱情和社會的規則、法律之間的矛盾”。但他們意志薄弱,神經纖敏,多愁善感,帶有一種普遍的憂郁癥,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尋找避難所。[1]
《沉淪》(1921.5)當中,主人公“他”身世可憐,造就了他敏感自卑的性格;年少時反抗專制,卻受到了社會的壓迫;留學日本,卻因祖國的貧弱受到屈辱。他的人生迷茫痛苦,理想逐漸破滅,感到孤冷。于是他親近自然,將大自然作為自己的避難所;讀喜歡的文學書,以書為友;渴望得到女人的愛情,這其中既包括精神上的理解也包括肉體的滿足,可這些他都得不到,只能壓抑自己的性欲。這幾種自救的辦法,卻使他越來越孤冷,“憂郁癥愈鬧愈甚”,最后只能自殺。《銀灰色的死》(1920)的主人公Y君留學日本,妻子因肺病在孤獨中慘死,他無家可歸;喜歡酒館里的女孩靜兒,卻因自己的窮困只能看著靜兒嫁人,愛而不得。他冷清孤寂,無人理解。于是他拼命喝酒,一面消解自己的哀傷,一面復仇。最后腦溢血而死。《南遷》(1921.7)中伊人所想要的“名譽,金錢,婦女……什么也沒有”[2],他只能用“心貧者福矣”的宗教信仰來麻痹自己,最后因肺炎而成為將死之人了。《茫茫夜》(1922.2)于質夫耿介正直卻四處碰壁,他的愛欲無法得到滿足,便愛上同性吳遲生,到妓院找妓女,甚至做出買針買帕刺血的可笑行為。
郁達夫的作品帶有個人自敘傳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正與他本人的經歷有關。他留學日本十年,對于中國在國際社會所處的地位是很清楚的,《雪夜》(自傳之一章)曾寫“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里所處的地位……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后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3]93郁達夫深愛祖國,然而對于中國的出路,他仍是不知所措的,《蔦蘿集自序》里寫“人家都罵我是頹廢派,是享樂主義者,然而他們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我豈是甘心墮落者?我豈是無靈氣的人?不過看定了人生的運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3]153理想的美好和現實的迷茫,促成了他塑造“無為的理想主義者的沒落[3]149”形象的零余者。
由上可以看出,早期零余者總是受到現實的壓迫,但是并沒有付出實際的行動,進而自身的理想和訴求破滅,于是只能做出病態的行為,而他們種種病態的表現,或是患病自殺,或是沉迷酒色。這正像悲觀的浪漫主義者在面對困境時,往往不會積極的反抗,而是會選擇自我逃避。
二、中期零余者:堅定的人道主義者
1922年,郁達夫回國。這時候他不僅僅是局限于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苦悶與頹廢,而是認為“性的苦悶不就是人生的全部”,要“描寫比性的苦悶還要更重大的人生的苦悶”[3]86。他將個人融入到社會當中去,注重描寫個體在社會的壓迫中所感受到的生的苦悶,包括政治的苦悶,經濟的苦悶。從1922年到1926年,這一時期可以看作是郁達夫創作的過渡期,相應的,郁達夫的零余者形象也有所變化。這一時期的零余者往往會作為留學生歸國,他們懷揣自由平等的理念,只會與政治黑暗,權貴橫行,視知識為糞土的社會產生沖突,但是他們仍然胸懷理想,堅守原則,不肯同流合污,這其中還有的零余者盡管自己生計艱難,卻仍然關心和幫助同樣窮苦的底層人民。
《春風沉醉的晚上》(1923)的“我”失業住到貧民窟,因為衣服的破舊和神經衰弱,只能選擇在春季的夜晚出去散步,可是我依舊會忍著饑餓,等著陳二妹一起吃“我”買的糖食,在我情動時,不去傷害純潔的陳二妹;《薄奠》(1924)中即使“我”貧窮到無力養活自己的家庭,依然會偷偷地給人力車夫一塊銀表,為他燒紙糊地洋車;《秋柳》(1924改作)于質夫沒有看不起卑賤的妓女海棠,卻同情她的遭遇……作者完整地描述了零余者與這些可憐可敬的人從相識,到相熟,到最后相惜的全過程,也許這只是一些小事,蘊含的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
郁達夫創造這樣的零余者形象,正與其中蘊含的人道主義思想有關。他在《蔦蘿行》描寫回國后的感受 “生計問題就逼緊到我的眼前來”[3]216《離散之前》(1923)“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頹風于萬一,然而社會上的勢利,真如草上之風,他們的拼命的奮斗的結果,不值得有錢有勢的人一拳打。”[3]274-275以己度人,他知道在貧民窟、破廟中有“悲哀的男女”“可憐的讀者”。所以他想借零余者和這些窮苦人簡單的關愛“來挽回那墮落到再無可墮落的人心”[3]32。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零余者雖然受到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仍然秉持人道主義精神。
三、后期零余者:自我救贖的精神囚徒
郁達夫將1925年作為自己的一個轉折點,他在《雞肋集》題辭中提到“一九二五年是我頹廢到極點以后焦躁苦悶,想把生活的行程改過的一年……我就和兩三位朋友,束裝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一九二六年年底,遷回上海……這前后卻得到了一種外來的助力,把我的靈夷,把我的肉體,全部都救度了……我現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3]1721925年,郁達夫對于中國的現狀和未來,他仍然是焦躁和苦悶的,然而在他回到上海,寄情山水之時,他卻“得到了一種外來的助力”“得到了光明的去路”。這一系列的轉變也直接體現到了他的創作中,從1926年底他回到上海到1935年他發表最后的小說《出奔》,這十年可以算作郁達夫小說創作的后期。在這十年的作品中,他詳細地展現了五四運動高潮過后三種零余者形象,以及他們的精神困境和精神上所感受到的苦悶,同時也暗示了這些零余者的結局。
其一,零余者理想破滅,逐漸走向死亡。這些零余者和前期和中期的零余者形象差別不大,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延續。《微雪的早晨》(1927)朱雅儒不畏強權,正直善良,卻被軍閥搶走了未婚妻,自己憂郁而死。《楊梅燒酒》(1930)寫留學生懷著滿腔熱血回到祖國,卻是懷才不遇,報國無門。《唯命論者》(1935)像是《蔦蘿行》的延續,小教員李德君為一家的生計而勞苦,最后投河自盡。這些零余者不僅和社會格格不入,家庭關系也十分糟糕。《煙影》(1926)中的文樸,《在寒風里》(1927)的和尚都因自己的貧苦,或是遭到母親的責罵,或是遭到兄嫂的欺凌,有家難歸。他們正是這世上“生則于世無補,死亦于人無損。”[3]216的零余者。
其二,零余者被人性的弱點所打敗,走向墮落。他們不是追求官能的享受,就是心理變得扭曲。《迷羊》(1926)講述了小資產階級王介甫對女戲子謝月英變態的占有欲,以及他和謝月英在南京和上海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二人就似“迷路的羔羊”。《她是一個弱女子》(1932)刻畫了鄭秀岳頹廢,迷茫,痛苦的一生。《出奔》(1935)革命青年錢時英在感受到自己是受到地主之女董婉珍的引誘和經歷到對她厭惡后,竟放火燒了董玉林全家。這些零余者在社會的長期壓迫下,人性異化。
其三,零余者回歸自然,通過自然來滋養個體精神,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郁達夫深受盧梭“人性返歸自然”的思想和傳統儒道中樂于山水,崇尚自然思想的影響,他曾在三十年代的初期,退隱山林,這也可以顯現出郁達夫創作精神的轉變。這一類作品的代表作主要有《東梓關》(1932.9)《遲桂花》(1932.10)《飄兒和尚》(1932.12),其中的《遲桂花》是集大成之作。“我”的老同學翁則生因肺病回鄉隱居,然而病卻莫名的好了,他做了小學教師,寡妹和母親料理家務,一家人在鄉間過著溫馨寧靜的生活;我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對翁蓮的欲情也凈化升華。這時的零余者同樣經歷了生活的苦悶,但他們卻如遲桂花一般,樂觀堅韌的生活,展現了零余者形象中積極的一面。
從悲觀的浪漫英雄,到堅定的人道主義者,再到自我救贖的精神囚徒,零余者形象的流變,與郁達夫的個體生存經驗和外在社會的劇變始終緊密結合在一起。故而,零余者自身也成為了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不同時期心態外現的窗口。
參考文獻:
[1]羅成琰. 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J].外國文學評論,1994(03):116-122.
[2]郁達夫.郁達夫文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86 ,93,153,149,86,216,274-275,32,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