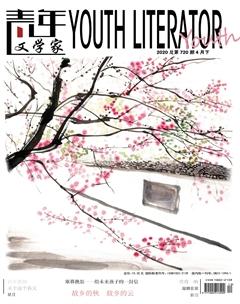淺析唐代說體文的藝術特色
胡睿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12-0-03
許慎的《說文解字》有言:“說者,道也,談說也。”[1] “說”首先是用話來表達的意思,它是一種語言行為;其次,“說”是解釋說明的意思,《文章辨體序說》中闡述了這一點:“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2]例如《墨子》有《經說上》、《經說下》,《漢書·藝文志》記載:《易》有《五鹿充宗略說》,《書》有《歐陽說義》,《詩》有《魯說》、《韓說》等等,都是對經籍的解說;“說”還可以代表言論主張,如:著書立說,這是春秋時期流行于社會上的一種價值觀,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以求“不朽”[3];除此之外,“說”也是用話勸說別人使聽從自己的意見,如戰國策士在各國游說(shui),主陳說自己的政見或主張,以謀官爵。上述“說”的含義都是構成說體文內部的不同形態。
說體文是古代側重于說理的文體樣式之一,可以發表觀點議論說理,也可以是記敘文寫一時之感。徐師曾認為:“說之名,起于《說卦》。漢許慎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4]古代的“說”源于戰國策士游說之詞,“說”比“論”更偏重于講究技巧。戰國時的策士周游各國,向君王講述自己看法,即要“說”得動聽,后期墨家提出“說,所以明也”和“以說出故”,認為推論是說明事物原因和規律性的方法。在寫法上,這類文章不僅注重于推理演繹,還有的是因事而發,抒發作者的感觸,揭示和闡述某一個問題和道理,帶有明顯的雜感色彩,因而論題可大可小,行文靈活多變。
劉勰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5]劉勰這里的“說”雖然是勸諫的行為方式而非文體形式,但“游說”作為說體文的來源之一也表現了其特征。從這里可以看出,說體文作為一種說理的文章,有一定的方式方法,運用寓言、典故、正反對比等等,都是說體文所具備的,同時也構成了它們的藝術特色。
1.善用典故,寓意深刻
唐代雜說雖然有時候是一時之感,但行文構思卻十分精妙,他們常借典故、創作寓言故事來講道理,構思奇巧,文字洗煉。錢穆有言:“詩人之比興,正似小說家之寓言[6]。”這句話便是說,在說體文中運用寓言就像詩歌的比興手法一樣普遍。以寓言揭示道理、表達中心思想,既含蓄,又十分形象。
柳宗元是唐代說體文最多的文學家,錢穆有言“雜記之外,復有雜說,于韓集不多見,而柳集乃頗盛[7]。”而柳宗元雜說最多的便是以寓言揭示深刻道理的說體文,有《鶻說》、《羆說》、《謫龍說》等。《鶻說》中鶻雖然是一種猛禽,外表也兇悍,但卻懷有仁義之心,不食抓來的小鳥而將其放飛以報取暖之恩。作者借此對社會上以貌取善惡的現象予以了批評,同時對那些道貌岸然的善者不知報恩的丑陋行徑進行了諷刺和痛批。茅坤評價此篇曰:“柳子疾世之獲其利而復擠之死者,故有是文,亦可以刺世矣[8]。”《謫龍說》以龍女自喻,將自身貶謫之后所遭受的屈辱喻為龍女貶凡后所受的欺凌。通過對龍女的外貌和性格的描寫,表現出自身品性的高潔,不愿與“非其類”者同流。《羆說》寫了一個只會學百獸鳴叫而無實際本領之人,通過學百獸鳴叫僥幸捕得猛獸,最終卻被猛獸吞噬。諷刺了那些“不善內而恃外”[9]蒙混度日之人,同時對當時朝廷“以藩制藩”的政簧進行了大膽而深刻地嘲諷。這三篇文章通過寓言或類似寓言的方式對社會的一些現象、國家的一些政策進行了辛辣地諷刺抨,因以物為寓托,所以顯得含善委婉。
陳黯的說體文也常借用寓言說理。如《御暴說》:“或問爲物之暴者,出于狼虎也,何暴?攫搏于山藪之間爾。權幸之暴必禍害于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狼虎之暴,炳其形,猶可知也。”[10]這段話鮮明地指出權幸之暴比狼虎還可怕,同時作者又比喻說,為田鄙者知道除狼虎,有國者卻縱容權幸施虐,“豈有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11]也是把矛頭指向朝廷。再如《本貓說》,表面批評貓棄其職守,交善于鼠,而且遵循損友之道,與鼠狼狽為奸,倒戈以攻擊其主人,實際借此諷刺時政。此類還有李翺《知鳳說》和《國馬說》、來鵠的《貓虎說》、司空圖的《說燕》、韓愈的《馬說》、劉禹錫的《說驥》等等。
在《劉勰文心雕龍·事類》一文中提到:“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劉勰認為用典即是通過引用古事、古語來說明當下的道理。唐代許多說體文運用典故,便是用古事以諷今事。
開元三年春夏,山東遭受重大蝗災,姚崇奏請捕殺蝗蟲,而黃門監盧懷慎認為殺蝗太多,恐傷天和,姚崇反對盧懷慎而作《答盧懷慎捕蝗說》。“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蛇,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子將圣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開篇即用了楚莊王的寬仁待下、孫叔敖的為民除害、趙宣子進諫一心為國、孔子維護綱常禮制四個典故,表現了古代仁者的優秀品質。文章接下來再述如今蝗災泛濫,說明了自己這樣做是為了百姓著想,以此而達到說理的效果,態度堅決,說服力極強。
用典不僅可以借古諷今,諷刺時事,還能夠表達某種愿望或情感。李觀的《交難說》開篇敘述了很多歷史上肝膽相照的佳話和患難與共的友情,表達了李觀對知音難求,人情淺淡的感嘆,以及他對尋找知己的渴望之情,讀來使人有強烈的沉重感。文中的典故不僅很好的訴說了作者與歷史人物相似的情感,并且在原來的基礎上還有可能得到更深層的感悟。
這一類雜說大都篇幅短小精悍,而內容簡潔生動,創造了一種準確而生動的文風,很豐富的趣味性之下卻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可謂說體文有別于其他文體之優點。
2.正反對比,深化論點
劉勰的《文心雕龍》把文章分為“陳政、釋經、辨史、詮文”[12]四品,“議、說、傳、注、贊、評、敘、引”[13]八名,以“論說”總其名。說體文在劉勰看來屬于“論辯”,經由過程對客觀事物的深入觀察,推尋埋沒于背后的道理,認為說體文是一種明辨是非的文章。這樣的說體文寫作講究說理深刻、邏輯嚴密、條理清楚,所以作者在文中往往會用一組或幾組例子,兩種截然相反的形象進行對比,是非對便可以了然于文中,最后得出鮮明的論點,表明作者的觀點和態度的。
韓愈的名篇《師說》、《馬說》文中都有對比之處,《師說》是針對當時以從師為恥的不良風氣而作的,說理透徹、論證雄辯,非常有說服力。文章開篇先表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間從三個方面進行對比,抨擊“恥學于師”的人。分別用古今對比、人們對自己與對孩子的要求、“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對比。從后果、行為、心理等方面逐層深入分析,指出了他們在“從師”問題上的不同態度,點明了從師學習的重要。《馬說》中,因“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而將造成了千里馬的兩種不同結果的對比,又將千里馬和伯樂對比,最后發出“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14]的感嘆。
與《馬說》類似的說體文還有劉禹錫的《說驥》,文章寫了主人未能識別自家的好馬,使之“秣之稊秕、飲之污池”[15],還將它作為駑馬賣掉。而在懂得此馬價值的人那里,馬由于得以以“寶馬蓄之”,很快就顯出出眾之處,因此而發出“寶與常,在所遇耳”[16]的感嘆,以此說明能香擇賢用能的關鍵在于執政者能否識別人才,而不在于有無人才。
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本文在寫作手法方面,全文處處運用對比:捕蛇者與納稅的對比、捕蛇者的危險與納稅之沉重的對比、捕蛇者與不捕蛇者的對比。通過捕蛇者的遭遇,表現了永州百姓們的悲苦,以此揭露朝廷的黑暗和對百姓的殘害,借以諷勸時政。呂祖謙《古文關鍵》稱道:“感慨譏諷體。”[17]浦起龍《古文眉詮》亦云:“捕蛇刺暴政,守官者當合而誦之。”[18]
李翺《知鳳說》和《國馬說》兩篇中也運用了對比。《知鳳說》通過“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圣人之在人也”,將鳥與人做對比,最后得出“故曰知賢圣人者觀其道”[19]的觀點。《國馬說》通過國馬與一些人對比,借以批評“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20]這樣的人。這兩篇都是以寓言形象象征人的高貴品質,然后通過動物與人的對比,發出自己的感嘆。
以上說體文都是列舉正反面的事例層層對比,反復論證,具有極強的說服性。
3.駢散結合,氣勢磅礴
說體文除了在初唐時期沒有出現之外,幾乎跨越了唐代散文創作的高峰時期。首先是陳子昂的出現,在唐代前期的文風轉變上起了關鍵作用,他提倡風雅寄興和漢魏風骨,使“天下翕然,質文一變”[21]。他的文章多用間有駢句的散體寫成,從他開始,寫散體文的人數開始增多,如姚崇的《十事要說》。
大唐開元盛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開創這一盛世的宰相姚崇功不可沒,他上任之前提出要唐玄宗答應他十件事:“為政先仁義”、“不求邊功”、“中官不預公事”、“國親不任臺省官”、“行法治”、“租庸賦稅之外杜塞貢獻”、“寺廟宮殿止絕建造”、“禮接大臣”[22]等。作為論體,該文直言敢諫,氣魄雄偉,涉及為政、邊功、稅賦、吏治等國家政治生活的重大事項。既有簡短的事實陳述,又有具體的諫議內容,以疑問句形式排比鋪陳,一氣呵成。
到了中唐時期,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駢文的極度雕琢、唯美的形式,不適合社會對文學的要求。因而,許多有識之士們反對駢文,提倡恢復先秦兩漢的文章傳統,以無拘束的散行單句來闡述儒家思想。錢穆在他的《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提出,古文運動的一大貢獻就是有著先進的文體判別,讓短制散文在文學史上有了一席之地。[23]從說體文的數量上來看,古文運動之后說體文不再像初盛唐時期那么寥寥無幾,而是大量發展起來,且題材豐富、行文靈活。總的來看唐代的說體文有的是對仗嚴格的駢體文,有的則是駢散結合,而后者數量更多。
李觀創作的說體文駢化傾向很明顯,文章多為整齊的四字句,氣格與駢文相似。如其《交難說》,全文表面看全為整齊劃一的四字句,句式隨文意自由變換,仿佛沖口而出,靈動自然。其《說新雨》也同樣,文章仿佛是在寫新雨,其實是寫對圣朝的仰慕,排比能夠使文章達到一種加強語勢的效果,氣勢磅礴。但這樣的文章還是存在駢文的一些缺點,即整齊華麗的四字句使得作者觀點表達不夠鮮明,略微缺乏說服力,文中用語晦澀艱深,沒有深刻的思想性。
另一類駢散結合的說體文則更加條理分明,內容上層層遞進,作者觀點鮮明,同時在閱讀時還富有節奏感,能夠加強文章的表達效果。曹丕《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主”,駢散結合能夠使文章氣勢磅礴,全篇的主旨在句子中也能得到充分的表現。
姚崇的《答盧懷慎捕蝗說》,開篇即用四個典故排比鋪陳,后文則進行論述,既有典故,又陳述了事實,短小精悍。開篇的排比句定了全文的氣勢,表現出姚崇的態度堅決。再如李翺的《雜說上》:“上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24]這樣的排比貫穿全文,將天人關系表達的淋漓盡致。《雜說下》也是駢散結合,蘊含了深刻的儒家哲學思想。再如周愿的《牧守竟陵因游西塔著三感說》,以排比開篇:“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為者,歌功而為者,詭時而為者,感舊而為者:旌物,謚也;歌功,形也;詭時,詐也;感舊,情也。若乃折裂金石,騷牢鬼神,莫尚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耶?客曰:何謂也?”[25]總結了古人作文的幾種樣式,同時也為自己作此篇說明緣由。文章中的排比搭配感嘆、反問等手法,達到了很好的議論效果。
說體文中的駢散結合,能夠使句子表達更佳精辟深刻、含蓄凝練,使整個文章顯得雄健渾厚、氣勢磅礴。駢文的對偶性,將所議論之事巧作比較,加上感嘆詞、反問、夸張等修辭手法,更加增強了說理的效果。
結語:
本文深入分析了用典、對比、排比等藝術手法選了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說體文來歸納總結,分析了唐代說體文的藝術特色。研究唐代說體文,能夠更了解這個時代的散文發展樣貌,唐代尤其是古文運動,使得這個時期的散文在文體發展上不僅是承上啟下的作用,更具有開創意義。由上文可看出,唐代說體文不僅是認識歷史的寶貴資料,更是文學創作的豐富借鑒,有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唐代社會,拓寬視野,得到藝術上的享受。
注釋:
[1]王洪主編.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M].北京:學苑出版社,1991.第832-833頁.
[2]吳訥.文章辨體敘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43頁.
[3]左丘明.左傳[M].長沙:岳麓書社,1988.第226頁.
[4]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132頁.
[5]劉勰,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220頁.
[6]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從(四)[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55頁.
[7]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從(四)[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55頁.
[8]高文,屈光.柳宗元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02頁.
[9](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5900頁-第5901頁.
[10](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7984頁.
[11](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7984頁.
[12]劉勰,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212-213頁.
[13]劉勰,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212-213頁.
[14](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5644頁.
[15](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141頁.
[16](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八[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141頁.
[17]朱一清,于石.古文觀止鑒賞集評·第三卷[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第372頁.
[18]朱一清,于石.古文觀止鑒賞集評·第三卷[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第375頁.
[19](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428頁.
[20](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428頁.
[21]徐鵬校點陳子昂集上海中華書局1962第260頁
[22](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二百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2085頁.
[23]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從(四)[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57-58頁.
[24](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427頁-第6428頁.
[25](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百二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257頁.
參考文獻:
[1](清)董誥等.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吳訥.文章辨體敘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3]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4]劉勰,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2012.
[5]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從(四)[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6]陳志揚.說文文體與宋前說文研究[D].遼寧:遼寧師范大學,2008.
[7]南哲鎮.唐代雜說研究[J].安徽:古籍研究,2004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