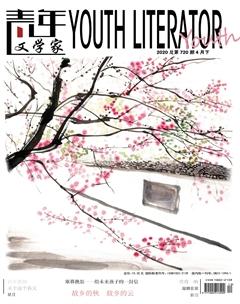三維轉換視角下古詩《相思》英譯本對比研究


摘 ?要:本文以古詩《相思》三個英譯本為例,運用生態翻譯學中“三維轉換”理論對其進行對比分析,并嘗試得出“整合適應選擇度”較高的譯本,并驗證“三維轉換”對古典詩歌的翻譯指導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表明,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過程中運用“三維轉換”理論有助于原詩語言、文化及信息的準確傳遞及再現,驗證了“三維轉換”在中國古典詩歌翻譯中的可行性。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三維轉換;《相思》英譯本
作者簡介:顏悅(1996-),女,漢族,山東人,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筆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12-0-03
一、引言
三維轉換是生態翻譯學的一種研究方法,要求譯者在翻譯時需要將選擇轉換的重點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這三個維度,即“在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原則之下,相對地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胡庚申, 2004:133)。”其中的“語言維”是指譯者在語言形式方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并且這種轉換又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文化維”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文化意識,認識到翻譯是跨越語言、跨越文化的交流過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以保證信息交流的順利實現(ibid:137)。“交際維”是指譯者在關注語言形式和文化內涵的轉換之外,還應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ibid:138)。事實上,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三維”轉換往往是同時進行、不可分割的,又是相互交織、互聯互動的。但這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不否認其中某一維度有時會在翻譯過程中有特別凸顯的情形。譯者需要至少進行三個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才有可能會產生較為恰當的譯文(胡庚申, 2008:2)。本文將運用生態翻譯學的“三維轉換”這一方法論與古典詩詞《相思》的英譯本進行結合,運用“三維轉換”理論對王維的《相思》三個英譯本進行對比賞析,并驗證“三維轉換”對古典詩詞翻譯的指導意義,促進古典詩歌語言、文化及交際信息的傳遞及轉換,為古詩譯者提供一條切實可行的翻譯方法,更好地指導未來的翻譯實踐。
二、《相思》及英譯本
(一)《相思》原詩
相思
王維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相思》是唐代詩人王維創作的一首借物抒情的經典詩歌。此詩是在抒發相思之情,而全篇卻一直都在描寫紅豆,詩人用意十分明確,通過相思子來傳遞相思之情。第一句闡明紅豆產于南方;第二句用一個問句“發幾枝?”,十分自然的設問使語言極為樸實而又十分形象,暗逗情懷;第三句勸友人多多采擷紅豆,但其意并不在此;第四句闡明相思子的所暗含的屬性,使用“最”字將其包含的思想情感最自然地流露出來,也就恰好對應上了上句“多采擷”這一愿望,而詩人想要傳遞的情感也深含其中。整首詩格律十分明快,但同時又含蓄委婉,雖描寫的景色極為淺顯,但要表達的情義卻十分深重,也就印證了此詩為何至今仍廣為流傳。
(二)《相思》英譯本
《相思》英譯包括許淵沖、辜正坤、吳均陶等在內的十多個版本,本文主要選取其中三個進行對比研究。
譯文一:
One-Hearted
By Wang Wei(Witter Bynner譯)(無押韻)
When those red berries come in springtime,
Flushing on your southland branches,
Take home an armful, for my sake,
As a symbol of our love.
譯文二:
Love Seeds
By Wang Wei(許淵沖譯)(韻式ABAB)
The red beans grow in southern land.
How many load the autumn trees!
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
They would revive fond memories.
譯本三:
Lovesickness
By Wang Wei(辜正坤譯)(韻式ABAB)
In the south red bean shrubs grow,
In spring abundant seeds they bear.
Gather them more, please, you know
They are the very symbol of love and care.
三、“三維轉換”視角下《相思》三個英譯本的對比研究
本文主要通過 “三維轉換”對古詩《相思》三個不同的英譯本進行比較,分析不同版本分別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這三個維度的優缺點,嘗試得出“適應選擇轉換度”較高的譯本,并驗證“三維轉換”這一方法論在古詩英譯中的可行性,有助于傳遞及再現原詩語言、文化及交際信息。
(一)語言維
語言維的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對語言形式進行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胡庚申,2009:49)。對于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則要求在譯詩過程中首先注意的便是對原詩的風格韻律進行恰當的轉換。因為當時創作詩歌的最初目的是吟唱,所以無論漢詩還是英詩都講究韻律節奏美。要做到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就必須保留原詩的風格韻律。從語言維的“音”來看,《相思》原詩是典型的五言絕句,一、三句分別以二聲‘國、‘擷,二、四句分別以一聲‘枝、‘思做韻腳,體現了漢詩句式工整、語言簡練的特點。在譯文一中,全詩無一處押韻,所以該譯本在“語言維”層面上的轉換沒有達到韻律美這一效果。譯文二和譯文三的韻式皆為ABAB,與原詩韻腳完全相符,即ABAB。所以可以看出,兩個譯文均在語言維的韻律層面進行了恰當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使譯本的節奏韻律方面與原詩保持一致,再現原詩的韻律。因此,在進行語言維轉換時譯者需將原詩的韻律進行轉換,所以譯文一在語言維韻律層面上處理的并不妥當,而譯文二和譯文三皆實現了語言維韻律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從語言維中的“行”來看,這三個譯本都是四行詩,這與原文的形式相當。每篇譯文句式長短均勻,基本符合原詩形式。所以從語言維層面來看,許譯和辜譯實現了語言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二)文化維
文化維層面的適應性轉換則強調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時刻關注源語及譯語之間存在的文化、內容及性質上的差異。譯者在進行文化維轉換的過程當中要對譯語及源語的文化的內在進行理解和解讀,防止曲解原文,要時刻關注著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體系(胡庚申, 2011:5)。所以在文化維層面進行轉換時,譯者需對源語中的文化負載詞進行恰當的選擇轉換。古詩是一種語言高度凝練的文學體裁,其中也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文化意象,和能夠體現中國文化元素的形象。所以在翻譯古典詩歌時,譯者需全力再現出中國古典文化中特有的文化意象和形象。原詩中關于紅豆寄托相思的傳說,古已有之。相傳古時候有一個役卒戍邊而死,他的妻子痛苦地思念丈夫,日夜在紅豆樹下坳哭致死,淚血染成紅豆,此樹因而得名相思樹。又據唐人撰寫的《云溪友議》記載,天寶十五載(756),安祿山攻陷長安,唐玄宗逃往四川,宮廷樂師李龜年流落到湖南,曾于湘中(湖南)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馀。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辭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歌闕,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慘然(陳鐵民, 2000:122)。由此可見,王維在這首詩中穿插了民間故事和歷史傳說,用樸實的語言傳遞出最真摯的情感,借紅豆的形象表達自己的相思之情。王維十分擅長使用有人間煙火氣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傳說,寓意簡明卻足夠深刻,讓人讀完回味無窮,體現出高超的駕馭文字的功底。而詩中的“春來發幾枝”還是“秋來發幾枝”歷來頗有爭議。學者朱競通過這首詩版本演變過程的探究,證明了應該是“秋來發幾枝”(朱競, 2008:53)。本文選取三個譯文中的“紅豆”和“春/秋”的翻譯進行比較分析如表。
紅豆生于南方,色澤華美,質地堅硬,紅艷持久,古時人們常用以鑲嵌飾物。古時有一位女子,因其夫君戍守邊疆而死,遂哭于相思樹下而死,終化為紅豆,所以從那時起紅豆又稱作“相思子”。后來的唐詩中就常用它來表達相思之情。而“相思”之情并不僅限于男女情愛范圍,朋友之間也有是存在相思的,如蘇李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即著例。此詩題一作《江上贈李龜年》,傳遞出對朋友思念與眷戀,可見一斑。譯文一將其翻譯為 “red berries” ,Bynner將紅豆理解為紅色漿果,在對比相關圖片后,發現紅色漿果并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紅豆。很顯然,由于中西文化差異,該譯文沒有表達春原詩作者想要傳達的文化意象—紅豆。而譯文二和譯文三都將紅豆翻譯為了 “red bean(s)” ,兩種譯文基本傳遞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紅豆這一形象,所以譯文二和譯文三在紅豆這一文化維層面的傳達更勝一籌。
其次,到底是“春來發幾枝”還是“秋來發幾枝”一直是學者們反復探究、爭論的問題。據相關歷史資料考證,此處原詩應為“秋來發幾枝”。因為王維原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縣),從他父親開始,遷居于蒲(今山西永濟縣)。他終年61歲,都是在北方讀書、考科舉、做官和隱居中度過的。從他一生的經歷來看,他從沒有到過“南國”。對于紅豆的自然生態,他是沒有看見過的。他所看到的,只是豆粒而已。對于紅豆在什么季節開花以及能夠開發幾枝,他也都是不清楚的(陳漢才, 2002:9)。因此這也就解釋了“春來發幾枝”一句后面問號的用法。筆者在查閱了紅豆的開花和結果期后了解到,紅豆的花期為每年的4~5月。譯文一和譯文三皆遵循了該詩演變而來的現代版本,即將原詩第二句中的花期翻譯為 “spring (time)”,兩個譯文符合了紅豆真實的花期。而許淵沖在翻譯時尊重了詩人的原作,即“秋來發幾枝”,即將第二句中的花期翻譯為 “autumn”一詞,雖然不符合紅豆的真實花期,但卻再次印證了詩人王維并不了解南方作物的生長習性這一事實,更加尊重原詩作者的創作,所以許譯更勝一籌。所以從文化維這一層面來看,許淵沖的譯文更好地實現了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一)交際維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胡庚申, 2011:8)。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要求譯者不僅需要進行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傳遞,同時需要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信息的層面上,要時刻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也就是說,譯者要仔細推敲原文詞語所要傳達的意思,同時進行準確翻譯,同時譯者要準確再現原文所要表達的信息與意圖,這樣就可以使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一樣的感受與信息的“一致性”。當然,受到源語與譯語文化差異的影響, “一致”近乎只能是一種理想的狀態,譯者只能做到盡量縮小文化和交際差距,才能實現交際維層面的選擇轉換。本文將針對三個英譯本對題目《相思》及“(發)幾枝”在交際維層面的轉換進行分析歸納如下表。
原詩題目為《相思》,又名《相思子》。但很顯然詩歌并不是在描述相思子這種植物,而是借相思子來寄托傳遞詩人相思的情感。作為詠物詩,王維并沒有把過多的筆墨傾注在紅豆的具體描繪上。他從關心紅豆的生長情況,到勸對方多多采集,最后歸到主旨所在,點出紅豆的寓意。因為紅豆本與“相思”相聯,所以這首詩寫得毫不勉強,十分自然。所以借紅豆來寄托相思之情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譯文一將“相思”直譯出來,直接表明原詩所要表達的感情,易于讓讀者在讀過題目后便知曉整篇詩歌所要傳達的情感。譯文二 “love”一詞的使用,將相思子這種植物所能夠呈現的情感立刻表現出來。相思子,顧名思義就是愛的種子。而這種愛既可以給戀人,也可以給友人。這種翻譯方法給讀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間,很好地實現了詩歌模糊性的寫作風格。譯文三中的 “lovesickness”意為“相思病”,此處屬于過度翻譯。詩人本意是借物喻情,只是表達對友人的思念。而譯文三則表現出詩人相思成疾,與原詩意圖并不相符,因此沒有實現交際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同理,對于全詩最后一詞“相思”的翻譯,許淵沖的譯文更為恰當和妥帖。因為相思之情不僅能夠表達愛意或者關心這種過于膚淺的意義,它更能夠激起人們對往昔歲月的翩翩回想,所以 “revive fond memories”很好地實現了這一層面的轉換,也讓譯語讀者對中文里的“相思”一詞的含義更加清晰明了。
其次,原詩寫道“春來發幾枝”,首先從交際維的單復數方面看幾枝,復數應好一些。譯文一將“幾枝”轉換為 “branches”,查閱相關資料可知,相思子莖細弱,多分枝,因此翻譯成branch較為準確。此外該詞使用了復數,與原文所要表達的意圖相符,較好實現“交際維”層面的轉換;譯文二在進行交際維轉換時譯為 “how many”,只譯出了幾枝的“幾”,省譯了“枝”的翻譯。由于中文多使用量詞,而這些量詞在英譯時是不需要譯出的,由此可見,許淵沖在翻譯時充分考慮到了中英語言的表達使用差異,將量詞直接省譯,很好地實現了交際維層面的轉換;譯文三譯為 “abundant seeds”,指大量的種子,原詩是一個問句,并不確定會“發幾枝”,而譯文三卻使用肯定語氣“大量”來指開了大量的相思子花,很顯然此處與原詩要表達的意思是完全背離的。綜合來看,譯文二對“幾枝”處理的較為恰當。從交際維這一層面來看,許淵沖的譯文更好地實現了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四、總結
本文基于生態翻譯的方法論,從“三維轉換”的視角分析了古詩《相思》的三個典型的英譯本,分別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進行系統地分析和對比,從而得出不同譯本在三維轉換層面各自存在有缺點。在語言維這一層面,許譯和辜譯句式工整且韻式與原詩一致,所以二者實現了語言維層面的轉化;在文化維和交際維中,只有許譯既尊重原詩作者的創作意圖又照顧了譯語讀者的閱讀和理解,所以實現了較高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所以從整體來看,許淵沖的譯本“整合適應選擇度”略高于另外兩個版本。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三維轉換”理論應用于中國古典詩歌翻譯中具有較高的可行度,但目前該理論主要用于詩歌英譯的對比分析上,在翻譯批評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它可以幫助翻譯批評家更加嚴密理性地分析各種譯文,但相信在未來,該理論將對翻譯實踐具有良好的實際指導意義。這就要求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必須時刻謹記并重視語言、文化、交際的三個維度信息的傳遞及轉換,使譯文更好地適應生態翻譯這一大環境、大背景之下。
參考文獻:
[1]陳漢才.詠物抒情 寄托相思——王維《相思》詩賞析[J].語文月刊,2002(03):9.
[2]陳鐵民.也談紅豆與《相思》[J].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02):122-125.
[3]陳貽焮.王維詩選[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4]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5]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觀[J].上海翻譯,2008(02):1-5.
[6]胡庚申.傅雷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J].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09,32(02):47-53.
[7]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J].中國翻譯,2011,32(02):5-9.
[8]朱競.王維《相思》“春”“秋”二字小考[J].井岡山學院學報,2008(01):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