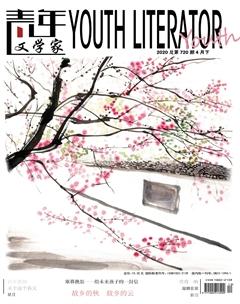淺論《哪吒之天降魔童》的互文性
摘 ?要:本文從互文性的角度分析《哪吒之天降魔童》影片與其他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哪吒形象和哪吒故事為方向進行互文閱讀不但給觀眾欣賞影片帶來互文性愉悅,而且讓人從發(fā)現(xiàn)差異之處挖掘改編所產(chǎn)生的新意義,也給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在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繼續(xù)前進和煥彩重生提供方向。
關鍵詞:互文性;弒父;新生
作者簡介:韓情(1994-),女,漢族,黑龍江省大慶市人,渤海大學文學院文藝學碩士生。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12--03
2019年上映的動畫電影《哪吒之天降魔童》在贏得高票房和高口碑的同時掀起了中國動畫崛起的聲浪,這很令我們高興和欣慰,但最關注的還是電影對哪吒形象和哪吒神話的改編處理。它以“哪吒神”為原型,在眾多重述“哪吒傳說”的作品中另辟蹊徑,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但又并非完全脫離原作,在人物、情節(jié)設計和眾多場景中通過“互文”的方式與原文本暗合,在解構之后又重新建構一個完備和諧的“新神話”,既帶來新鮮的劇情體驗又重新講述“哪吒神話”,勾起觀眾心底的童年記憶,也激發(fā)了人們強烈的觀看欲望。眾所周知,哪吒是中國神話故事中最具特色的人物,更是中國民間家喻戶曉的神明。關于他的傳說和故事千百年來不斷被演繹和填充,他的反抗精神也在影響和塑造著我們的民族精神。《哪吒之天降魔童》讓我們不斷和記憶中的小英雄形象以及文學作品中的哪吒相互比較,但見出差異不是目的,挖掘變化背后的根源才是目的。互文性理論給了我們一個較好的角度去探究。
“互文性”又譯為“文本間性”、“文本互涉”,“互文性”,這一概念是由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女性主義批評家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創(chuàng)立。互文性在眾多理論家的發(fā)展下越來越豐富,從文學文本不斷擴大到泛文本,建筑、繪畫、影視藝術也被包括在內(nèi)。影視領域的互文性“從狹義上講,說的是一部影片與另一部影片或明或暗的(例如,通過影射、模仿、戲仿或混成)參照方式,或者,從廣義上講,說的是一部(影片)文本與其他文本可能會有的各種關系”。互文性的研究價值并不在于“同”,而在于“異”——“同中之異”。《哪吒之魔童降生》通過引用、暗示、改編、戲擬等互文性策略將大量文本納入影片主文本中,使觀眾在觀影的同時調(diào)動自己的認知和原有記憶形成綜合性的視聽效應,在熟悉中品嘗陌生,在差異中挖掘新生意義。
一、新舊主角哪吒形象的互文
哪吒,是中國神話的外來者,原是印度佛教中的護法神,譯作那吒,梵文全名是Nalakuvara或Nalakubala。佛教經(jīng)典作品出現(xiàn)的那羅鳩婆、那吒鳩跋羅、那吒俱伐羅、那吒天王、那拏天等,這些譯名都是由梵文名音譯而來。宋代之后,特別是明清小說和戲曲中開始出現(xiàn)并使用“哪吒”一詞,這在佛經(jīng)譯本中是沒有出現(xiàn)的,此后通俗文學《西游記》、《封神演義》的風行,更是推動并奠定了對“哪吒”的認可。哪吒一開始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和信奉,而是隨著毗沙門天王影響才逐漸走進世人眼中。關于二者的關系,主要有兩種說法,父子說和祖孫說。在哪吒形象的演變過程中,毗沙門天王是至關重要的人物。漢譯佛教經(jīng)典中哪吒所占篇幅并不多,大多都與毗沙門天王共同出現(xiàn),且多是作為毗沙門天王的家人。隨著佛法的不斷宣揚,毗沙門天王信眾頗多,且記載其常在西北幫助唐軍獲勝。唐朝將領李靖因高超的軍事才能被世人有意神化,他和毗沙門天王的形象不斷融合,李靖最終發(fā)展演變成為毗沙門天王。隨著李靖被世人神化為托塔李天王后,哪吒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李靖的兒子。
哪吒在現(xiàn)存佛經(jīng)的記載中極其簡化,有的只是關于他某一方面的描寫,在唐不空所譯的《北方毗沙門天王隨軍護法儀軌》中有對哪吒外貌的描寫:“手捧戟,以惡眼向四方……毗沙門神其孫哪吒天神七寶莊嚴,左手令持口齒,右手詫腰上令執(zhí)三戟槊。”此處“惡眼”并非指哪吒神有兇惡之意,在密教中,常有“身現(xiàn)惡相心作大悲”之說,此處承襲了密教的說法,表明哪吒嫉惡如仇、神力無窮。哪吒的形象描述較之佛經(jīng)具體的是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哪吒“身長六丈,首戴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云足踏盤石,手持法律,大罅一聲,云降雨從,乾坤爍動。”此時的哪吒還保留著佛經(jīng)中的身高和形態(tài),但已經(jīng)中國化為道教神祗。
許仲琳的《封神演義》對哪吒故事描述最為詳盡,是集佛經(jīng)、傳說、民間故事于一體地進行綜合創(chuàng)作,但對哪吒形象并無多大改進,而更專注于故事的發(fā)展。寥寥幾筆勾勒一個“面如傳粉,唇似涂朱,眼運精光,身長一丈六尺”的形象,但這里的哪吒沒有受《西游記》孩童形象的影響,仍是身量修長、孔武有力、扶周伐紂的先行官。1979年版的動畫電影《哪吒鬧海》以《封神演義》為底稿對哪吒故事進行改編,第一次將文學文本的描述轉(zhuǎn)換成影視形象,哪吒變成了一個身量未足的孩童,唇紅齒白,劍眉星目,善良活潑又聰明可愛,深受周圍人的喜愛,基本上都未脫離上述關于哪吒的描述。《哪吒之魔童降生》開了先例,完完全全打破了各種版本的哪吒,雖然他仍是三歲小孩,但他已不是靈珠子的轉(zhuǎn)世,而是魔珠投生,因魔珠魔性的影響,哪吒在外形上十分魔幻,他帶著濃重的黑眼圈,仿佛化了煙熏妝,滿口豁牙,一身匪邪氣,憑著渾身蠻力,調(diào)皮搗蛋,到處惹是生非,活脫脫的一個“熊孩子”。等到突破自我時又變成三頭六臂的忿怒哪吒。這一人物設計在電影未上映的時候就引起廣泛討論,爭議不斷,也為電影的上映造勢。
創(chuàng)作者在現(xiàn)代性視域下通過不同途徑對傳統(tǒng)神話進行重述和改寫,將神話、文學、歷史記述等進行“互文”意義上的重述,對人物形象進行創(chuàng)新性的改造,既有所保留,又有新意,文本與電影互為“互文本”,相互勾連,相互詮釋。在跨文化的視野下,所有文本都可以作為‘互文加以解讀,所有的閱讀都是重讀,所有的改編都是重寫。《哪吒之魔童降生》不只對哪吒的形象進行重塑,敖丙變成了靈主轉(zhuǎn)世溫文爾雅的謙謙公子,成為哪吒的好朋友;太乙真人變成了一個騎著一只豬的操著四川口音的胖“酒鬼”;申公豹是一個長著豹頭的口吃男;殷夫人武藝高強,每天斬妖除魔保護一方仍愛子如寶的慈母;李靖是一個寡言少語卻又默默守護哪吒的好父親。這些設定的改變必然也預示著故事情節(jié)的不同尋常。
二、故事情節(jié)的新舊互文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是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哪吒”故事,幾乎接近許仲琳的《封神演義》,哪吒是玉皇大帝座下大羅仙,因世間魔王禍亂,玉帝命其下凡,托胎為托塔天王李靖之子。哪吒出生第五天,在東海沐浴嬉戲,腳踏水精殿,翻身直上寶塔宮。龍王怒而向哪吒索戰(zhàn)。出生第七天就能戰(zhàn),殺九龍。龍王無奈何而上告玉帝,哪吒知道后之將其截在南天門打死了他。后又無意射死石記娘娘之子,石記興兵,哪吒與之戰(zhàn),李靖畏懼群魔之主的石記,害怕哪吒殺死石記惹怒諸魔之兵。哪吒為了不連累父親,遂割肉刻骨還父。哪吒的真靈向世尊求救,世尊因其能降魔,折荷菱為骨,藕為肉,系為脛,葉為衣復活他,傳授法輪密旨,“親受木長子三字,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轉(zhuǎn)斗;嚇一聲,天頹地塌;呵一氣,金光罩世;磚一響,龍順虎從;槍一拔,乾旋坤轉(zhuǎn);繡球丟起,山崩海裂……”哪吒憑著靈通廣大、變化無窮的本領蕩除了世間妖魔,靈山會上以為通天太師、威靈顯赫大將軍,玉帝封其為三十六員第一總領使,天帥元領袖,永鎮(zhèn)天門。
《封神演義》從第十二回《陳塘關哪吒出世》到第十四回《哪吒現(xiàn)蓮花他身》,花費大量筆墨描寫哪吒,可以算得是哪吒的個人傳記。《封神演義》將《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哪吒與妖魔的矛盾轉(zhuǎn)化成哪吒與父親的矛盾和仇恨。故事從一開始就在為“父子成仇”做鋪墊,母親懷孕三年零六月,產(chǎn)下肉球,父親疑是妖怪,砍破肉球后發(fā)現(xiàn)是一個可愛孩子,便留其性命。太乙真人將其收為徒弟,命名哪吒。七歲便能戰(zhàn)夜叉殺敖丙,龍王也奈何不得。李靖懦弱,因哪吒惹禍愈多,恐牽連自己,對哪吒很不待見。當四海龍王帶天兵來捉拿父親李靖夫婦時,哪吒毅然挺身而出,厲聲道“一人行事一人當……豈有子連累父母之理!”便析骨肉還父母,龍王敖廣念其“救你父母,也有孝名”,便讓哪吒以死償命。哪吒為求重生,托夢于母親在翠屏山為他建行宮并造哪吒神像,受百姓三年香煙奉祀即可修成肉身。李靖卻責罵其:“生前擾害父母,死后愚弄百化。”把哪吒像打壞,燒了廟宇;哪吒神無所依,求告太乙真人,真人用蓮花、荷葉合成人形,使哪吒肉身復現(xiàn),并傳武器火尖槍和風火輪,又付豹皮囊,囊中放乾坤圖、混天綾、金磚一塊。哪吒下山就要報李靖毀廟、阻其再生之仇,認為自己既己交還骨肉,自認與他無關,為何還要阻撓自己。李靖不敵哪吒,戰(zhàn)敗逃走,后遇燃燈道人贈予李靖金塔,才得鎮(zhèn)伏哪吒,哪吒不憤又無可奈何,父子終講和。可以說,《封神演義》將各種版本的故事融合重整,著重描寫父子沖突,甚至惡化到“殺子”與“弒父”的程度,成功塑造哪吒反抗父權的抗爭形象,對后世影響深遠。
《西游記》只在第八十三回《心猿識得丹頭 姹女還歸本性》中對哪吒的出身進行了簡要說明。哪吒名字的來歷是因為出生時左手掌上有個‘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他出生三天就能下海游水洗澡,闖禍踏倒了水晶宮,捉住蛟龍抽其筋要做絳子,李靖知道后恐生后患,欲殺之。哪吒憤怒,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靈魂到西方極樂世界求告佛祖。佛祖將碧藕為骨,荷葉為衣,念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重生后來要殺李靖,報剔骨之仇,李靖求告如來,如來賜其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塔上層層有佛,艷艷光明,讓哪吒喚佛為父,解了冤仇。《西游記》也將矛盾集中于哪吒重生弒父,敢于直接反抗人倫孝道的約束,哪吒自此成為與齊天大圣孫悟空相比毫不遜色的反叛者,在中國神話傳說的歷史上熠熠生輝。
哪吒故事在《封神演義》后基本定型,后世大多以此為藍本進行創(chuàng)作,在人物和情節(jié)設計上都沒有太大出入,但《哪吒之魔童降生》完全打破了這個故事框架,它從一開始就改變了故事走向,混元珠一分為二化為靈珠/魔丸,哪吒陰差陽錯成為魔丸降世,三太子敖丙卻變成靈珠投胎。原本的善惡雙方被倒置,哪吒成為人人懼怕又奈何不得的“魔”,敖丙則成為正面形象,這種錯置也是哪吒逆天改命的敘事動機。這樣,原本哪吒所面臨的析骨肉還父母、“弒父”等極具戲劇沖突和張力的情節(jié)就轉(zhuǎn)變?yōu)槟倪敢蚴悄话傩諈挆墸胍@得人們認同的而不能之后走上抗爭改命之路,最終達到自我認同的主體性建構。傳統(tǒng)哪吒故事中的核心并不是善與惡的對抗,哪吒與龍王之間是一種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哪吒的力量是壓倒式的,善/惡之間無法建構起有效的矛盾對抗和張力充足的戲劇沖突。更深層、更震撼的悲劇性情節(jié)是哪吒與父親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沖突。《魔童降生》將李靖塑造成了一位愛子無聲的慈父,為他不惜舍棄自己的性命以渡哪吒平安。于是原文本中哪吒與父親核心沖突消失了,變成了哪吒與敖丙雙主角的成長故事,個體與父權之間的倫理悲劇,轉(zhuǎn)化為“我命由我不由天”這樣一個西方式的尋求主體性的故事。
三、從“弒父”到“新生”的精神內(nèi)核
創(chuàng)作者對哪吒故事進行了一次類型化的現(xiàn)代文本改編,電影被溫和化為一個容易為觀眾接受的合家歡類型動畫片,使用“愛可以拯救一切”好萊塢類型電影的敘事法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悲壯弱化為找到自我的“成長敘事”,“削肉還母,剔骨還父”的反叛精神內(nèi)核和“弒父”的悲劇核心元素被徹底解構。
父子沖突一直是東西方文學的共同母題,但對于這一母題的結局處理卻完全不同,“殺子”與“弒父”截然相反的結局走向,這與東西方文化有很大關系。一般說來,父親是陳舊沒落力量的代表,兒子則是新生進步勢力的代表。在父子沖突中,西方文學大多以父輩失敗,甚至被子殺死取代而結束,“弒父情結”成為西方的一種文化,從神話、史詩、戲劇、小說等許多作品都有描寫,表現(xiàn)出西方人強烈的反抗精神和抗爭意識。對父親的反抗,就是對絕對意志、權力的反抗,是對自由、個性、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向往。弗洛伊德認為人類天生具有‘弒父情結,從其出生開始,他就注定要和父親展開斗爭,以擺脫被統(tǒng)治,被支配的地位,爭取獨立自由的權利,進而掌握家庭主導權和社會主動權。但東方文學則往往是以子輩的屈服、認輸甚至是傳承父輩為結局,在儒學“以孝為先”統(tǒng)治幾千年的中國,父親擁有無上的權力,“天無二日,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父親成為家庭中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存在。“父為子綱”的倫理觀念使父親對子女擁有絕對的處置權,甚至發(fā)展到了“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的極端情況。所以哪吒的存在就成為中華孝文化中的一個反叛者,他以命償命是救父母于危難之中的孝心,但采取“削肉還母,剔骨還父”自毀肉身的方式卻隱含著對“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孝文化的反抗,歸還父母精血以斷人倫,斬斷親情血脈的聯(lián)系,追求自我獨立和精神自主。所以當李靖毀壞哪吒的塑像以后,哪吒誓要報仇,認為自己既己交還骨肉,自認與李靖無關,就決然與之對抗,“弒父”便有了合理性。雖然最終結局仍是父權獲得勝利,哪吒敵不過“金塔”,喚佛為父,究其根本還是哪吒無法與強大的維護父權的社會制度相抗衡,結果只能無奈屈服,受其驅(qū)使。
《哪吒之魔童降世》將哪吒這一形象所包含的對抗父權的力量,轉(zhuǎn)化為了對抗抽象天命的抗爭行為。這種對抗看似宏大,實則空洞。哪吒作為一個本性非惡的孩子,不但沒有肆意妄為,還一心想要被大家喜愛和認可。更何況,哪吒成為魔丸降世,并不是出于天命(天命哪吒本是靈珠投生),而是由于申公豹的刻意破壞、報復和太乙真人的疏漏、大意。雖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確像極了一個悲壯的命運悲劇,但在敘事過程中,宿命悲劇早已轉(zhuǎn)換為一個在親情感召之下“找到自我”的成長故事。
總之,《哪吒之魔童降世》建構了新型的中國風動畫。依托在中國傳統(tǒng)神話資源的基礎上,吸收、引用、拼貼、融合、轉(zhuǎn)換其他的文化資源,雖削弱了哪吒這一形象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中的反叛性與對抗性,卻使故事的走向更加溫暖,世俗,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注釋:
①[英]吉爾·內(nèi)爾姆斯.電影研究導論[M].李小剛 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141.
參考文獻:
[1]韓美鳳.《封神演義》中哪吒形象探析[D].內(nèi)蒙古:內(nèi)蒙古大學,2008.
[2]付方彥.哪吒形象流變研究[D].長沙:長沙理工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