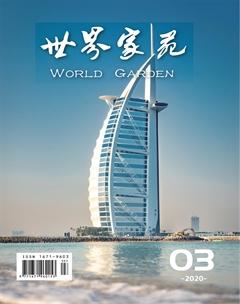從《赤穗事件》看日本江戶時期忠孝觀
摘要:根據元祿14年發生的真實故事《赤穗事件》改變而成的《忠臣藏》自誕生之日起至今200多年仍經久不衰。其講述的是47名義士集體為主君復仇,最終集體剖腹的故事,向主君表達了“忠”。47壯士的義舉在日本幾乎為人不知無人不曉,至今的每年12月14日,日本各大劇院仍然會上演《忠臣藏》,本文試圖通過《忠臣藏》來分析日本江戶時期的忠孝觀念。
關鍵詞:《忠臣藏》;忠孝觀;復仇
1 赤穗事件
元祿14年3月14日,赤穗藩主淺野長矩為“御馳走役”,但因淺野不明典禮規程,將軍便將他安排至專門從事幕府儀式,但淺野未向吉良行賄,因此便刁難淺野,并將錯誤禮儀教給他,導致淺野在典禮當天丑態百出,淺野惱羞成怒便拔刀刺傷吉良,將軍府動刀乃大忌,德川綱吉為之大怒,命令淺野當天剖腹謝罪,并剝奪其在赤穗的全部領地,淺野家全部家臣一夜之間成為“浪人”。然而卻未對吉良做任何追究,這明顯違背了武家社會“喧嘩兩成敗”原則,即爭吵雙方不問理由均要受到處罰。淺野家47名家臣認為主君受到不公正待遇,于是他們暫定交出赤穗城,家臣們流落在外,隱姓埋名,成為浪人,但是他們為主君淺野復仇的念頭確更加強烈,經過一年多的縝密的計劃,最終以大石為首的47武士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1702年12月14日)借著月光和雪地的反光,潛入吉良家,將其殺死,翌日清晨將吉良首級奉在淺野墓前,成功完成復仇行動,其他46人被判集體剖腹,之后也同他們主公一起葬在泉岳寺。
2 《忠臣藏》中的“忠”與“孝”
淺野家47名武士集體為主君復仇的事跡在當時引起不小轟動,在主君淺野剖腹謝罪到他們成功復仇之間一年多時間里,他們拋棄一切名聲、正義、親情,準備復仇工作。大石為告別妻子,變賣家產,甚至為籌集路費,還把的妻子和妹妹賣到當地妓院,自己則到江戶城低級妓院,打架斗毆,47名武士在不惜一切完成復仇,其根源思想在于對主君的“忠”的束縛,在日本,對領主的“忠”是建立在“施恩”與“奉公”的所謂“主恩從報”的基礎之上,因此,這使得在日本社會中,“忠”優先于“孝”。大石為表明對主君的“忠”,不禁舍棄對親情的“孝”也佐證了這一點。這也成為江戶時代重“忠”輕“孝”的模范。武士們不惜舍棄自身名譽和犧牲家庭,也要為了主君而盡忠。那么江戶時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重“忠”輕“孝”的價值取向呢?
幕府時代,社會上實行嚴格的“士、農、工、商”嚴格的身份制度,作為“四民”之首的武士階級,其收入實行俸祿制,因此切斷了武士與土地的直接聯系,武士作為大名的家臣,失去了與主君對抗的經濟基礎,便使得武士對上級主君的絕對服從。
儒學中強調“大義名分”和“倡導天理、反對私欲”思想的朱子學更加受到幕府重視,更多宣傳主君對武士有恩,所以武士應該對上級報恩,宣傳“恩”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忠”與“孝”所涵蓋的范疇不同,在實際生活中也必然會產生矛盾。“忠”的對象為國家主人,“孝”的對象為尊卑血親,因此會產生“忠孝不能兩全”現象。“恩”實際上作為一種“債”,必須要還,所以全力報恩在日本人看來是一種美德。
德川將軍將土地作為恩典分給各“大名”,各“大名”作為受恩的回報要效忠于幕府將軍,因此赤穗藩主淺野處于對將軍“恩”的回報有義務完成典禮,當淺野為維護自身名譽公然在幕府上拔刀刺傷吉良時,也有義務剖腹來彌補自己對主君的“不忠”,這也可以視為是對幕府的報恩。而接受淺野作為恩典分給以大石為首的武士們的土地,處于對淺野恩典的回報,他們也有義務為其復仇。因此,當淺野死后,他們面臨兩種選擇,跟隨淺野剖腹而死,或等待機會為淺野復仇。否則,其作為武士的名譽將會被玷污,在德川時代,武士把名譽看的比任何東西都重要,獲得名譽評價是武士身份者所有社會活動中最大的價值目標,因此淺野家47武士在通過一年多的等待之后,忍辱負重,最終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殺死吉良,成功為主君復仇。因此,“報恩”做為表達家臣對主君的“忠”,也成為了一種價值取向。
在日本,特別是“在日本戰國以后的非血緣協作型社會中,血緣意義上的孝親觀念開始淡薄,人們對孝的理解,接近于中國社會的“忠”的,當47名武士面對“忠”和“孝”的矛盾時,他們都懷著“君父之仇恨,不共戴天”的信念,像維護家的名譽一樣維護主君。這種犧牲個人以及家庭作為代價來為報效主君的求“忠”而舍“孝”的行為,引起了日本人的共鳴。
3 江戶時期的“忠”與“孝”
“忠”與“孝”這兩個儒家倫理觀念是中日共同推崇的道德準則,“忠”是指對主君盡忠,“孝”則是指對父母盡孝,但是兩者在中日兩國之間所處的位置卻不相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基于親子血緣關系而產生的“孝”,而日本傳統文化則強調基于“主恩從報”的“忠”,尤其江戶時代后,人們對“忠”的認識超越了對“孝”,“忠”不再是只是實現政治目的的道具,而成為了全民的道德要求。
德川時代,武士作為行政官僚,失去了獨立的經濟基礎,武士及其家庭的生存完全依靠主君發放的俸祿。因此,武士對于來自幕藩體制越來越強化的“盡忠”要求,已經沒有任何資格要求任何條件。
日本在17世紀前后才使“孝”在全社會得以普及,其內容大多表現為子女對長輩承擔的義務,而且,日本“孝”道還摻入了大量佛教色彩,更多的宣揚“恩”的作用,認為子女對父母“盡孝”就是報答父母的恩情,“恩”是“孝”的前提,這種對恩的等價償還,稱之為“義理”,日本人自出生起,無時無刻不生活與“義理”之中。因此對于武士來說,無論是父子還是夫婦,最終都是為主君“盡忠”。因此,這也說明了日本集團主義的傾向十分明顯,同時也說明“忠”的進一步強化。
4 小結
如上所述,在《忠臣藏》中,由于扎根于家臣心中的為主君“盡忠”的束縛,使他們舍棄了對家人的“孝”。日本人基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孝”,結合本國獨特的社會條件和人文條件,最終形成了一種不同于中國傳統“忠孝”的“重忠輕孝”的思想,通過對此的研究,可進一步了解日本文化的特質。
參考文獻:
[1] 莫文沁.《趙氏孤兒》與《忠臣藏》忠孝觀念比較研究[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6(09).
[2] 劉金才.中日倫理價值取向比較—以傳統文化中的“忠孝觀”為中心[J].人文雜志,1994.
[3] 王煒.日本武士名譽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4] 莫文沁.解讀歌舞伎《忠臣藏》中“情義”的束縛[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5(07).
[5] 新渡戶道造著,張俊彥譯.武士道[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6] 魯思本尼迪克特著.菊與刀[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作者簡介:張拓(1994—),男,湖北荊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學文化。
(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