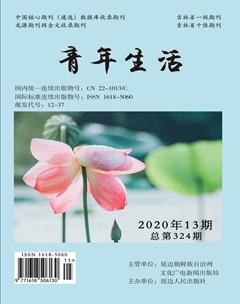app應(yīng)用程序中的個(gè)人信息保護(hù)
劉彬
隨著信息技術(shù)與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交匯融合,各類移動(dòng)應(yīng)用程序的運(yùn)用,使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完成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各個(gè)方面的事項(xiàng),極大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截至2019 年12 月,我國國內(nèi)市場上監(jiān)測到的App 數(shù)量為367 萬。移動(dòng)網(wǎng)民人均安裝APP總量增加至60款,用戶每天花在各類App 的時(shí)間為5、1小時(shí)。從應(yīng)用類型看,App 已實(shí)現(xiàn)生活場景全覆蓋,形成圍繞個(gè)人需求的完整消費(fèi)閉環(huán)。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極大便利了人們的生活,而人們在享受移動(dòng)應(yīng)用程序(APP)帶來的便利時(shí),公民個(gè)人信息的泄漏問題也屢屢發(fā)生。根據(jù)CNNIC發(fā)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jì)報(bào)告》,個(gè)人信息泄漏的網(wǎng)民比例排名,從2018年12月的第二位上升到2019年6月的第一位。盡管國家加大了APP侵害用戶權(quán)益的專項(xiàng)整治工作,但是信息泄漏問題仍然屢見不鮮,僅2019年7月到2020年1月這4個(gè)月期間,至少進(jìn)行過7次公開點(diǎn)名要求APP進(jìn)行整改,且每次都有知名APP在列, 目前相關(guān)部門對于問題APP主要采取自查、曝光、下架、限期整治等之類措施,但由于此類措施威懾力不大,整改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如何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加強(qiáng)APP個(gè)人信息保護(hù)。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一、APP應(yīng)用程序應(yīng)用環(huán)節(jié)中個(gè)人信息存在的問題
1、APP應(yīng)用程序中個(gè)人信息收集環(huán)節(jié)存在的問題。根據(jù)艾媒咨詢機(jī)構(gòu)發(fā)布的《2020年中國手機(jī)App隱私權(quán)限測評(píng)報(bào)告》,當(dāng)前多數(shù)手機(jī)App仍存在強(qiáng)制超范圍索要權(quán)限的情況。部分APP運(yùn)營者為了盡可能的收集公民個(gè)人信息,通常會(huì)超范圍的索要用戶權(quán)限,企業(yè)在相關(guān)協(xié)議中都會(huì)盡可能將擴(kuò)大用戶授權(quán)收集數(shù)據(jù)的范圍,或者模糊授權(quán)條款收集用戶個(gè)人信息。
2、 APP應(yīng)用程序中個(gè)人信息共享環(huán)節(jié)存在的問題。數(shù)據(jù)共享已經(jīng)成為信息數(shù)據(jù)利用的一種重要方式。數(shù)據(jù)共享能實(shí)現(xiàn)數(shù)據(jù)資源的重復(fù)利用,降低數(shù)據(jù)收集成本,實(shí)現(xiàn)同類數(shù)據(jù)社會(huì)效益的最大化,與此同時(shí),為了獲得用戶的授權(quán),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通常都會(huì)用其經(jīng)營、技術(shù)上的優(yōu)勢地位通過格式條款以概括性授權(quán)。鑒于個(gè)人信息與信息主體人格利益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此種委托可能會(huì)造成信息主體失去其作為信息主體的控制權(quán)。 并且概括性授權(quán)主要依賴于格式條款的捆綁同意,在實(shí)踐中用戶在安裝使用一些軟件和程序時(shí)如果不同意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的格式條款,則無法安裝使用。由于APP在數(shù)據(jù)收集時(shí)使用概括性授權(quán),缺少合理的授權(quán)機(jī)制。對于該類行為,APP運(yùn)營者對于個(gè)人信息共享行為往往會(huì)受到合法性的質(zhì)疑。
3、APP應(yīng)用程序中個(gè)人信息使用環(huán)節(jié)存在的問題。APP信息收集者在收集到關(guān)聯(lián)信息之后,需要對信息加以處理和分析,掌握數(shù)據(jù)背后的用戶喜好,進(jìn)而預(yù)測未來市場的走向,制定下一步的商業(yè)計(jì)劃,由此才使得信息數(shù)據(jù)發(fā)揮其巨大的價(jià)值.通過對于信息的分析,獲得相關(guān)結(jié)論、發(fā)展趨勢、主體喜好等,在這些結(jié)論的基礎(chǔ)上制定行動(dòng)計(jì)劃,可以實(shí)現(xiàn)商業(yè)經(jīng)營者的商業(yè)目的和商業(yè)利益。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僅僅從外部屏蔽大數(shù)據(jù)主體挖掘個(gè)人信息是很難實(shí)現(xiàn)的,收據(jù)運(yùn)作者一般都是通過多種數(shù)據(jù)掌握他人個(gè)人信息。目前,各社交網(wǎng)站一般會(huì)不同程度地開放其用戶所產(chǎn)生的實(shí)時(shí)數(shù)據(jù),這些信息可能被一些數(shù)據(jù)提供商收集。另外,還存在一些監(jiān)測數(shù)據(jù)的市場分析機(jī)構(gòu),通過對人們在社交網(wǎng)站中寫入的信息、智能手機(jī)顯示的位置信息等多種數(shù)據(jù)組合,己經(jīng)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鎖定某個(gè)人以及挖掘出其個(gè)人信息體系,用戶的信息安全問題堪憂。因此,在保護(hù)個(gè)人信息安全的過程中需要考慮如何規(guī)范過度分析的行為,從而做到針對性的規(guī)制。
二、APP應(yīng)用程序中個(gè)人信息保護(hù)的具體建議
1 完善APP應(yīng)用程序中信息收集的授權(quán)規(guī)則。
APP個(gè)人信息收集作為個(gè)人信息事前防范的關(guān)鍵步驟,可以通過區(qū)分信息授權(quán)等級(jí),禁止個(gè)人信息回溯以及設(shè)立隱私信息的備案許可這三種規(guī)則來進(jìn)行完善。對信息管理控制者實(shí)施的信息收集行為而言,首先可以區(qū)分信息授權(quán)等級(jí),把個(gè)人信息按照敏感程度來進(jìn)行劃分。例如按照一般性、敏感性、公開性來劃分信息的授權(quán)范圍,對于一般性信息,可以一次性授權(quán),對于敏感類信息可以進(jìn)行二次授權(quán)。二次授權(quán)的信息應(yīng)當(dāng)經(jīng)過用戶的單項(xiàng)同意,并且根據(jù)信息等級(jí)區(qū)分,信息與第三方機(jī)構(gòu)共享根據(jù)等級(jí)的需要征求用戶同意等。例如無法別人具體個(gè)人以及不涉及隱私的信息、用戶的該類信息可以一次性授權(quán),對能夠識(shí)別具體個(gè)人的以及涉及到用戶隱私的信息在與第三方機(jī)構(gòu)共享時(shí)需要征求同意等等。 二是禁止個(gè)人數(shù)據(jù)“回溯”。用戶注銷信息或一部分信息被共享給第三方時(shí),都要求對個(gè)人信息進(jìn)行匿名化處理,但是這些匿名化、去標(biāo)識(shí)化的個(gè)人信息,只要有足夠的外部數(shù)據(jù)來源,數(shù)據(jù)控制著仍然可以通過技術(shù)反向追蹤用戶。因此對于個(gè)人信息的保護(hù)應(yīng)當(dāng)嚴(yán)格禁止數(shù)據(jù)回溯,匿名化與去標(biāo)識(shí)化以數(shù)據(jù)的不可追溯為標(biāo)準(zhǔn)。 三是隱私信息的備案與許可。 《信息安全技術(shù) 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應(yīng)用(App)收集個(gè)人信息基本規(guī)范(草案)》規(guī)定了各類APP的最小化收集類型,對于超范圍的信息收集行為,可以根據(jù)個(gè)人信息保護(hù)的不同程度進(jìn)行備案和許可,對于超過最小化信息收集的一般信息,例如無法識(shí)別個(gè)人,以及無法追蹤的信息,可以向信息管理機(jī)構(gòu)進(jìn)行備案。對于超過最小范圍收集的涉及用戶個(gè)人隱私的信息或者可以追蹤到個(gè)人的信息,可以向信息管理機(jī)構(gòu)申請?jiān)S可,獲得信息管理機(jī)構(gòu)同意后再進(jìn)行收集。
2、完善信息主體的各項(xiàng)權(quán)利
在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信息處理者對個(gè)人信息的處理,其目標(biāo)應(yīng)當(dāng)是信息主體權(quán)利的最大化,其行為不應(yīng)與該宗旨相違背,因此增強(qiáng)信息主體對個(gè)人信息的控制至關(guān)重要。用戶對信息的控制主要體現(xiàn)在信息主體的知情權(quán)、查詢權(quán)、更正權(quán)、刪除權(quán)等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的。第一,保障用戶的知情權(quán)。個(gè)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信息主體的個(gè)人信息時(shí),應(yīng)當(dāng)履行告知義務(wù),滿足信息主體的知情權(quán),個(gè)人信息處理者在收集個(gè)人信息時(shí),將處理個(gè)人信息的目的、種類、因共享其次合同需要轉(zhuǎn)讓的第三方信息等向信息主體明確告知,以保障信息主體的知情權(quán)。在個(gè)人信息處理過程中,如改變信息的使用目的,或有因企業(yè)內(nèi)部原因造成個(gè)人信息泄漏、損毀和滅失,也應(yīng)及時(shí)履行告知義務(wù);第二,信息主體對于信息處理者處理其信息的行為有查詢和更正的權(quán)利,信息主體可以查詢信息處理者對于其信息的使用范圍,以及對于個(gè)人信息處理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信息主體對于其個(gè)人信息同意具有更正權(quán),對于不正確的個(gè)人信息,信息主體可以要求信息控制者對其信息進(jìn)行更正;第三,信息主體具有刪除權(quán),當(dāng)個(gè)人信息的存儲(chǔ)已經(jīng)不被允許或不再需要,或其準(zhǔn)確性無法確保,或信息主體反對時(shí),信息主體有要求APP對其個(gè)人信息采取阻滯或者刪除的權(quán)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