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笛,帶五億人種“螞蟻森林”
尹潔

徐笛。浙江人,2011年入職螞蟻金服,花名祖望,曾任商業智能部總經理。螞蟻森林項目創始人之一,2019年代表團隊獲頒聯合國“地球衛士獎”,現任螞蟻金服社會公益部總經理。
用手機“種樹”是從什么時候成為風潮的?
早上醒來,打開手機里的螞蟻森林,為自己養的虛擬樹收一波能量或者“偷”一波能量;每天跑步、騎車、在線支付,通過各種低碳生活方式積累能量,看著虛擬樹越長越大;直到有一天,能量值達到要求,螞蟻森林的種植員會將一棵真樹種在沙漠里。
這一套操作,讓無數網友樂此不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幾年下來,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為中國的綠化事業創造了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奇跡。
3月中旬,在中國第四十二個植樹節到來之際,全國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發布了一份國土綠化狀況公報。其中顯示,2019年中國共完成造林706.7萬公頃、森林撫育773.3萬公頃、防沙治沙226萬公頃。
公報里特別提到,社會公眾參與國土綠化的熱情高漲。“全國綠化委員會辦公室聯合中國綠化基金會、螞蟻金服集團開展的‘螞蟻森林項目,超過5億社會公眾參與,植樹造林168萬畝。”
實際上,截至2020年3月,螞蟻森林用戶已經達到5.5億人,累計碳減排超過1100萬噸,種植真樹1.22億棵。
“跟國家的大力投入相比,無論是種樹總量還是總面積,螞蟻森林做得還遠遠不夠,但它成功喚醒了很多人的環保意識,見證了低碳環保在中國的流行。”徐笛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作為螞蟻森林項目的創始人之一,他去年代表團隊到聯合國領取了“地球衛士獎”。

2019年4月,志愿者在春種時節植樹。
四成中國人用手機種樹
根據阿里巴巴集團的慣例,徐笛也有一個花名——祖望,在媒體報道中常常代替了他的本名。對于自己,徐笛不愿意多談,但說起當初創建螞蟻森林的經過,他平緩穩重的聲音里還是帶著一絲“想不到”的感慨。
徐笛在大學里的專業是通信工程,畢業后進入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工作,至今已快10年。最初他在商業分析團隊,通過研究各種數據,幫助公司管理層進行商業決策。工作近5年后,徐笛接手會員團隊,負責數億會員用戶的管理和運營。
2016年夏天,一個艷陽高照的正午,徐笛接到了上司打來的電話。“祖望啊,我們剛剛開了個重要的會,公司要推動綠色金融戰略。這個會雖然沒有讓你參加,但大家一致、全票通過,由你來做這個產品。”
徐笛就這樣進入了螞蟻森林的初創團隊。他覺得大家之所以選擇自己,是希望找一個對用戶比較了解的人,“剛好那個時間點,我負責會員業務,所以他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我”。
至于螞蟻森林是怎么做起來的,徐笛用“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他之前從沒接觸過植樹造林行業,但對綠色生態很感興趣,接到任務后,第一個想法就是設計一種模式,激發用戶的參與欲望。
為了這個模式,一群人討論來討論去,但全世界都沒有可參考的案例。當時團隊做了一個評估,發現很多用戶有綠色低碳意識,比如坐公交、地鐵代替開車,每天步行活動,通過移動支付減少紙張使用,等等。這些行為都可以用數字科技記錄下來。于是有人提出,能不能像銀行那樣,給每個用戶開一個“碳賬戶”。
問題是,記錄下這些行為后,用什么來回饋用戶,實現一個完整的商業閉環?
“我們不停地討論,最后討論出了一個方案,就是種樹。”徐笛說。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參加過植樹活動,“讓沙漠變綠洲”“防止水土流失”的觀念也深入人心,但在日常生活中,要自己去種、去養一棵樹是不容易的。
徐笛認為螞蟻森林之所以能推廣開,關鍵就在于極大降低了普通人的參與門檻。人們只要將低碳理念變成生活習慣,積少成多,就能實現“種一棵真樹”的夢想。每天收獲的綠色能量都是一種鼓勵,讓用戶有成就感,從而激發起更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坦率講,當初設計的時候,我們也沒想到今天能有這么大的用戶規模。”徐笛說,“我們只是想讓它盡可能地簡單、好理解、好操作。”
早期的一個方案是讓用戶把自己的環保行為拍下來、上傳,但這樣比較麻煩。后來,團隊想到利用手機的記錄功能,將用戶每天的環保行為記錄下來,第二天可獎勵一個減排量。
另外,螞蟻森林也在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之間建立了一個連接。普通人要到內蒙古、甘肅、青海去種一棵樹,成本高得難以想象。螞蟻森林不僅幫大家種了,還通過衛星地圖,把樹木在當地的生長情況展現給用戶。
“螞蟻森林的很多功能都是根據用戶反饋添加和改進的,比如約好友一起種樹、幫好友收能量。大家熱情很高,我們也是邊干邊學。”徐笛說。

上世紀90年代末,位于內蒙古的庫布其沙漠地區在植樹造林、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已經有了一定成效。(資料圖)
“網友選樹也看顏值”
徐笛一直生活在南方,因為螞蟻森林項目跑了很多西北、華北的荒漠化地區,每次看到螞蟻森林的種植現場,他總有一種被震撼的感覺。
螞蟻森林的第一片種植林在內蒙古的阿拉善。“阿拉善”在蒙古語里是“五彩斑斕之地”。這里地處內蒙古自治區最西部,往北就是蒙古國。那里有片一望無際的開闊地,螞蟻森林種下了大量的梭梭樹,遠遠望去,就像一群倔強的、正在排兵布陣的“雜草軍團”。
“說到梭梭,也是個蠻有意思的故事。因為我們叫螞蟻森林,很多用戶就覺得我們的樹應該長得特別高大。其實梭梭更像灌木,那些高大的喬木對水的需求量比較大,在荒漠化地區難以存活。”徐笛說。
但很多網友在手機里選“樹”時并不了解這個情況。梭梭在螞蟻森林里是所需能量最少、最容易種的樹,所以選擇的人很多。然而當一些熱心的網友親自跑到阿拉善,希望親眼看看自己種的梭梭時,卻有些失望:“不是說好種‘樹嗎,怎么給我種了一團草?”
其實在沙漠里,梭梭才是真正的王者。看著不起眼,生命力卻極其頑強,只要有一點點水,梭梭就可以在兩三個小時內生根發芽,深深扎入沙土里。網友看到的“草”只是梭梭的幼苗期,它長成后可以達到4米,扎根可達十幾米,耐旱、耐寒、耐鹽堿,能有效防止沙漠化和水土流失。
“當我看到一大片梭梭的時候,那樣頑強地生長著,阻擋著風沙,一望無垠,那個畫面還是蠻震撼的。”徐笛對記者感嘆道。如果沒有梭梭,可能螞蟻森林也要換個模式了。徐笛回憶,團隊曾經認為種真樹太難實現,不如把每天產生的綠色能量做成一個個小泡泡,讓用戶像玩游戲一樣,每天戳泡泡。
“種樹”和“戳泡泡”的方案爭論起來,有人起哄:“誰敢說能找到真樹,我就做!”徐笛以為沒人敢接這個話,結果一個女孩子站出來說她去找。她找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后者當時正好計劃種植1億棵梭梭。
于是梭梭成了螞蟻森林最早引入的樹種,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成了螞蟻森林第一個合作伙伴。后來為了照顧網友的多樣化需求,團隊又相繼引入了花棒、樟子松、胡楊等一系列樹種。
有一次,團隊請的環保專家問:“你們為什么要種這么多花棒?”團隊告訴他,因為網友覺得花棒長得很漂亮,選擇它的人特別多。專家感嘆,做了一輩子研究,原來科研還要與人性相結合。
“當然花棒本身也有防風固沙的作用,但專家沒想到,用戶種得多的原因是它會開花、顏值高。”徐笛笑道。
很多網友都有個性化的需求。除了花棒,胡楊也很受歡迎。這種樹有一個特性:千年不死,千年不腐。很多人將它作為愛情樹,種一棵胡楊來紀念愛情。
被種樹改變的生活
徐笛的工作被螞蟻森林填滿了。大眾的熱情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上線3個月,螞蟻森林用戶突破6000萬人;上線5個月,超過2億。
“每天早上,至少幾千萬的用戶一醒來就要進螞蟻森林收能量,讓我們的團隊壓力巨大,如果服務器擴容不夠,就不得不限流。為了用戶更好的體驗,那段時間大家每天都熬夜。”
第一批梭梭很快種完了,線上的申請數量還在不斷增加,團隊好不容易湊齊新樹,剛種到土里,線上又來了一批新用戶,樹又不夠用了。“當時每天睜開眼睛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上哪兒去找樹?”
與此同時,許多普通人的生活也因螞蟻森林而發生了改變。
蘇州一所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的師生們,合力完成了“1年種101棵樟子松”的目標,為此早起收能量的學生多了,上課遲到的學生少了。

螞蟻森林的梭梭6號林現場,看起來像雜草的梭梭生命力極其頑強。
一個男孩總是偷偷地在螞蟻森林里幫一個女孩的梭梭樹澆水,兩人因此聊了起來,沒多久就確定了戀愛關系,最后還在螞蟻森林種下的樹林里拍了婚紗照。
一個體重280斤的小伙子,為了積攢能量,起早貪黑鍛煉,堅持步行、騎車,用3年時間在螞蟻森林種了很多樹,還減肥110斤。
“有用戶留言說,種完樹后,感覺這個世界終于因為自己的存在而有了一點不同。”徐笛說,“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個英雄夢,但因為現實的限制,很多人沒辦法實現。螞蟻森林讓大家感受到,原來通過自己的點滴努力,真的能夠為保護地球做一點實事。”
除了阿拉善,螞蟻森林在呼和浩特、鄂爾多斯、敦煌、承德、邯鄲等地也有項目。幾年跑下來,徐笛感受到不同地區的風土人情,也看到螞蟻森林給當地帶來的改變。
“我們的項目能為當地創造一些就業機會。我在阿拉善見到很多植樹人,有內蒙古本地的,也有來自青海、甘肅的,通過植樹,他們的收入都有所增長。”徐笛說。此外,現在每年有越來越多的人去阿拉善旅游,看自己種的樹,一定程度上也帶動了當地經濟。
在呼和浩特的清水河縣,螞蟻森林種植了很多沙棘。徐笛告訴記者,他們與當地政府有一個合作項目,將沙棘果加工成果汁,然后在網絡平臺上銷售,所得利潤全部投入當地脫貧和生態保護工作中。
“我們叫它生態脫貧。”徐笛說。為了改善生活,當地人非常努力地種植沙棘,日復一日地勞作。尤其是沙棘果的收獲季節在深秋至整個冬天,沙棘本身又是帶刺的,他們必須穿著厚厚的衣服、冒著嚴寒、戴著手套去采摘,然后送到本地的加工廠,十分辛苦。

2019年3月,甘肅民勤紅崖山,黃色部分是荒漠,綠色部分是人工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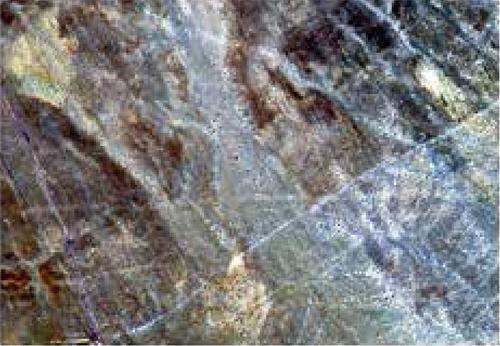
阿拉善荒漠化地區的衛星照片。
2019年末,第一批來自螞蟻森林保護地的沙棘汁被送到了網友手中,有人留言:“云種樹多年,終于等到了自家樹生產的沙棘汁!有一種農民伯伯的滿足感。”
今年3月,內蒙古31個國家級貧困旗縣全部“摘帽”。
“開發沙棘汁并不是我們一開始就規劃好的,而是在種樹的過程中,發現它還有這樣的經濟價值。我們希望在改善環境的同時,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讓他們擁有自我造血能力,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科技,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公益”
奮斗在一線的、數以萬計的植樹人和護林員,是真正用雙手和汗水改變生態環境的“地球衛士”。他們絕大多數都默默無聞,給徐笛留下過許多感動。
“他們大多是牧民和農民,非常淳樸。很多人沒有選擇出去打工,而是守護著家鄉的土地。我們有一個項目在甘肅一處林場,那里有一家人,家族三代一直堅持在那片土地上植樹,對抗風沙。”
這家人姓劉,他們所在的地區是甘肅省武威市民勤縣,林場的名字叫石羊河。上世紀60年代,家族第一代劉向銓種植的是沙棗林,當時這里是一望無際的沙海,睡一覺會被沙子蓋滿身,生活極度貧苦。很多人都離開了,劉向銓卻沒有走,他認為只有治沙,家鄉才有希望,于是一輩子都在種樹。
家族第二代劉成基也選擇留在家鄉,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種植喬木,進一步改變當地面貌。2003年,家族第三代劉永剛放棄了外省市的工作機會,帶著農業技術回到家鄉,開始種植梭梭,并將林場帶入了互聯網時代。
在劉永剛的帶領下,石羊河林場參與了螞蟻森林合作項目。在短短兩年時間里,其新增種植林地面積就占到建場以來林地種植總面積的1/5。這個數字也說明了,中國的環保事業正在從個人行為變成全民行為。
40年來,中國森林面積增長了一倍左右。中國的人工林面積和對全球植被增量的貢獻比例均居世界首位。正是無數劉家祖孫這樣的普通人,幾十年如一日地艱苦努力、默默奉獻,才讓中國變得越來越綠,讓中國人的生活環境越來越好。即使他們的名字不為大眾所知,他們的功績將與中國的治沙奇跡一起永載史冊。
每年春種的時候,螞蟻森林都會組織網友去看自己種下的樹。有人對徐笛說,那種感覺就像見到了自己的孩子,更激發了“要多做一些綠色公益”的熱情。
2019年9月,螞蟻森林獲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頒發的“地球衛士獎”,這是聯合國表彰環境保護行動的最高獎項,每年頒發一次。2017年,中國塞罕壩的造林人獲得了這一獎項;2018年,浙江省“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也獲得了這一獎項;到螞蟻森林,已經是中國綠色創新項目和環保人士連續第三年獲此殊榮。
“螞蟻森林所帶來的變化,本質上是由于數字科技的發展,讓幾億人能夠連接在一起,讓每個人能夠看到種下的那棵樹在哪里,這對用戶是非常大的鼓舞。”徐笛對記者說,“真實性激發成就感。如果只是一棵虛擬樹,我相信是無法吸引到5.5億用戶的。”
徐笛認為環保并非單純的公益行為,而是與科技、經濟和社會治理體系密切結合。螞蟻森林的成績,是整個中國對綠色生態事業重視程度和發展力度的縮影。
過去10年間,徐笛見證了數字化浪潮是如何一步步改變中國的,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也快速改變著某些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很慶幸能夠生活在這個時代。
曾有人問徐笛:這個項目為什么叫螞蟻森林?他說,希望匯聚每一份如螞蟻般平凡而微小的力量,最終給世界帶來一片森林。中國的綠色生態事業還有很多事情可做,每個領域里都有數字化變革的機會,用徐笛的話說:“科技,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