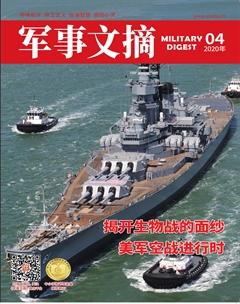專常兼備,枕戈待旦
曹亞鉑 冷沙 任雙堂

近年來,SARS、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疫病的頻頻爆發,給世界公共衛生安全拉響了警報。尤其是年初以來,各類病毒肆虐,給人類造成的威脅和恐懼日益嚴重。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武器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重視,生物武器的擴散進一步加劇,使得人們意識到生物戰的威脅并不遙遠,不論在戰爭或和平時期均會引發疾病的流行,造成人員的傷亡及長期的心理恐慌。生物戰可導致嚴重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無法回避的問題。目前,有關生物性攻擊的威脅和人類將面臨何種生物威脅都成為國家安全與公共衛生關注的焦點。因此,我們不得不深刻思考,面對未來的生物戰爭,我們將如何有效應對。
應對生物戰威脅任重道遠
據記載,人類首次“生物戰”發生于1763年3月英國進攻印第安部落時。然而,現代意義上的生物武器卻是在20世紀隨著武器技術和微生物學的發展而出現。盡管國際社會已達成《禁止生物武器條約》,并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但生物領域軍事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21世紀以來更是愈演愈烈。
狹義的生物戰主要是指在作戰過程中通過各種方式施放生物戰劑,造成敵方軍隊和后方地區傳染病流行,大面積農作物壞死,從而達到削弱對方戰斗力、破壞其戰爭潛力的目的。廣義的生物戰不僅僅體現在戰爭中,還包括以威脅、恐嚇、污染、改變基因等方式造成的生物侵害,比如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給人類健康和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造成的危害,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危害巨大。當今世界,生物技術日新月異,生物疫情頻頻爆發,生物領域的斗爭更加激烈,未來生物戰爭將更加殘酷,生物安全問題將更難防范,人類直面應對生物戰挑戰之路步履艱難。

據記載,人類首次“生物戰”發生于1763年3月英國進攻印第安部落時
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將生物威脅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界發生的生物威脅,即傳染病迅速傳播直接影響人口健康、安全和繁榮;另一類是蓄意和意外的生物威脅,主要是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使用或擴散生物武器,對他國安全、人口、農業和環境構成的挑戰。可以說,未來生物威脅可能是突發的人、動物或者植物疫情,與自然發生的傳染病或公共衛生事件很難分清。隨著生物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生物威脅樣式的增多,應對生物戰將不再僅僅局限于應對戰場上作戰對手惡意發起的生物攻擊,還在于應對邪教組織、恐怖分子等施放的生物戰劑所造成的社會危害,以及有效預防和控制自然界生物疫病等。直面生物戰爭,國際社會應對手段明顯捉襟見肘。在作戰層面,一般采取多維偵察手段,收集情報證據,分析生物攻擊方式;以精準打擊,預先摧毀敵人發射生物武器的陣地和施放工具;采取防護措施,預防人、畜、農作物受染發病。在戰略層面,各國則能力不一,主要軍事強國生物技術科研能力強,主導制生物權,但動蕩的國際局勢下存在生物攻擊技術“政治化”輸出的風險,小國則更多基于《國際禁止生物武器使用公約》,技術上依靠主要大國支援,消除生物威脅。另外,盡管國際早已簽約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公約,國際社會抵制生物戰認同也一致,但各方備戰程度卻不同,國際社會和相關組織在規約生物武器使用、反生物戰爆發的能力不足,機制不夠完善。
各國如何應對生物戰挑戰
中國——納入安全體系,制度建設逐步完善。與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物安全管理經驗相比,早期中國在生物威脅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和生物科技支撐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對農業安全、環境安全、食品安全等認識還不夠到位,對生物安全缺乏足夠的警惕性。厚積薄發,在應對2003年非典疫情過程中,中國依靠強大的制度優勢,以出色表現得到了世界各國的高度認可,也為有效應對生物戰威脅積累了一定經驗。2020年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明確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可以說,這是既立足當下又深謀長遠的戰略決斷,預示著生物安全被正式納入我國國家安全戰略,并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
美國——構筑生物國防,確保制生物權優勢。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在生物安全領域展開研究,并率先進行生物安全立法的國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就開始關注生物威脅,于1976年公布了全球首部生物技術研究安全管理規定——《重組DNA分子研究準則》,并首次提出了“生物安全”概念。2001年炭疽襲擊事件之后,美國又出臺了《公共衛生安全和生物恐怖準備反應法案》等多部法律法規。2004年,布什簽署了《21世紀生物防御》總統令,內容涵蓋了美國生物防御計劃的四大支柱。2009年,奧巴馬簽署了《應對生物威脅的國家戰略》,全方位闡述了美國應對未來生物威脅將使用的七種武器。2018年,特朗普簽署總統令頒發了新版《國家生物防御戰略》。此外,美國在生物安全基礎設施建設和力量整合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總體來看,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政府針對生物安全威脅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國家戰略和部署。
德國——居安思危,完備應急管理體系。德國嚴謹務實的傳統使他們能夠居安思危,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其不僅在生物科學實驗硬件設施上加大投入,而且在生物防衛制度管理上也追求卓越,建立了完善高效的應急救援體系。在救援領導體制上主要實行屬地管理,成立以州為主的應急管理體制。在救援指揮部方面分為行政指揮部和戰術指揮部,行政指揮部主要負責后方決策與溝通協調,戰術指揮部主要負責前方應急救援組織實施。救援隊伍體系方面形成了以專業救援人員為核心,以技術救援為后備骨干,以志愿者為支柱,社會高度參與的分工格局。在救援程序上實行模塊化、標準化管理,具有標準化的原則和步驟。總的來看,德國應急救援體系法律制度完善,機制協調有序,救援隊伍充足,分工布局合理,裝備先進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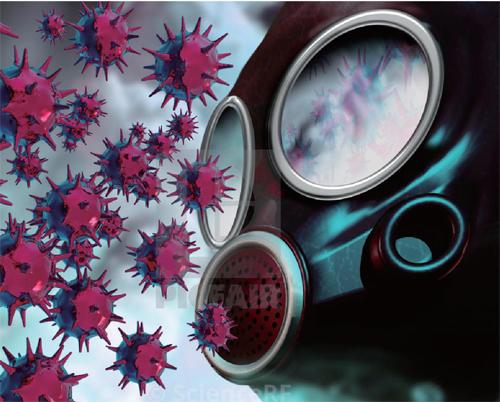
應對生物戰威脅任重道遠
日本——目標明確,生物戰略規劃清晰。2019年6月,日本正式發布了國家新版生物技術發展戰略——《生物戰略2019——面向國際共鳴的生物社區的形成》。該戰略明確提出日本生物技術發展的總體目標為“到2030年成為世界最先進的生物經濟社會”,具體包括建立生物優先思想、建設生物社區、建成生物數據驅動三個方面,并提出了五項基本發展方針。根據日本社會發展的需求和挑戰,該戰略提出了實現未來社會情景的4個建設重點和9個重點市場領域。此外,該戰略還明確了日本生物技術發展的9項重點任務和相關舉措。總體來看,日本在生物技術發展方面目標明確,戰略規劃路線比較清晰。
應對末來生物戰之策
加強國際協同合作。應對生物戰挑戰作為人類共同擔負的使命任務,既需要各國密切合作、共同擔當,更需要國際組織的密切協同協調。然而,現實生活中國際爭端不斷,互不信任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因此,面對生物戰的潛在威脅,為保護人類共同利益,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發展,一方面需要聯合國相關組織積極敦促國際社會按照《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和《關于人類基因組與人類權利的國際宣言》精神,在全球范國內盡早達成限制基因技術使用、全面禁止基因武器研制的公約和協議;另一方面,聯合國要盡快健全審查機制,由締約國共同參與,加大對成員國生物武器檢查核查力度,以便更好地督促和協調國際社會按照條約規定,加強對自身生物武器的控制。此外,有關國家和地區發生嚴重生物疫情和自然災害時,還需要國際社會積極協調,加大援助救助力度,共渡難關。

應對生物戰挑戰需要各國密切合作、共同擔當

美國政府針對生物安全威脅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國家戰略和部署
依法規范應對。應對生物戰威脅,離不開法律規范和制度保障。國外層面,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形成相對較為成熟的體制機制;國內層面,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15個體系”“9種機制”“4項制度”的建設要求,相關法規制度呼之欲出。因此,應對生物戰這個系統工程,需要國際組織和各個國家共同用力,既要加強頂層生物安全戰略規劃,又要完善科學研究、野生動物保護、物資儲備、疾病防控、應急管理、生產調度等配套法律法規,確保應對生物戰行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多方全力抗擊。生物戰是對國家指揮體系、軍事體系、應急救援體系、社會動員體系、物資儲備體系、通訊信息體系、輿論引導體系、傷病救治體系等的全面考驗,需要多方全力綜合應對。一是要完善應急預案。結合國家實際情況,針對敵人可能實施生物戰的戰法、途徑和手段進行專門研究,及早制定切實可行的行動預案。二是要組建有力的生物安全防衛力量。應對生物戰人人有責,人人參與,需要軍民結合,群防群治,可組建專家隊伍、應急機動部隊和志愿者“三結合”的安全防衛力量。三是要加強訓練演練。針對疫情特點和發生規律,組織部隊、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和企業等力量,定期進行訓練和演習,不斷提高應對生物戰的能力。四是要統籌規劃軍地聯合保障。應對生物戰需要軍地優勢互補、聯合行動,著力做好通用衛生防疫裝備研發、一體化防疫藥材聯合保障工作。
前沿科學預防。由于生物戰極具危害性和隱蔽性,所以應對其挑戰除了應急處置、戰后救治消除等手段,利用科學的手段進行監測預防更為重要。一是要加強生物安全教育培訓力度。把生物安全知識納入國防教育體系,建立以軍事醫學科研和軍隊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為骨干,以國家相應機構為依托的教育培訓體系,提高全民生物國防意識,打造過硬生物安全科技隊伍。二是要加大監測識別力度。建立和研發應對生物威脅的信息系統、檢測系統、監測系統、通訊和報告系統、支持技術系統等,形成對突發疫情、環境災害、生物武器等全頻譜威脅動態實時監測、感知、鑒別與溯源的能力。三是加強民族基因密碼保護。認真研究本民族的基因密碼,及早察明其中特異性和敏感性基因,有針對性地采用相應技術,提高和增強民族基因抵抗力。
責任編輯:張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