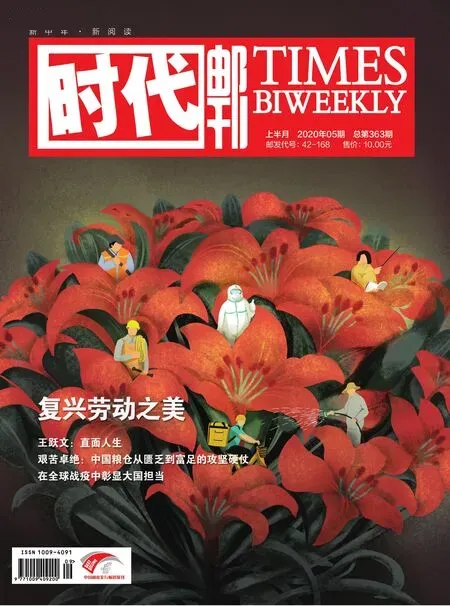大師許倬云:一生與中國的歷史和命運緊密相連
●
在面對大國興衰、全球性精神危機、歷史經驗教訓等大問題時,一個時代的思考者能給出怎樣的回答?
“我們要想辦法拿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要算是我走過的路之一。”這是著名史學大師許倬云先生對我們說的話。




許先生已89歲高齡,他這一生,始終與中國的歷史和命運緊密相連。他出生于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大陸,童年時飽受戰亂流亡之苦;青年時求學于臺灣和海外,受教于當時最杰出的一批學術大師;而立之年開始執教,成為紅極一時的學術新星;之后又遠走美國,和海外學人一起奠定了海外中國歷史研究巔峰期的基石……他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孤本,橫跨新舊兩個世界,學問博涉中西古今;他體察歷史變遷,思考人類命運;他有著兼濟天下的精神,他是知識分子的良心,他比我們想象的更重要。
我知道中國不會亡,中國不可能亡
許倬云生于1930年,中國正處于艱苦掙扎、存亡未知的年代。
他1歲時,九一八事變爆發;7歲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隨后10余年,戰爭不斷;20歲之前,他基本都在遷徙和流亡中度過。
因為許父是軍人,許家人也就經常要隨著軍隊轉移,或隨著難民逃難。在顛沛流離的日子里,年幼的許倬云滿目所見,盡是戰爭的殘酷場景——他們乘船逃難時,遭到日本人的機槍掃射;敵機空襲過后,他看見了玩伴的尸體……但他也看到了,戰爭沒有摧毀,反而凝聚了國人,有糧食拿出來一起吃,沒糧食就一起挨餓,多少老年人走不動了,對孩子說:“你們走,走!”
2020年3月4日,在許知遠的視頻訪談節目《十三邀》中,年近九旬的許倬云回憶起這一切,依舊心緒難平,哽咽失聲:“所以我知道中國不會亡,中國不可能亡。”
這段經歷對許倬云影響至深,并決定了他日后的治史方向。他說:“我從小在戰爭中長大,戰爭是非常殘酷的事,我知道什么叫做鮮血。我不講武功,不講開疆辟土,只講文化圈的擴大。”
老天起初對我不好,不過后來對我真是非常好
許倬云先天手足畸形,直到6歲都不能動,7歲才能坐上椅子,13歲后才能拄著雙拐行走,一輩子衣食起居都要靠人照料,但他后來卻說:“我是個有福之人。”
因為不良于行,許倬云一直未能入學。好在許家是世家大族,家中藏書眾多,父親的書房就是他的學堂。父親是性喜文史的儒將,看他沉迷武俠小說,對他說歷史里有更有趣的東西,給他拿來了《史記》,那時他9歲。
抗戰勝利后,許倬云投考家鄉無錫的輔仁中學。他的國文、史地分數非常高,英文不行,數理化沒讀過。但輔仁中學破例收下了他,他承諾英文和數理以后一定及格,結果到了高三時,他就開始自學微積分了。
1948年底,許倬云隨父母去了臺灣。1949年,19歲的許倬云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數學還得了滿分,但他的國文、歷史成績卻引起了校長傅斯年的注意。傅斯年找他談話:“你應該去讀歷史系。”大二時,許倬云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傅斯年又找他說:“你好好讀歷史系,將來到史語所來幫我。”于是許倬云轉到了歷史系,從此一生以治史為專業。
當時的臺灣大學可謂大師云集,許倬云是被李宗侗、李濟、芮逸夫、董作賓、沈剛伯、凌純聲、錢穆和嚴耕望等名動天下的學術泰斗一路呵護向前的。
那時歷史系15個學生,老師比同學多,許倬云經常一個人一班,等于幾個名師一起教他。讀文科研究所時,學制是由一個3到5人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共同指導一個學生,許倬云跟李濟學考古,跟李宗侗學古代史,跟董作賓學甲骨文,向嚴耕望、錢穆、沈剛伯問學。7年中,他幸運享受了絕無僅有的學習條件,多年后仍感念,“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跟臺大那些老先生們有著很大的關系。”
那時的師生之間,都是以道義相結合,以學問相切磋。因為許倬云走路不便,李宗侗找三輪車讓人把他推到自己家里上課;董作賓教他時也是一對一,一講一下午,餓了買一個饅頭,師生一人一半,到了講不來的地方,就找朋友來教他。先生們覺得,年輕人愿意學,他們愿意教,如此而已。
1957年,許倬云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芝大學術氛圍開放,他學到了一種大歷史視野,這影響了他一生的治學面向,他說:“我的歷史觀,個人的地位最小,最短是人,比人稍長是政治,比政治稍長是經濟,比經濟稍長是社會,比社會稍長是文化,更長的是自然。”
而且在這里,許倬云再次受到了“優待”。他住院做手術時,教他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帶著書到病床前授課,一邊講,一邊討論。
許倬云說:“所以我說自己是一輩子幸運,老天起初對我不好,不過后來對我真是非常好。”他一生都感激這些不同風格的老師,每個人都給了他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了一個楷模讓他去仰慕,從而讓他走出了自己的路。
我視個人良心與學術規范高于一切
不同于專注書案的學者,許倬云始終不失“濟世”熱情。
早在美國留學時,他就一邊讀書,一邊參加民權活動。1964年,34歲的許倬云成為臺大歷史系主任,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的課拿掉。此舉無疑是捅了馬蜂窩,但他堅持教育應有的規矩——不給學生開與專業無關的課。
因容不得虛假,許倬云還與當時在臺大讀研究生的李敖發生了沖突。起因是許倬云發現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里涉及的一些人和事是編造的,就當面糾正:“我們學歷史別的沒有什么,但基本的行規就是不許編造故事。”就這樣倆人吵翻了,開始了終生的齟齬。
1970年,許倬云赴美講學之后,準備回臺灣時,王世杰等前輩因故勸他不要回。許倬云便留在匹茲堡大學任教,自此沉潛學問三十載,著作等身。當時還有大批中國知識分子流寓美國——何炳棣、黃仁宇、楊聯陞、徐中約、周策縱,余英時、杜維明、李歐梵……許倬云與他們亦師亦友,共同奠定了海外中國歷史研究巔峰期的基石。1986年,許倬云當選美國人文學會榮譽會士。
有人問他:“作為一位中國大陸出生,后到中國臺灣求學,又在美國歷練并執教多年的學者,你怎么定位自己的身份?”他說:“我是一個學術界的世界公民,視個人良心與學術規范高于一切。”
我們不像一般談戀愛,是心靈上的來往
許倬云“傷殘卻不自卑”,婚姻上也是。姐姐和嫂嫂曾對他說,“你隨便去鄉下找一個人回來,給你生孩子管家就行。”他聽了十分生氣:“我為什么要那樣就行了?我就要找我要的。”
許倬云談到與妻子孫曼麗的感情,曾經給過一句這樣的評價:“我們不像一般談戀愛,是心靈上的來往。”
孫曼麗是他在臺大當系主任時的學生。許倬云雖然上課風趣,但教學更不含糊,每次碰見學生必問功課,同學們見到許老師就跑,唯獨曼麗不跑;許倬云是系主任,雜事繁忙,有時只能周六上課,沒人敢逃課,唯獨曼麗敢逃——“禮拜六,我要和男朋友出去玩的。”
曼麗畢業后第三年,因為有事請教老師,通信中卻發現倆人“凡事都談得攏”,于是開始交往。父親的反對,卻被她的一句“好手好腳的人也會撞車”堵了回去。1969年兩人成婚,同學驚訝:“你怎么敢和他結婚?”曼麗說:“沒什么敢不敢的。”
年過七旬的孫曼麗回憶起往事,笑聲依舊如銀鈴,滿眼都是幸福與愛意,仿佛還是當年那個明媚的臺大女生。
有人說孫曼麗是“慧眼識英雄”的奇女子,但在她自己看來,這只是愛一個人而已。她笑言:“我很多朋友,結婚時也還不錯,可不知為什么越過越遠。我覺得很幸運,我倆是越過越近。”節目中許知遠感嘆:“許先生很幸運。”孫曼麗笑著糾正:“我倆都很幸運。”
如今的許倬云,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少有篳路藍縷的艱辛傷懷,多的是對人生際遇的種種感恩,以及對現實世界的憂患。他所擔心的問題仍然是:在世界文明變化之大潮中,中國如何自處?以至于妻子在節目中打趣他:“他真的很會愁,世界不好他發愁,中國不好他發愁,中國好了他又發愁,他發愁好了以后不能更好……你不是先天下憂呀,你是天天憂呀。”
如今,老輩學人多已遠去,正如陳寅恪先生感嘆的“正始遺音真絕響”,現在還能聽到許倬云先生的聲音,是我輩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