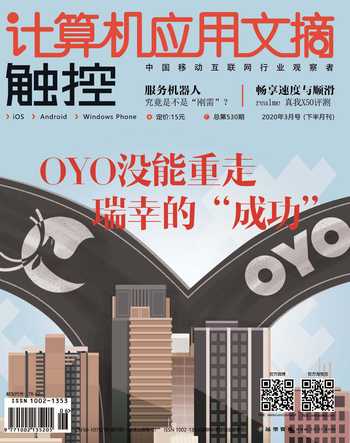36歲的聯想,像極了109歲的IBM?
螳螂財經

缺乏消費者基因的聯想和IBM
2019年對聯想而言是多事之秋,先是“精神圖騰”柳傳志退休,隨后年末手機業務主管常程跳槽小米任副總裁。
在手機業務上,聯想一路走來更是磕磕絆絆。早在2002年聯想就已經進入手機行業,比華為還要早一年。如今,在移動領域的主流視野中已很難看到聯想的身影,后來收購的摩托羅拉系列產品的全球高端化定位也未能掀起較大波瀾。
批評者認為這是由于聯想長期走針對企業的大客戶模式,缺乏消費者思維所導致的。
聯想的業務模式形成了聯想以大客戶需求為主的慣性,這種業務模式的特點是合作關系穩固、客戶需求變動小和盈利率高。
在小米依靠社群和粉絲經濟起家的檔口,聯想手機業務已經摸爬滾打了8年。期間,在2008年出售手機業務,2009年又回購手機業務,可見,當時聯想對要不要做手機以及如何做手機舉棋不定。
即使是在聯想的核心業務PC上,也沒有與消費者建立起有效溝通和情感連接,網絡上大部分針對聯想的指責,都集中在產品配置以及售后等問題上。
而任何一個品牌都會有一群核心的用戶,他們可以成為免費宣傳的“種草粉”,也能成為全網搜集黑點的生力軍,廠商是否“良心”就是他們首要的判斷標準。
可惜,聯想在數次輿論危機中面對的是一面倒的傾向,人們更愿意相信,聯想在對待全球消費者上并未做到一視同仁。
IBM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狀態與聯想類似。早期的IBM業務主要是針對航空等大客戶的電腦銷售制造,1975年,IBM創造性地推出首款型號為5100的“便攜式”計算機。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PC業務成為IBM業務的主營業務之一,并且創造了ThinkPad這一輝煌的商務電腦品牌,但是此時IBM產品的用戶定位依然是專業人士、商務人士,以及面向大公司的批量采購產品,美國大公司的大客戶訂單保障了IBM可以保持穩定的盈利和產品銷量。
此時蘋果的MAC、惠普、戴爾以及日本的小型PC廠商都對IBM形成了壓力,IBM劇烈虧損的1992年,戴爾坐收20億美元的營業額。
進入20世紀90年代,資本市場和業界普遍認為IBM處在破產邊緣,1992年IBM的虧損額度達到49.7億美元,IBM逐漸將經營重點從硬件轉向軟件和信息化服務,服務對象定位依然是機構組織類的大客戶。
時勢造英雄,但是英雄更容易失于時勢。好在,IBM沒有對日漸成為買方市場的PC依依不舍,而是迅速壯士斷腕。
從設備制造商轉型為服務供應商
回顧IBM和聯想發展史,都經歷了數次大型調整,其中最重要的轉型都是從設備制造商轉向服務供應商。
IBM從一家生產記錄數據的穿孔卡制造商,到考勤機器以及大型計算機公司,然后轉型為個人PC制造公司,將PC業務出售給聯想后,又化身為一家咨詢、軟件業務為主的服務供應公司,近年又在量子計算和AI領域有不少亮眼表現。
2020年IBM官方認定的成立年限已經達到了109年,實際上IBM開業已經達到130多年,這個世界上沒和IBM打過交道的大型企業屈指可數。
聯想在2000年做到中國PC市場第一時,楊元慶接管了分拆后成立的聯想,并制定了當時的三年戰略,希望終端廠商向因特網服務轉型,然而這次轉型并不成功,在2004年的“裁員”事件之后,各界普遍認為聯想岌岌可危。
一直到收購IBM的計算機業務,聯想才堅定以計算機硬件為核心的業務路徑,并迅速國際化,最終在2014年打敗老對手惠普和戴爾,登頂全球PC之王。
在PC領域站穩腳跟之后,聯想開始了第二次業務結構的重構—增加服務供應比重。
2014年4月1日,聯想成立了四個相對獨立的業務集團,分別是PC業務集團、移動業務集團、企業級業務集團、云服務業務集團,這奠定了至今聯想業務方向。
把收購作為拓展業務圈層的法寶
《21世紀商業評論》發行人吳伯凡曾說過“大公司轉型比戒毒還難”。尤其面對新興事物,個體也不一定能夠非常迅速地反應,對于大公司更難以迅速進入新的商業節奏。
這種情況下,與其投入資源,吸納新人繼續擴充已經龐大的組織架構,不如直接通過收購在相關業務相對成熟的公司,并給予對方一定的獨立性。
聯想和IBM在熱衷收購方面極其相似。聯想進行過多次重要的收購嘗試,2005年聯想宣布以12.5億美元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被認為看作國產崛起的代表性事件,眼望全球的聯想將總部遷移到了紐約。
2007年,聯想試圖收購歐洲的第三大PC廠商Packard Bell,但是被宏碁以3 100萬歐元阻擊;2008年,聯想又試圖收購巴西最大的PC廠商Positivo,后來因為金融危機而放棄;2009年,聯想收購了位于美國西雅圖的消費者技術公司Switchbox Labs;2011年,聯想繼續收購了有117年歷史的日本通信和計算機“巨頭”NEC,這次收購聯想總共用13億元人民幣買了NEC 90%的股份。
就此,聯想全面淡出IT服務、網絡、軟件領域,將業務重心放在個人電腦領域。
2014年1月30日,聯想又以29億美元的價格從谷歌手中收購了摩托羅拉移動,而人們普遍認為這不是一次成功的收購案例,一方面聯想的手機業務并未因此得到提振,另一方面摩托羅拉原有的上萬件專利已經被谷歌消化殆盡,聯想獲利不多,被調侃道“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總的來說,聯想的收購都在于將自己的PC業務打入地方市場,貫徹自己全球化硬件企業的戰略,而這種基于貿工技的收購策略,頗有點交入場費門票的意味。
反觀同樣熱衷于收購的IBM收購史,則是一次次小而精確的局部戰爭,瞄準在行業中與自身戰略方向重合的公司進行收購。
同樣是收購行為,背后的站位、目的體現出了聯想和IBM對自身屬性理解上的差異。
IBM重大收購史和業務表中的公司都是當時在軟件和數據領域具有優勢的公司。可以看到,IBM的每一次收購都是完成自身階段性的戰略目標,業務能力和技術積累是IBM永遠的追求。
2019年為了拓展云計算方面的業務能力,IBM完成了公司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購,以340億美元收購了開源解決方案的紅帽公司,2020年1月19日,IBM宣布將收購私有云計算基礎設施提供商SoftLayer Technologies,增強自身在云計算方面的實力。
未來的聯想,能更像IBM嗎?
雖然聯想與IBM有諸多相似之處,這種共性有偶然因素存在,也有中西方發展階段差異的影響。
IBM在以硬件為主營業務時,恰逢歐美的航空航天等機構組織亟需優質、穩定、先進的信息設備,在這種情況下,專注于大客戶的大規模訂單,會產生穩定的營收。聯想以國內企業機構為主要的合作對象,也是出于同樣的歷史機遇
IBM和聯想都從硬件生產商過渡到信息服務提供商,這個轉型IBM更早一些,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做,而且IBM有信息技術行業長期的深度技術積累,這一點是聯想所缺乏的。聯想的轉型,是2010年后在全球PC市場占據高位之后的轉型。二者都缺乏消費者意識,聯想通過國際化戰略,完成了PC賽道的勝利,只是惜敗于新興移動的移動市場。
IBM和聯想都熱衷于收購,聯想的收購是為了自身在PC業務國際化的目標而努力,并且對摩托羅拉的收購不甚成功。而IBM的收購是在轉型后以自己的業務方向為目標的精準收購。聯想成于硬件,也因為硬件而遭到拖累,因為PC的業務附加值已經過了最佳紅利期,聯想在移動設備賽道的思路明顯經歷了一個較長的迷茫期。但是二者在的根本差異,在IBM對自身定位和市場趨勢有著非常清晰、透徹的洞察。
從目前聯想的業務結構來看,以PC為核心展開,聯想要繼續保持競爭力,在消費者溝通和用戶需求方面有必要改變策略,尤其注重小群效應,或能夠有效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并且重新點燃人們對聯想品牌的熱情。
雖然聯想與發展百年巨擘IBM比起來還是很年輕,不過我們仍然期待,36歲的聯想有一天也可以成長為像IBM一樣的“百年巨人”。
聯想仍然有不少機會,更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