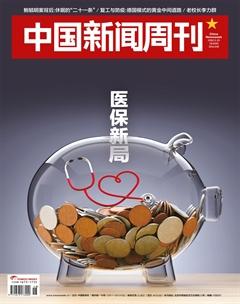鮑毓明案背后:休眠的“二十一條”
古欣

圖/視覺中國
距李星星第一次報案已經過去了700多天。距《南風窗》和《財新》兩篇報道先后掀起輿情嘩然,也已有一個多月,鮑毓明方和李星星方在法律、道德、輿論的戰場上仍然在纏斗。
女孩的年齡,第一次報案的時間,兩人最初是以收養的名義還是其他的目的走到一起,一起生活的時間等,雙方對這些關鍵信息點的說法仍然各執一詞。
在這次事件中,真正戳中公眾痛點的,是二人關系中巨大的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地位、可支配資源以及智識水平的懸殊差異。
十年前,連鎖教育機構山木培訓的創始人宋山木被爆出性侵集團內多位年輕的女員工,從那時開始,公眾開始認識到隱蔽在權力下的侵犯與剝削。十年后,鮑案提供了一個更加極端、雙方實力更加懸殊的樣本。
近些年,隨著大量職場、高校性侵與性騷擾事件的曝光,公眾認識到,類似的事件已經不只關乎暴力,而且關涉熟人語境下的權力與控制關系。盡管類似案件總會引發輿論關注,但司法實踐中,這些案件常常處于道德與法律的中間地帶,證據不夠不能立案,或者情節顯著輕微不予起訴,是此類案件常常遇到的難題。
“洗腦”與立案難
目前,鮑毓明案還處于公安機關偵查階段,對于該案是否能最終進入司法程序,李星星的代理律師、常年從事未成年女性性侵維權的郭建梅感到擔憂。
曾經援助過李星星的律師李瑩,曾代理過滿洲里人大代表性侵幼女案,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刑事訴訟證據標準很高,要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要形成完整、閉合的證據鏈條,僅僅只有孤證或者被害人一方的陳述,或者證據的指向不一致,有相反的證據,公安機關都大概不會立案。
而鮑毓明案就存在有相反證據的可能。鮑毓明曾經向媒體泄露一份他與李星星的聊天記錄,該記錄里,李星星對鮑毓明說了一些示愛的話。
能否立案,取決于公安機關如何理解性侵案件中最核心的要素“自愿”。對于鮑毓明案,有人認為,即便這些記錄沒有偽造,表面上來看李星星是自愿的,但實際上仍應認定為“不自愿”,因為李星星在長期與鮑毓明相處的過程中,可能已經被其“洗腦”了。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副教授曾文科曾經撰文探討,“洗腦”是否能構成強奸罪的手段行為。他指出,強奸罪保護的是婦女性的自主決定權或者說性自由,在婦女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的情況下與之發生性行為的,都屬于強奸。郭建梅也認為,要考慮到被害未成年人案發時,是否有能力正確認知自己言行的法律意義和后果,又是否有能力在完全不受外在因素影響下具有選擇表達不同意的意思自由。
具體到鮑案,這需要司法機關全面結合案發時李星星的年齡、認知水平和身體狀況、成長的經歷,犯罪嫌疑人鮑毓明的身體狀況、身份背景、與被害人李星星所處的角色地位、相處模式等等各種因素去判斷。
但一個顯著的現實是,郭建梅從前代理過的案件中,依靠權力控制、心理控制,以及精神強制或曰“洗腦”這樣的手段行為進行“強奸”,往往在還沒進入司法程序時,就倒在立案的第一環。
郭建梅曾經代理過黃波案件。黃是一家大學生培訓機構的導師,好幾位參加課程的女孩,稀里糊涂地跟他發生性關系后,后來都要告他,理由就是被黃“洗腦”。
據《南方都市報》前記者李思磐的報道,黃波的洗腦方式是,以成功與未來作為誘惑和考驗,以談人生的名義將學生約到房間,掐著秒表,測試學生當著他的面,能不能在90秒超越自己,克服心理障礙,脫掉衣服。衣服脫掉后,下一步就面臨著跟他發生性關系。
郭建梅作為黃波案受害者的代理人做了巨大努力,但警方最終還是決定不立案,理由是缺乏證據。李思磐回憶,黃波案中有受害者是未成年的大專生。當時《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二十一條(下簡稱“二十一條”)尚未出臺,能夠援用的法條僅僅是“暴力”“脅迫”之外“其他手段”這一兜底條款。而警察卻對報案的學生說,“你們自己有錯,這個情況不是強奸。”
近些年郭建梅代理過的涉及“洗腦”與誘惑的性侵案件里,勝訴的只有2010年的宋山木一案。宋山木案是權力關系下性侵的里程碑式的案例,郭建梅、李瑩都曾參與其中。她們在向《中國新聞周刊》復盤宋山木案件時都表示,宋案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除了被害人的自述,法院還認定了其他證據。
在宋案中,法官認定了如下事實:被害人被宋山木帶到山上一所地處偏僻的公寓,處于孤立無援的環境;被害人與宋山木之間沒有情感關系;被害人事后的行為顯示出厭惡之情,遭到強奸后,把當天的所有衣服丟棄到垃圾桶里,被害人在遭遇強奸的當晚,向同寢室的人和男朋友哭訴。這些證據互相印證,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證明強奸是違背被害人意愿的。
多年的辦案經歷讓郭建梅有一個體會,很多基層辦案人員在意識理念上,在對相關法條的理解適用上,是趨向保守的。很多時候,基本上只是認直接的肢體暴力手段,而對類似發生在熟人之間的,行為人不是通過直接肢體暴力,而是更多利用其與被害人之間的上下級從屬關系(不平等權利關系)或特殊的職權便利,通過權力控制、精神強制和心理控制等手段實施的性侵行為缺乏正確的認識。
律師李瑩認為,十幾歲的孩子經歷熟人性侵的案件,樣態往往十分復雜,她們常常來自于貧困家庭,處于權力控制或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很難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她舉例自己曾經主辦的滿洲里一位人大代表性侵幼女案。該案的基本事實是高年級女生強迫低年級女生賣淫,收取嫖資。嫖資的一小部分被當作零花錢和生活費給了被強迫賣淫的低齡女生。在這個案件中,大部分已滿14歲的未成年人因為接受了這一小筆錢,有的甚至是因為被侵害后與大家一起吃了宵夜,就被認定為是性交易而非強奸。最后還是因為被性侵的幼女中有個人未滿14周歲,才對侵犯該女的行為認定為強奸。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證據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性侵案件又多在隱秘環境下發生,證據鏈達不到公安機關的立案標準,最后不予立案,是郭建梅、李瑩在代理類似案件中遇到相同的困境。
鮑案引發輿情之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再次撰文倡導他一直以來的觀點,即在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的問題上,要確立“報案即立案”制度。
“父女”與現行法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頒布《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下文稱《意見》),其中第二十一條規定,“對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意見》第九條明確了負有特殊職責人員的范圍,即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教育、訓練、救助、看護、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
2014年,時任最高法院刑一庭法官周峰、薛淑蘭、趙俊甫、肖鳳共同撰文《<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下文稱“理解與適用”)。文中解釋“二十一條”的制定是為了針對一種事實情況,即實踐中,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少女雖然比幼女的認知、判斷能力有所增強,但其身心發育尚未完全成熟,在日常生活、學習和物質條件方面對監護人、教師等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存在一定的服從、依賴關系,容易在非自愿狀態下受到性侵害。“有時行為人對此類被害人實施程度相對于成年被害人而言可能僅是輕微的脅迫,即可使未成年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進而達到奸淫目的。”
為了解決此種情況,“二十一條”規定了在認定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與對其有特殊職責的人之間的強奸時,適用特殊的證據標準。“對于強制手段和程度的認定,應充分考慮未成年被害人身心脆弱,及與特殊職責人員之間存在特殊關系,易受傷害等情況,與針對成年人實施的強制性侵害行為有所區分。”
“理解與適用”進一步指出:具體而言,所謂“利用優勢地位”進行奸淫是指,行為人故意利用這種特殊關系,以使未成年被害人的生活條件、受教育或訓練的機會、接受救助或醫療等方面可能受到影響的方式,對被害人施加壓力,使其不得不容忍行為人對其進行奸淫,比如,養(生)父以虐待、克扣生活費迫使養(生)女容忍其奸淫,或者對處于身患嚴重疾病、流落街頭需要接受救助等境地的未成年被害人進行奸淫。
這意味著中國在司法實踐中已經認識到,特殊職責地位在針對未成年人實施的性犯罪中的作用,但該文同時指出,“職責地位這一事實狀態本身并不足以將性行為轉化為犯罪,職責地位的存在與否影響的只是‘自愿認定。”也就是說,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夠提供證明被害人是與其自愿發生性行為的相關證據,仍然需要綜合考慮來判斷強奸是否成立。
郭建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刑法對強奸罪的規定以及“二十一條”的法律框架下,李星星案件有三個核心的法律爭議點,一是李星星的年齡,二是鮑毓明對李星星是否具有特殊職責,三就是同意與自愿的問題。
此案中,李星星與鮑毓明發生性關系已經年滿十四歲,郭建梅主張按照“二十一條”的規定,只要兩人形成了事實上的監護關系,就有可能對鮑毓明追責,無論鮑毓明是否具有收養李星星的法律資格。
在郭建梅看來,雙方最初的接觸到底是以收養的名義,還是鮑某主張的談戀愛,這是鮑毓明案件定性的一個關鍵。郭建梅提到了如下事實:鮑承認自己與李星星在北京、天津、煙臺、南京等地一起長期生活過;鮑毓明曾給李星星寫過一封保證書“給我現在的女兒,和未來的妻子”;他和李星星的網絡聊天記錄里,星星也一直叫他爸爸。這些都是鮑毓明自己向媒體提供的“證據”。
休眠的二十一條
司法實踐中,佟麗華很少見到有司法機關根據上述“二十一條”辦理案件,他感覺這個條款“似乎休眠了一樣”。
《中國新聞周刊》檢索裁判文書網,發現《意見》頒布以后的過去七年之間,僅有三例案件法官明確適用了第二十一條規定,這三例案件都是2019年判決的,其中兩例發生在繼父與繼女之間,一例發生在中學體育老師與學生之間。
佟麗華和他的團隊曾就2009至2014年間媒體報道的1065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進行統計分析,除去被害人和侵害人關系未知的16個案件外,有739個案件是由熟人實施,占全部案件的69.39%。
在熟人作案的739個案件中,監護人(父母、養父母、繼父母)實施的共66件,其他家庭成員或親屬實施的32件。學校工作人員(包含學校的校長、教師以及與學校有勞動關系的其他員工)實施的性侵害案件共140件。
現在的“二十一條”,最初的雛形,是佟麗華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就《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征求專家意見的會議上提出的。當時他建議,只要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教育、培訓、救助、看護、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身份或職務便利,與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之間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就以強奸論。
他的建議被吸納,但《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正式發布時,對內容有所調整,增加了“利用優勢地位或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的表述。
佟麗華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司法機關是為了排除確實基于“談戀愛”的情形。
從“二十一條”的出臺過程里,也可以看到在打擊未成年性侵犯罪方面,一直存在兩種法益,即保護未成年人與尊重個體自由決定的沖突權衡。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教授羅翔表示,支持在被害人與侵害人之間有特殊關系時,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8歲。理由是這時法律實行的是一種家長主義,通過限制未成年人性自由和處分權來保護她們的性利益。如果沒有限制,一定會導致強者濫用對弱者的優勢地位,造成強者對弱者的性利益剝削。
李思磐發現,這一類事件有一個共性,受害者和加害者往往是一對多的關系,而加害者被捅出的契機,也是其中一個受害者突然發現自己只是眾多對象中的一個,而并不是專一的“愛”的對象,曾經用來自我說服的理由轟然倒塌。黃波案的爆發,就是從黃波最信任的女助手收到了一封別的女生寫給黃波的控訴信開始。
羅翔提出,在條件成熟時,應該在刑法規定中增加濫用信任地位剝削性利益罪名。郭建梅也希望通過立法層面完善,防止權力關系下的性侵行為。根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牛帥帥的研究,在澳大利亞部分州及英格蘭和威爾士,如果一個人利用相對未成年人的權威或信賴地位,使后者與之發生性關系(不限于性交),那么法律有理由不認可未成年人做出的“性承諾”的有效性。
但法律界也存在另一種觀點。羅翔的同事曾文科就認為,如果單設一個罪名,會出現檢察院只要證明行為人具有優勢地位,與受害人發生性關系就是犯罪,這種情況就沒有給被告人留下任何一點余地,否定了“意愿”作為強奸罪的本質構成要件。
從立法技術的角度,曾文科認為,比起單設一個不允許被告反駁的新的強奸罪名,通過司法解釋,或者在現有的立法條文中,增加一條關于舉證責任分配的條款更為理想。他舉例,譬如可以做類似規定,“如果利用優勢地位,諸如親屬或者師生,上下級之間發生性關系的,除非被告人提出相反證據外,推定是違背未成年受害人意愿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檢察院可以減輕自己舉證責任負擔。”
根據Legal Ages of Consent By Country網站提供的全球201個國家和地區性承諾年齡的統計,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規定的性承諾年齡集中在14~18歲之間,其中有76個國家的性承諾年齡為16歲,占37.8%。性承諾年齡高于14歲的共147個,占全部總數的73%。相比之下,中國的性承諾年齡設置在全球范圍內偏低。
郭建梅認為,很多歐美國家性開放程度比中國高很多,也有較為完善的性教育。然而它們的性同意年齡定在16歲、18歲。而中國性文化氛圍相對保守,性教育不充分,在這樣的情形下,性同意年齡過低是對女孩極大的不負責。
曾文科則提醒,保護的同時也是在限制自由,當法律把一般的性同意年齡定到16歲時,同時也剝奪了一個16歲女孩自愿與人發生性關系的自由。“立法建議需要建立在實證數據調研的基礎上,并聽取心理學和生理學專家的意見。”
曾文科同時指出,很多人大代表建議提高性同意年齡的同時,又提倡刑事責任年齡往下調。既然要求刑事犯罪年齡降低,說明青少年能夠認識到強奸意義上的年齡是降低的,這種情況下,做提高性同意年齡的呼吁,其實是一種很矛盾的做法。